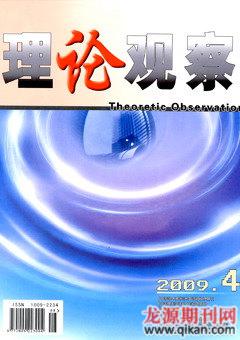悲壯的生存抉擇與歷史跋涉
蔡 軍 唐守祥
[摘要]“闖關(guān)東”歷史社會(huì)現(xiàn)象作為中華民族發(fā)展史中不容置疑的客觀存在,不僅理所應(yīng)當(dāng)?shù)某蔀橹腥A民族發(fā)展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dú)v史篇章,而且更應(yīng)成為中華民族發(fā)展史中不該遺忘的寶貴精神遺產(chǎn)。闖關(guān)東現(xiàn)象就是中華民族的先民們?cè)谀菢O其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世代薪火相傳以其生命的代價(jià),在一片荒漠的土地上刻下的人類爭(zhēng)取生存自由的意志印記。
[關(guān)鍵詞]闖關(guān)東;生存抉擇;歷史跋涉
[中圖分類號(hào)]G122[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文章編號(hào)]1009—2234(2009)04—0010—03
“人類生存環(huán)境受到的挑戰(zhàn)愈強(qiáng)烈,而刺激文明生長的積極力量就愈加強(qiáng)烈。”——這是哲學(xué)思想史中的一個(gè)著名論斷。而出現(xiàn)在中國歷史上的“闖關(guān)東”現(xiàn)象,則正是不同歷史時(shí)期的中華民族底層民眾在面對(duì)生存挑戰(zhàn)時(shí)所激發(fā)的一種促進(jìn)文明生長的積極力量,是最底層的人民面對(duì)生存危機(jī)時(shí)所作出的歷史與現(xiàn)實(shí)的悲壯抉擇。“闖關(guān)東”的悲壯并不僅僅在于個(gè)體民眾對(duì)天命反抗的行為特色,更主要的是在于“闖關(guān)東”過程中實(shí)踐主體的那種敢于直視慘淡命運(yùn)義無反顧的本能勇氣,那種敢于藐視艱難困苦百折不撓的不屈韌性,那種敢于蔑視生死險(xiǎn)惡前赴后繼的主動(dòng)精神——我們中華民族的先民們也正是因?yàn)橛辛诉@種堅(jiān)強(qiáng)意志和主動(dòng)精神,才有了一代代愚公移山般薪火相傳、精衛(wèi)填海般奮不顧身、夸父逐日般執(zhí)著無前的“闖關(guān)東”實(shí)踐。因而造就了今日祖國關(guān)東大地生機(jī)勃發(fā)的文明命運(yùn),成就了今日祖國關(guān)東大地生機(jī)盎然的文明傳統(tǒng)……正所謂——“無民風(fēng)之擊壤,何來王頌之封疆?”正是當(dāng)年那些生存受到挑戰(zhàn)、受到威脅的人們以“闖關(guān)東”的生命實(shí)踐真正創(chuàng)造了一段沒有記錄的歷史,也正是“闖關(guān)東”這段不被記錄的歷史跋涉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地域的燦爛文明。
一、不可抹殺的中華民族抗?fàn)幟\(yùn)重壓的歷史真實(shí)
“闖關(guān)東”作為中華民族成長史的一個(gè)沉重伴音,但由于正史文籍記載很少,所以,很長時(shí)間里為史學(xué)界所忽視,鮮有涉獵者。偶有論及,卻也偏誤多多,有的將其與戍邊拓疆相聯(lián)系,有的又將其與流人文化合流……甚至還有人干脆就把它稱為清代中晚期的一項(xiàng)移民工程,閃爍其詞的暗示“闖關(guān)東”乃朝廷指令開發(fā)的結(jié)果……在這里,應(yīng)該澄清的至少有三點(diǎn);首先一“闖關(guān)東”現(xiàn)象絕不是近二三百年方才突發(fā)的歷史事件;第二“闖關(guān)東”也絕不是出于某個(gè)朝代頒發(fā)的開發(fā)動(dòng)員令的導(dǎo)向所至;第三“闖關(guān)東”亦非官方有組織有計(jì)劃的規(guī)模性集體行為。它是一個(gè)幾乎綿延噬個(gè)封建社會(huì)的漫長的歷史社會(huì)現(xiàn)象。“闖關(guān)東”從一開始就是一個(gè)來自民間的、散在無序的、相當(dāng)漫長的、涓流成河積沙成塔的歷史過程;從一開始就是來自社會(huì)底層民眾個(gè)體的自我生存選擇,而且根本不以統(tǒng)治者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甚至不為當(dāng)時(shí)的官府王法所羈絆。從歷史縱向去觀察“闖關(guān)東”的歷史過程是悲壯的、生生不息的、綿延不斷的,而從每個(gè)歷史橫向點(diǎn)看去則是悲涼的、零散殘斷的、時(shí)有時(shí)無的……
“闖關(guān)東”所指的“關(guān)東”并非一般歷史文集中所稱述的地理概念,亦非具體地名的稱謂的載體。這里所說的“關(guān)東”是泛指山海關(guān)以東以北、長城邊墻以外的廣大地區(qū),也就是當(dāng)今的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內(nèi)蒙古的部分地區(qū)。由于歷史上對(duì)“關(guān)東”多有封禁圈圍政策,嚴(yán)禁關(guān)內(nèi)民眾進(jìn)入關(guān)東,故而闖關(guān)成為具有極大風(fēng)險(xiǎn)的民生行為。據(jù)史料記載,清代康熙年間,為防止關(guān)內(nèi)漢人闖關(guān),除了加固、加強(qiáng)了山海關(guān)、薊鎮(zhèn)邊墻的防范之外,還又修建了柳條邊,嚴(yán)禁中原漢人出關(guān),對(duì)關(guān)東所謂的滿清“龍興之地”實(shí)施圈圍保護(hù)禁止開發(fā)。《柳邊記略》中就曾記述:當(dāng)時(shí)旗人出關(guān)尚需本旗固山額真向兵部報(bào)送牌子簽發(fā)滿文路票,而漢人出關(guān)則須逐級(jí)呈請(qǐng)兵部,或報(bào)請(qǐng)隨使印官衙門簽發(fā)漢文路票。對(duì)于當(dāng)時(shí)的普通百姓,特別是那些流難災(zāi)民來說,是根本無法獲得這些路票、關(guān)牒的,因而惟有闖關(guān)一條路。
“闖關(guān)東”作為中國社會(huì)歷史移民現(xiàn)象的一種特定稱謂,雖然直到明代才初見于史料文字記載。其實(shí),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進(jìn)程中這種“闖關(guān)東”社會(huì)現(xiàn)象卻幾乎哪個(gè)朝代都曾不同程度的發(fā)生。據(jù)有關(guān)史書記載:在公元前西漢建平元年間就有中土人士避難流徙遼西;到了三國、北魏年代也多有中原人等因列國紛爭(zhēng)逃難到遼東;兩晉到隋末年間中原戰(zhàn)亂大批難民紛紛涌向邊隅自不必說;僅宋代建炎元年一次就流徙東北18000余人,零散鄉(xiāng)眾尚未計(jì)其中——據(jù)部分史料不完全統(tǒng)計(jì):截止元代末期有籍可查流徙東北的中原人等至少已超過200萬以上;待到明代“闖關(guān)東”現(xiàn)象更如洪水猛獸,統(tǒng)治階級(jí)刻意阻堵都成為困難。(1381)洪武年間重修萬里長城構(gòu)筑山海關(guān),更是為了外防異族侵犯內(nèi)阻國人闖關(guān)——緣由于此,因而在中國語匯中從此出現(xiàn)了“闖關(guān)東”這一特定語詞。后來的年代“闖關(guān)東”就更是成為動(dòng)蕩社會(huì)司空見慣的現(xiàn)實(shí),僅從清代晚期到1949年就有3000萬關(guān)里人闖出山海關(guān)到東北尋求生計(jì)。
但是這里值得特別強(qiáng)調(diào)的是:盡管“闖關(guān)東”社會(huì)現(xiàn)象歷朝歷代不絕于世,可在封建社會(huì)的正史典籍中卻少有記載,偶爾字里行間帶上幾句,也大多為粉飾太平之詞,可信度也大打折扣。顯然,封建社會(huì)的歷代當(dāng)政者全都羞于承認(rèn)失政,他們把自己當(dāng)政期出現(xiàn)的“闖關(guān)東”現(xiàn)象視為丟人與丑陋的敗績(jī),沒有哪一個(gè)統(tǒng)治者愿意把自己當(dāng)政時(shí)期“闖關(guān)東”這一不光彩的記錄留下來——應(yīng)該說,是歷朝歷代的統(tǒng)治階級(jí)有意隱瞞了“闖關(guān)東”這一歷史真實(shí)。所以“闖關(guān)東”是一種已經(jīng)在歷史上實(shí)際發(fā)生了的大而又大社會(huì)現(xiàn)象,同時(shí)又是一件不被以往文史所登錄與記載的少而又少的社會(huì)史實(shí)。
二、不可磨滅的中華民族追求生存自由的意志印記
這里還應(yīng)該再次強(qiáng)調(diào)的是,任何年代出現(xiàn)的“闖關(guān)東”現(xiàn)象,究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來自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環(huán)境對(duì)于底層民眾的生存壓迫,是當(dāng)時(shí)底層民眾的生存環(huán)境受到破壞或面臨生存危機(jī)后而激發(fā)的本能反應(yīng),實(shí)踐主體從而作出的鋌而走險(xiǎn)的個(gè)體生存抉擇。求生求存的本能需求成為在生死線上掙扎的底層民眾“闖關(guān)東”行動(dòng)的原始內(nèi)在驅(qū)動(dòng)力——這種本能的求生力量,雖然來自民間,盡管自發(fā)而零散,但卻是任何勢(shì)力所無法阻擋的。因而,“闖關(guān)東”的關(guān)鍵點(diǎn)在于這個(gè)“闖”字。雖然后來中原內(nèi)地也曾出現(xiàn)諸如“走西口”“下南洋”等移民現(xiàn)象,但其移民主體以及規(guī)模與影響,尤其是根本性質(zhì)卻與“闖關(guān)東”不可同日而語——是“闖”的性質(zhì)決定了他們的個(gè)體追求必然與統(tǒng)治階級(jí)的愿望背道而馳,是“闖”的性質(zhì)決定了他們的自主行為必然不以統(tǒng)治階級(jí)的意志為轉(zhuǎn)移。“闖關(guān)東”其實(shí)闖的是關(guān)東的遠(yuǎn)荒地帶——可以想象,皇家圈圍的“龍興之地”會(huì)讓逃荒的流民涉足嗎?商賈掌控的市井鬧市能有要飯的饑民棲身之所嗎?王爺領(lǐng)主的封地牧場(chǎng)會(huì)讓流難的災(zāi)民開荒種地嗎?土豪劣紳霸占的土地山林會(huì)讓這些饑寒交迫的人們安家立業(yè)嗎?所以“闖關(guān)東”只能往關(guān)東更深遠(yuǎn)的荒蠻之地去闖;到山高皇帝遠(yuǎn)的地方去闖;到官府衙門鞭長莫及的地方去闖;到窮山惡水出刁民的地方去闖……恐怕,這就是“闖關(guān)東”精神的核心價(jià)值
所在。
所以,每當(dāng)社會(huì)出現(xiàn)周期性動(dòng)亂,或發(fā)生人力無法抗拒的自然災(zāi)害時(shí),社會(huì)都可能出現(xiàn)人口的流動(dòng)現(xiàn)象。兵爨、天災(zāi)使人民無所依聊,被迫流徙尋求生計(jì),“困易從革,窮則思變。”于是乎,“闖關(guān)東”就成為歷史的必然了。人類發(fā)展史證實(shí),無論生存環(huán)境如何險(xiǎn)惡,都無法泯滅人類對(duì)新事物的不懈追求與渴望。在“闖關(guān)東”這場(chǎng)浩大的人類追求生存自由的行動(dòng)中,當(dāng)時(shí)的人們求生、求存的本能欲望成為最基本的主體意識(shí)。盡管這種主體意識(shí)的外延是模糊的,具有著方向與目標(biāo)的不可測(cè)性。而其內(nèi)涵又是多元的、復(fù)合的,呈現(xiàn)出多民族的、多階級(jí)的、多層面的,或原始蒙昧的、或封建傳統(tǒng)的、或復(fù)合雜交的多元色彩。而且這種主體意識(shí)也許有的源于中原農(nóng)耕民族生態(tài)意識(shí)的因襲,有的源于流難災(zāi)民的盲流本性;或來自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的自發(fā)心理,或來自形形色色冒險(xiǎn)生涯的占有欲望……但無論具有怎樣的正義的還是罪惡的、善良的還是丑惡的各種紛紜復(fù)雜矛盾對(duì)立的內(nèi)在驅(qū)動(dòng)心理,其求生、求存、求進(jìn)、求新的基本心理需求卻是相同的,那種對(duì)關(guān)東黑土地的認(rèn)同感卻是一致的。正是由于這種強(qiáng)烈追求理想與自由的信念激發(fā),才會(huì)有自清末以來一批又一批血管里流淌著不安分血液的“流民”義無反顧、執(zhí)著無畏地?fù)溥M(jìn)這片神秘而陌生的黑土地,誠如一首賦中所言“……五湖四海是匯,萬水千山是聚,紛紛然闖關(guān)東飛蛾撲火之前赴,洶洶然投北荒餓蟻搶灘之后繼……”“闖關(guān)東”的人們將人生命運(yùn)的賭注押進(jìn)關(guān)東大地這片天涯洪荒,以堅(jiān)韌不拔的血汗拼搏在亙古荒原上刻下人類文明的印記。正是有了“闖關(guān)東”的歷史存在,才使得關(guān)東大地呈現(xiàn)出“洪荒草昧初治耕冶,邊極榛莽始奠稼桑。”正是有了“闖關(guān)東”的歷史存在,才使得關(guān)東大地呈現(xiàn)出“寒風(fēng)笳角鴻聲里民族雜處而代進(jìn)相融,絕塞星河雪影中移民遷徙而漸興邊圉”的歷史局面。“闖關(guān)東”人們以艱苦卓絕的開拓性實(shí)踐顯示了人類對(duì)命運(yùn)對(duì)自然的抗?fàn)帒B(tài)度。而且這種生存跋涉愈險(xiǎn)峻愈艱苦,所遭受阻力與壓力愈大,那種被壓抑的欲動(dòng)的渴望與思變的決心反而愈加強(qiáng)烈,當(dāng)實(shí)踐主體的悲壯情緒與欲動(dòng)渴望不時(shí)的與對(duì)象客體的悲涼現(xiàn)實(shí)與慘淡現(xiàn)狀相撞擊時(shí),終于迸發(fā)出一團(tuán)不滅的獨(dú)具“闖關(guān)東”人特質(zhì)的精神之火——這就是具有鮮明的征服與開拓特色的“闖關(guān)東”精神。
三、不該忘懷的中華民族追求生存自由的主動(dòng)精神
“闖關(guān)東”社會(huì)歷史移民現(xiàn)象,為社會(huì)學(xué)研究提供了一個(gè)很耐人尋味的課題。人口是社會(huì)活動(dòng)的主體,人口的變遷乃是社會(huì)變遷最基本的動(dòng)態(tài)表現(xiàn),任何朝代任何政權(quán)都可能面臨不可避免的政治經(jīng)濟(jì)不平衡所引發(fā)的社會(huì)危機(jī)或動(dòng)亂,而普通民眾采取非暴力的遷徙流難方式自尋生路,這在客觀上實(shí)際起到了幫助執(zhí)政者平衡和緩解社會(huì)矛盾的積極作用。但中國封建政權(quán)卻對(duì)這種民眾合理性舉動(dòng)往往采取否定政策,甚至于以一些極其可笑而愚蠢的理由加以阻止和鎮(zhèn)壓。就連康熙這樣一代圣明君主尚且提出“因祖宗肇跡,興王之所于彼”而對(duì)關(guān)東實(shí)行封禁。試想如果當(dāng)年關(guān)東不實(shí)行封禁政策,何至于康熙兩克雅克薩,反倒簽約“尼布楚”,全都棄城而返,究其根本原因卻是無民守城無人守疆……正是由于清王朝統(tǒng)治者犯下的這種低級(jí)錯(cuò)誤,以至后來俄羅斯得寸進(jìn)尺卷土重來侵占我國遠(yuǎn)東數(shù)百萬平方公里土地。所以“闖關(guān)東”的核心內(nèi)涵在于一個(gè)“闖”字,這種“闖”尤其悲壯與艱難,“闖關(guān)東”的實(shí)踐主體不僅要面對(duì)窮山惡水的艱難險(xiǎn)阻,還要應(yīng)對(duì)統(tǒng)治階級(jí)的圍追堵截。因此說,在這個(gè)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中華民族最基本的底層民眾在為爭(zhēng)取生存自由時(shí)所表現(xiàn)出的那種堅(jiān)韌不拔的意志品質(zhì)與誓死不渝的主動(dòng)精神,才是“闖關(guān)東”實(shí)踐主體本質(zhì)力量真實(shí)顯現(xiàn)。
新中國的建立,一掃舊日的陰霾,針對(duì)過去政權(quán)無法面對(duì)無法解決的社會(huì)問題,新中國的締造者們?cè)诔浞挚偨Y(jié)歷史籌劃未來的基礎(chǔ)上,從代表全中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出發(fā),實(shí)事求是的正視建國初直至上個(gè)世紀(jì)60中葉尚存的“闖關(guān)東”現(xiàn)象,并進(jìn)行了認(rèn)真的現(xiàn)實(shí)性研究與歷史性分析。當(dāng)國家政治經(jīng)濟(jì)出現(xiàn)周期性變化時(shí),黨和政府就果斷進(jìn)行了有組織有計(jì)劃的重大移民行動(dòng)——新中國、新社會(huì)、新時(shí)代的“闖關(guān)東”。從1954年起就不斷的強(qiáng)化“屯墾戍邊”——尤其1958年,一支有十萬之眾,以軍事建制意氣風(fēng)發(fā)浩浩蕩蕩開進(jìn)關(guān)東地域亙古荒原1北大荒。這是一次具有歷史性超越意義的浩大移民工程,關(guān)東邊極地域人口出現(xiàn)激增,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jì),當(dāng)年僅進(jìn)入北大荒的官兵就有十萬之眾,另外還有十?dāng)?shù)萬官兵家屬,同時(shí)還從山東、四川等省招來的幾十萬支邊青年。這次浩大的前所未有的移民行動(dòng)不僅為以后共和國糧倉的建立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同時(shí)也為北方工業(yè)的崛起創(chuàng)造了條件,更重要的新中國、新社會(huì)、新時(shí)代的這場(chǎng)“闖關(guān)東”一定程度的緩解了建國初期內(nèi)地自然災(zāi)害引發(fā)的經(jīng)濟(jì)壓力,相對(duì)有序的吸納與安置了大量關(guān)內(nèi)災(zāi)民,在當(dāng)時(shí)起到了穩(wěn)定社會(huì)的重要作用。
新中國、新社會(huì)、新時(shí)代的“闖關(guān)東”是以軍事人群為主體組成的拓荒大軍,這支隊(duì)伍不乏堅(jiān)定的共產(chǎn)主義信仰、鮮明的無產(chǎn)階級(jí)立場(chǎng)、高尚的政治思想覺悟,而且更具先進(jìn)的生產(chǎn)手段、旺盛的生產(chǎn)能力、堅(jiān)強(qiáng)的勞動(dòng)意志、嚴(yán)謹(jǐn)?shù)膭趧?dòng)組織。這支隊(duì)伍的覺悟性、純潔性、紀(jì)律性、服從性都是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移民工程既無法比擬的。新中國的“闖關(guān)東”揭開了關(guān)東歷史開發(fā)的新紀(jì)元,僅北大荒就有數(shù)千萬畝荒原、林地、水面得以開發(fā),幾十座大型礦山開工,修成了幾百公里的鐵路運(yùn)輸線、公路通車?yán)锍踢_(dá)數(shù)千公里……。總之,開拓者的超越性征服業(yè)績(jī)是巨大的,創(chuàng)造性成果是無比輝煌的,與此同時(shí)北大荒的開拓者們也同時(shí)創(chuàng)造了完全能夠代表新中國風(fēng)貌的新時(shí)代“闖關(guān)東”精神——北大荒精神。
北大荒精神雖然屬于一種新時(shí)代地域精神,但在本質(zhì)上卻是與傳統(tǒng)的“闖關(guān)東”精神是一脈相承的。都是在征服性實(shí)踐中塑造了一個(gè)大環(huán)境的地域群體的思想品格,而且在時(shí)間的考驗(yàn)中形成一種觀念形態(tài)的歷史積淀,使這種精神不僅成為當(dāng)?shù)卣挝幕闹匾M成部分,并且深深地滲透于普通人的人格之中……“闖關(guān)東”作為一種社會(huì)現(xiàn)象,能產(chǎn)生如此巨大的社會(huì)效應(yīng)是令人吃驚的。這種精神是以地域群體的生存欲望和現(xiàn)實(shí)需要為內(nèi)在驅(qū)動(dòng)力,因而形成了一個(gè)昂揚(yáng)向上的主動(dòng)爭(zhēng)取與征服情調(diào)的發(fā)展態(tài)勢(shì),表現(xiàn)出總基調(diào)的進(jìn)步性。當(dāng)然它囿于歷史的局限,其形成過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某些不確定因素的沖擊和影響,因而構(gòu)成了多元化的選擇途徑和多變化的發(fā)展形式,文化表現(xiàn)上總能暗示或標(biāo)明不同階段的時(shí)代色彩與時(shí)代印記。但是,盡管這種精神充滿了活的變化色彩,它卻并沒有隨著即時(shí)性政治的變遷而消亡,也沒有隨著那些特質(zhì)因素的消退而改變。這種地域精神反而做為一種地域群體的文化意識(shí),從活躍變?yōu)榉€(wěn)定、從零散變?yōu)榧小碾鼥V可塑的胚胎輪廓,變?yōu)橄到y(tǒng)而完整的有血有肉的具有凝聚力和包容力的帶有鮮明地域特色的精神傳統(tǒng)而固定下來。一種社會(huì)現(xiàn)象能夠轉(zhuǎn)變?yōu)橐环N地域群體認(rèn)同的文化心理,這不僅是一種鮮見的進(jìn)步,而且應(yīng)該是一種超越。關(guān)東地區(qū)是一個(gè)十分特殊的地域,這里曾極其原始荒蠻,缺乏歷史傳統(tǒng)文化的積淀,每一個(gè)踏上這片土地的人,都會(huì)出于本能的、自我的、超我的心理尋找精神的支撐點(diǎn),以抗衡自然力的壓迫,要建樹一種現(xiàn)實(shí)的信仰與崇拜,賴以維系與支持自我人格的獨(dú)立。追溯歷史,過去時(shí)代“闖關(guān)東”的先輩們?yōu)槲覀兘淞诉@個(gè)精神的支撐點(diǎn),“闖關(guān)東”不僅成為獨(dú)立的地域文化事實(shí),而且做為一種特有的地域文化心理積淀深深地浸透于闖進(jìn)關(guān)東黑土地上的每一個(gè)普通人的人格之中,在他們的思想意識(shí)中占有統(tǒng)治地位,并以其強(qiáng)大的輻射力影響和支配著他們的是非觀念、價(jià)值取向、道德規(guī)范、審美意識(shí)。
我們都知道,文化精神是人類社會(huì)歷史生命的最深層次,具體的地域文化精神乃是該地域群體最基本最深層的心里積淀。它一方面表現(xiàn)為歷史的繼承性與穩(wěn)定性,另一方面又常常表現(xiàn)出現(xiàn)實(shí)的即時(shí)性和功利性,特別是當(dāng)它以感性特征顯現(xiàn)特定時(shí)期、特定環(huán)境、特定人群的需要層次的實(shí)體內(nèi)容時(shí),這種傾向就更為鮮明。“闖關(guān)東”既是歷史社會(huì)現(xiàn)象同時(shí)又是歷史文化現(xiàn)象,它曾作為舊中國的歷史呻吟,傾吐出中華民族遭受重壓下奮勇抗?fàn)幍囊庵拘穆暋K苍鳛樾轮袊臅r(shí)代吶喊,迸發(fā)出由優(yōu)秀的共產(chǎn)黨人所領(lǐng)導(dǎo)全體民眾蔑視任何艱難困苦不屈奮斗的理想呼聲。舊時(shí)代的“闖關(guān)東”使關(guān)東從一片原始的莽原與荒野變?yōu)槿祟惿畹募覉@;新時(shí)代的“闖關(guān)東”使關(guān)東從一派自然的貧窮與落后變?yōu)楣埠蛧墓まr(nóng)業(yè)生產(chǎn)基地。“闖關(guān)東”雖然已經(jīng)成為歷史,但它留在漫長歷史階段中沉重足音卻永遠(yuǎn)不會(huì)消失。正是“闖關(guān)東”這種偉大精神的感召,才使我們現(xiàn)代人將夢(mèng)想化為追求,又將追求化為現(xiàn)實(shí)。當(dāng)這種精神作為進(jìn)步意識(shí)浸透到地域群體每個(gè)具體成員的血液之中時(shí),那種強(qiáng)烈的教化作用所產(chǎn)生的精神力量將是無比巨大的,這是一種健康向上的進(jìn)步文化信仰,它塑造了地域群體最優(yōu)秀的文化品質(zhì)。“闖關(guān)東”社會(huì)移民現(xiàn)象已經(jīng)成為過去、成為故事,將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但“闖關(guān)東”的偉大精神卻將永世長存。“闖關(guān)東”歷史過程中表現(xiàn)出的那種中華民族特有的堅(jiān)強(qiáng)意志與英雄氣概,將如圣火永遠(yuǎn)照亮后人走向未來的征程。
[責(zé)任編輯:張振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