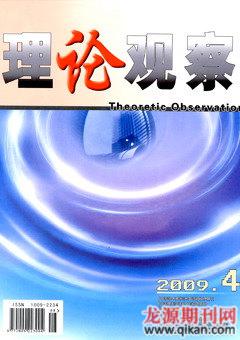赫爾德的全球治理思想探析
郭寅歌
[摘要]隨著冷戰的結束和全球化的發展,全球治理理論日益受到人們關注。本文從全球治理的理論框架和現實條件出發,詳細闡述了赫爾德關于全球治理的觀點——即一種以世界主義原則和世界主義制度為基礎的全球多層治理的世界主義民主,文章最后簡要對其觀點進行了評價。盡管赫爾德的全球治理觀點有些理想化,但它無疑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式。
[關鍵詞]赫爾德;世界主義原則;世界主義制度;全球多層治理;世界主義民主
[中圖分類號]D5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2234(2009)04—0060—03
隨著冷戰的結束和全球化的發展,全球治理理論日益受到人們關注。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國內外許多學者都對這一理論作了深入的研究,如:詹姆斯·羅斯諾的“在國際一國內邊疆上的治理”、羅伯特·吉爾平的霸權下的全球治理、羅伯特·基歐漢的理性制度治理理論、赫德利·布爾的“新中世紀主義”、哈特和內格里的“帝國”理論等等。戴維·赫爾德是其中一名著名的全球治理理論專家,他的世界主義全球治理觀點備受人們關注。赫爾德現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在民主理論、全球化理論和全球治理理論領域卓有建樹。本文從全球治理的理論框架和現實條件出發,詳細闡述了他的以世界主義原則和世界主義制度為基礎的全球多層治理的世界主義治理模式,文章的最后對其世界主義民主的觀點進行了評價。盡管赫爾德的全球治理觀點有些理想化,但它無疑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模式。
一、全球治理思想產生的理論基礎和時代背景
赫爾德早年從事民主理論研究,他的民主觀為其全球治理思想提供了總體的理論框架。赫爾德認為民主有三種基本形態:一、直接民主制或參與民主制,即公民直接介入公共事務的決策制度。這是民主的“原型”,發源于古代雅典;二、自由主義民主制或代議民主制,這種制度是經由選舉產生的“官員”在嚴格界定的地域內行使權力以“代表”公民的利益或主張并堅持“法治”;三、以一黨模式為基礎的民主制的變化形式,這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存在。西方多數國家實行的代議民主制是民主的主導形式,這一民主形式認為,在民族國家范圍內,政治決策者和政策接受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對稱和一致的關系,即在一國領土范圍內公民投票選舉對其負責任的決策者,而決策者向其領土內的人民輸出決策。然而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赫爾德認為政治權威不僅局限于國家層面,而是廣泛分布于全球、區域、區域間、國家、次國家甚至是個人層面,這種限制在一國范圍內的民主的效力已大不如從前。因此,赫爾德提出民主應該在地方、國家、區域和全球各個層次上得到深化,而這種民主就是世界主義民主。
赫爾德對全球化的研究又為其全球治理的思想提供了必要的現實依據。赫爾德認為全球化是場大變革,它是諸多因素作用的結果,包括技術變革、市場力量、意識形態及政治決策等等。全球化的過程充滿了變革和矛盾,因此,全球化既推動了社會的進步,也給社會帶來了一些負面的影響。(一)在法律方面,傳統認為國家是國際法的主體,而全球化的發展使民族國家不再是唯一的政治權威中心,全球范圍內出現了全球政治的新形式,包括民族國家、區域性組織、國際組織、非政府間組織、公民社會及跨國公司等等。這些全球政治的新形式使國家主權的效力衰退,對國際法的主體提出了挑戰。(二)在政治方面,現行的國際制度、國際組織的作用大大削弱了:(1)地區、國家和全球之間的差異使得各自為政,產生了誰應對全球性問題負責任的客觀問題;(2)現行的國際體制并不能為全球最重要的政府和非政府力量提供足夠的發言權;(3)由于缺乏一個超越國家的實體來管理全球公共物資的供應和使用,對緊迫的跨國問題找不到持續的解決辦法。(三)在經濟方面,生產、貿易、及金融的流動把民族國家卷入了全球體系之中。但不平等的國際分工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貿易的剪刀差越來越大,而金融的跨國流動也極大地改變了政策制訂者對成本和風險的認識。經濟的全球化使世界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民主的合法性受到質疑。(四)在安全方面,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產生了一系列的全球性問題,這些問題構成了非傳統安全的主要內容,如恐怖主義、全球變暖、環境惡化、資源枯竭、傳染性疾病、全球貧困、有組織犯罪等。這些日益嚴重的全球性問題使全球治理勢在必行。
二、世界主義民主的全球治理觀點
赫爾德在其民主理論和全球化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他的全球治理觀點——即一種以世界主義原則和世界主義制度為基礎的全球多層治理的世界主義民主的全球治理模式。
(一)世界主義原則
世界主義的思想源于古希臘的斯多葛學派,康德的“世界公民”思想發展了世界主義的觀點,近代貝茨、博格等人也對世界主義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在全球化時代,赫爾德認為世界主義可以理解為制定標準或劃定界限的基本原則。任何行為體——無論是政府、國家、或公民組織的代表——都不能違背這些原則。赫爾德認為在當代世界主義原則主要有八點:平等的價值和尊嚴;主觀能動性;個人責任和義務;同意原則;公共事務必須通過投票集體決策;包容性和兼容性原則;避免嚴重傷害、緩和緊急需求;可持續性。
這八個原則中,原則一、二、三確立了世界主義道德的基本原則,為每個人自由、平等地具有現實的參與性和自主性奠定了基礎。原則四、五、六確立了世界主義法律的基本原則,為所有層次政治權威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據。
(二)世界主義制度
世界主義民主建立在所有人都認同這八個原則之上,同時世界主義民主的實施還需要制度上的保障。赫爾德認為世界主義民主在制度上的要求是多種多樣的。這些要求包括從法律、政治到經濟、社會等許多方面,它們在不同的層次起作用。
世界主義法律要求區域、國家和地方的主權服從一個重疊的法律框架,在這個框架內,各個組織可以在不同的層次進行自我管理。法律世界主義在制度上的要求包括:擴展世界主義民主法律;重新制定包括政治、社會和經濟權力的更詳細的關于權利和義務的章程;建立一個相互聯系的全球法律體系,包括犯罪、商業和民法等;向國際刑事法院和國際平衡法庭提交仲裁;建立新的國際人權法庭,更深入地發展人權制度。
政治世界主義提倡區域和全球治理,主張建立一套政治組織和機制。政治世界主義的制度要求包括;多層次管理和分散權威;從地方到全球的民主論壇網絡;政治區域化;維護世界主義法律,建立一支有效的、負責的國際軍事力量。
經濟世界主義的目標是:在人類行為者特定選擇的背景下,為經濟競爭和合作創造公正的條件。經濟世界主義的制度要求包括:重構市場機制和經濟權利的領導區域;建立全球稅務機制;轉向經濟上最脆弱的資源,以保護和促進它們的效力。
文化世界主義是指在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命運和自主
選擇的生活方式之間協調的一種能力,它依賴于日益聯系的政治共同體中多數人的認同。文化世界主義的制度要求包括;承認政治共同體在社會、經濟和環境等不同領域中日益增強的相互聯系;在學習怎樣協調傳統文化的同時,要發展相互重疊的“集體命運”的觀點,要求集體解決地方、國家、區域和全球問題。
(三)全球多層治理
赫爾德的世界主義民主要建立“一種全球化的權威分散體系,一個受民主法律的約束和限制的、變化多樣的和重疊的權力中心體系”——即一種全球多層治理的模式。“多層”的含義主要指:參與全球政策制定的行為體不僅僅局限于國家,而且包括全球、區域、區域間、國家、次國家甚至是個人層面的所有行為體。這些層次之間不是一種等級關系,而是一種協作關系,每個層次都形成一個以公民自我管理為主導的自治共同體。因此,赫爾德主張在全球層次,要改革聯合國以關注那些關系壽命和生活機會的緊迫問題;在區域層次,要建立可行的區域機構,加強區域合作;在國家間層次,要增強政府間組織的有效性;在國家層次,要完善國內民主,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有效性;在個人層次,要增強公民社會的發言權,使之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在這種多層管理下,公民不僅僅是所在共同體的,而且是所有政治共同體的成員,他們就能打破地方或國家對其公民身份的限制,通過民主途徑在不同層次上參與那些影響其生活的決策。
同時,“多層”的含義還體現在:全球治理包括法律、政治、經濟、文化、安全等多個領域,每一個領域構成全球治理的一個層次,它們由各自的制度和機構管理,它們之間是一種功能性的關系。因此,赫爾德提出了世界主義治理的制度化來保障全球治理的順利進行。
以上為赫爾德的世界主義民主的主要觀點。我國學者俞可平認為全球治理的要素主要有五個:全球治理的價值、全球治理的規制、全球治理的主體或基本單元、全球治理的對象或客體以及全球治理的結果。根據這種解釋,在世界主義民主的治理模式中,全球治理的價值是世界主義原則,全球治理的規制是世界主義制度,全球治理的主體是多層權威,治理對象是政治、經濟、安全等各個層次,而治理的結果是要達到民主在各個層次深化。
三、世界主義民主的評價
首先,世界主義民主的全球治理觀點具有極強的理論解釋性。這種觀點是介于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問的中間道路,具有很大的包容性。現實主義注重權力和利益,他們強調民族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新自由主義注重國際制度和機制,他們強調國際制度和機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而赫爾德的全球治理觀點一方面既強調國家的權力,又看到了世界主義道德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既注重國際制度和機制,又不忽視其它層次上政治權威的作用。這種以法律、道德和權力共同發揮作用的民主制度無疑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模式。
第二、世界主義民主的模式介于聯邦制和邦聯制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實踐基礎。美國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世界主義國家的象征。美國這個大熔爐匯集了各個國家的人,他們雖持有不同價值觀,但他們卻在民族多元文化的基礎上實現著民主化;而歐洲國家在自愿的基礎上達成共識,這種協商式的民主與合作實際上是世界主義民主的典范。推而廣之,赫爾德的這種介于聯邦制和邦聯制之間的世界主義民主的道路也不是不可能的。
第三、世界主義民主的治理模式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長期以來,美國新自由主義極力向世界擴展的“華盛頓共識”是經濟全球化的一大動力,但是華盛頓共識的弊端卻日益凸顯出來:(一)華盛頓共識主張以市場為導向,推行貿易自由、資本流動自由,但正是這種自由阻礙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這些國家需要適當的保護性壁壘以獲得發展,拉美、俄羅斯的經濟就是“華盛頓共識”的悲劇;(二)華盛頓共識主張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縮小政府干預的范圍及力度,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恰恰反映出市場的過度自由以至于使政府失靈,有力地證明了政府干預的必要性,更說明了全球治理需要市場、國家及公民社會等各個層次的互動與合作。(三)華盛頓共識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為依托,是美國控制的工具,發展中國家在這兩個國際機制中的發言權微乎其微。在華盛頓共識遭到越來越多懷疑的今天,人們迫切需要一種新的公正、平等、可持續的發展戰略,迫切要求實現真正的民主。
第四,世界主義民主的治理模式還存在有利的現實條件。當今的全球化在廣度、強度、速度及影響上都史無前例:冷戰結束后,大量政府間組織、非政府間組織紛紛涌現,發展中國家地位和作用在不斷提升,世界市場已獲得很大力量,跨國公司正利用其不受國界約束的身份傳播著生產、消費觀念,新聞傳媒在利用全球化帶來的“時空壓縮”傳遞著另一個遙遠的地方的信息,公民社會也日益興起并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各國公民因全球性風險和危機產生了更多的認同……
然而,赫爾德的全球治理觀點在得到肯定的同時也存在不足之處。首先,盡管赫爾德明確指出了八點世界主義原則,但要讓所有人都認同這些原則、認同世界主義公民的身份還存在相當的難度。第二、赫爾德雖提出世界主義治理的制度化,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國際制度仍無法擺脫對大國的依附性。第三、赫爾德的“多層治理權威”是要把受決策影響的行為體全都納入到治理的過程中,但目前這些行為體還不能平等地發揮作用。然而從歷史的觀點來看,世界主義民主既是目標,也是手段,更是一個永不休止的過程。世界主義民主這項浩大的工程,需要一百年甚至幾百年的時間去實現,在這個過程中,民主在不斷深化,我們也將會一步步接近世界主義民主。
[參考文獻]
[1]戴維·赫爾德,民主與全球秩序——從現代國家到世界主義治理[M],胡偉,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
[2]戴維·赫爾德,全球化大變革——全球時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CM3,楊雪冬,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17
[3]戴維·赫爾德,安東尼·麥克格魯,全球化與反全球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125
[4]戴維·赫爾德,全球盟約——華盛頓共識與社會民主[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229
[5]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The GlobalTransformationsReader:anintroductionto theglobalization debate》,Polity Press,2003:523,524,525,526
[6]李剛,論赫爾德的全球治理思想[J],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236
[7]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論[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2,(01):25
[責任編輯:李允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