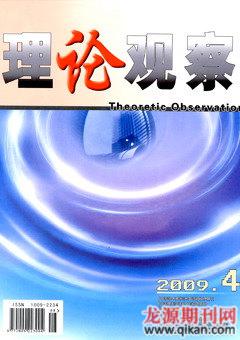從法律視角思考長期在外務工農民的住房問題
安桂君
[摘要]長期在外務工農民的生活重心已不在農村,農村的宅基地住房對他們來說意義已經不大。在城市,農民工是中低層收入者,購買商品房對他們是挑戰和難題。對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的申請又受到戶籍的限制,城鄉社會保障和戶籍改革尚需時日。為此,從法律的角度探索長期在外務工農民的住房難題不失為有益之嘗試。
[關鍵詞]法律視角;農村宅基地住房;經濟適用房;廉租房
[中圖分類號]D42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2234(2009)04—0106—02
一、概念理解
(一)農民工與長期在外務工的農民
“農民工是指戶籍身份還是農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從事非農產業,以工資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人員”。隨著工業化進程加快,農村和城市出現勞動力的富余和不足,產生了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農民離開土地成為“工人”,由此出現了“農民工”。“城市農民工的職業是工人,身份是農民。”
以浙江省為例,從勞動力外出方式看,舉家外出的情況越來越多。據抽樣調查資料顯示,2006年末,全省舉家在外的農村勞動力占全部鄉村勞動力的比重為6.8%,比上年增加了近2個百分點。這些人在城鎮有相對固定的工作和落腳點,與農村的聯系不再密切,也不愿再回到農村。長期在外務工的農民工不同于一般流動性強、在城鎮居無定所的農民工,但相同的是其社會地位低、經濟實力弱(下文稱農民工即為長期在外務工的農民)。
(二)宅基地住房
宅基地住房是以集體所有的宅基地為地基建造的房屋,唯集體組織的成員有權申請使用宅基地。《土地管理法》規定:“農村村民一戶只能擁有一處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積不得超過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的標準。…農村村民出賣、出租住房后,再申請宅基地的,不予批準。”第一,非集體成員無資格申請宅基地,宅基地住房流轉受限。第二;一戶只能有一處宅基地,面積受限。我國社會保障是城鄉二元的,宅基地住房對農民有社會保障的性質。城鎮居民享受另一套社會保障,故“城鎮居民不能購買農村的宅基地,國土資源管理部門不能為城鎮居民在農村購買和違法建設的住宅發放土地使用證”。另外,《土地管理法》規定了“因撤銷、遷移等原因而停止使用土地的,集體組織經批準可收回土地使用權”。
(三)城市住房——商品房、經濟適用房、廉租房
城市的住房體系有兩個部分,一是市場環境下的商品房買賣和租賃;二是社會保障性質下的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前者適合有經濟實力的群體,后者適合中低收入群體。
《經濟適用住房管理辦法》規定的經濟適用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優惠,限定建設標準、供應對象和銷售價格,具有保障性質的政策性質商品住房。第20條規定了申請購買和承租的條件:當地城鎮戶口或市、縣人民政府確定的對象;無房或現住房面積低于一定標準;家庭收入符合劃定的標準和其他。所以經濟適用房同樣具有社會保障功能,面向的群體是城鎮居民,以家庭為單位。
《城鎮最低收入家庭廉租房管理辦法》的立法目的之一是“為保障城鎮最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要”;其亦規定了申請的條件,即“符合市、縣人民政府規定住房困難的最低收入家庭”。同樣,廉租房也是社會保障功能的住房,以城鎮的低收入家庭為保障對象。
二、住房困境的提出
長期在外務工的農民長期在城鎮生活,尚未申請宅基地的,其可能放棄申請,但現實農民工即使空置房屋也會先建宅基地住房。已有宅基地住房的,因舉家遷移(非戶口上的遷移),宅基地住房并未發揮住房功能。此不利于后申請宅基地住房者的利益,也導致了農村建設用地的浪費。上文已提及《土地管理法》規定“因撤銷、遷移等原因而停止使用土地的”可收回宅基地使用權。法條未對“遷移”做出明確解釋,長期在外務工的農民的現有宅基地使用權可能面臨著被收回的風險。集體之內成員的宅基地面積有一定限制,集體之外的成員購買更受到法律和政策的限制,故宅基地住房的流轉受到限制,變現性差。
在城市,農民因經濟能力的限制,故從市場購買或租賃商品房有相當大的壓力。社會保障的城鄉二元結構導致農民工受戶籍的限制,不能享受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的住房保障帶來的好處。
農民工迫于生計不得不放棄宅基地住房,在城市卻又無法找到與其收入經濟狀況相適應的住房。單位在招聘中不解決住房者居多,即使有住房提供,也是條件極其惡劣。調查顯示:“北京市流動人口家庭住房內無廚房的占59.4%,炊事燃料使用煤炭的占38.1%,無洗澡設備的占82.3%,無廁所的占66.8%。”
無奈之下,農民工只能選擇離家近的周邊就業,一方面收入有限;另一方面勞動力供給也受到限制。我國沒有限制人口流動,但因住房困境的存在實際上造成了對遷移權的損害。農民工也常因“居無定所”身心終難穩定,帶來治安隱患。故正視和探索長期在外務工的農民的住房困境有重大意義。
三、困境的解決
(一)從農村宅基地住房角度解決
現有法律文件只規定了國有建設用地用于居住的使用權的使用期限最長為70年,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期屆滿自動續期,卻沒有對農村宅基地使用權期限作規定規定。筆者認為宅基地使用權可參照規定為70年,年限屆滿時自動續期。若繼承人在宅基地的使用期限內繼承房屋可繼續使用宅基地,但必須受每戶人家宅基地面積標準的限制。面積超過部分可以由集體組織對房屋補償后收回。或者由繼承人按面積按時間繳納使用費。若繼承人繼承的宅基地使用期屆滿的由集體組織對房屋作補償后收回或者繼承人繳納土地使用費。以宅基地使用期限的假設為基礎區分兩種情況。
1.尚未申請宅基地使用權建設住房的
農民工在尚不符合申請宅基地資格時外出,當符合條件時可申請宅基地并建造房屋。宅基地是一種對農民的社會保障,但因長期在外,該所謂保障事實并未有發揮作用。故可考慮將資格權利現實化:宅基地所有者——集體組織以70年的宅基地使用權為基礎,根據其針對該幅土地的使用權轉讓所得費用一次性付給有資格但放棄申請的農民工。農民工可以用這筆資金用作城市置房所用。技術上,集體組織可用轉讓該宅基地使用權的所得款項建立一個專門的基金并運作。集體組織需要農民工城市常住證明,集體組織對放棄申請的農民工進行充分告知:告知宅基地使用權的社會保障性質,充分建議農民工在動用所得資金時應有充分的打算。集體組織亦可為農民工開一個類似于住房公積金的保障帳戶定期發放資金。(農民工工作的企業單位有住房公積金安排的須提供證明并直接將該筆資金的轉賬。)
2.已申請宅基地使用權建房的
有些農民工在外出打工時已在農村有宅基地住房,但卻是人去房空。因此,可考慮宅基地住房的轉讓。轉讓有兩種情況,一是集體組織內部轉讓;二是集體組織外部轉讓。
第一,集體內部轉讓。其可行性在于:一是受讓方是集體內成員,故身份不存在障礙;二是農民工就宅基地上的現有建筑享有物權,可自行轉讓。但自主流轉會導致受讓方累計占用宅基地面積大大超過法律法規規定的每戶宅基地面積標準,而真正需要宅基地的集體組織成員卻得不到土地。故可考慮通過集體組織收回然后再做安排。但前提是農民工主動提出集體組織收回土地,集體組織根據房屋和宅基地剩余使用年限做一定得補償。同樣,集體組織需要對放棄宅基地住房的農民工予以說明和建議。
第二,集體外的流轉。現有制度下集體外流轉是被禁止的。但我們需正視農村中的小產權房的問題。筆者認為,集體外的成員對于房屋的受讓是沒有問題的。有問題的是其是不是會減少集體內部成員得到宅基地使用權的機會。因農村人口的外流,集體內對宅基地的需求減少,集體外成員產生若干要求,這是現實存在的供求關系。基于上文宅基地使用權的使用期限的設想,集體外的成員須向集體組織繳納剩余的宅基地土地權的使用費。集體組織將收取的使用費納入專用基金。使用年限屆滿時集體組織可民主表決是否收回該宅基地,決定收回的只要就房屋作價補償即可以。
集體外流轉另一個需要考慮的是發生繼承時集體外成員成為繼承人的問題。繼承有法定繼承和意定繼承,還有遺贈。因遺贈可能涉及到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可能,所以可以只局限于有撫養協議的受遺贈人。繼承權和受遺贈權不同于一般流轉。宅基地使用權的保障性質具有身份因素,故同住的集體外繼承人可繼續使用宅基地別無他礙。若是非同住繼承人則其只能在剩余使用期限內使用宅基地。因為房屋的翻建涉及到期限屆滿后集體決定收回該土地時對房屋的補償,故繼承人不能隨意對房屋拆除重建。宅基地使用權屆滿的,集體內成員可以自動續期,集體外成員的需要集體組織決定收回與否。
(二)從城市住房角度解決
1.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
商品房的租賃和買賣對農民工來說很困難,但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受農民工戶籍的限制。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適用面向的群體也有區別,同時放開尚需時日,可否從廉租房下手?在優先保障城鎮居民前提下,對已經和集體組織簽了放棄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的農民工可以憑常住證明(如在單位工作5年以上或者在城市經商常住5年以上且年營業額達到一定額度)、收人證明和放棄宅基地使用權的證明申請廉租房。待時機成熟時,可以逐步對經濟適用房也做類似的安排。
2.用人單位的住房問題和農民工住房保障款的繳納
浙江省出臺的《關于加快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實施意見》,強調了用工單位的責任:“用工單位要向農民工提供符合基本衛生和安全條件的居住場所;要求農民工自行解決居住的,要在勞動合同中明示”在出現“民工荒”的地方,可要求企業按招錄員工的數量提供一定比例的住房。提供住房的資金來源一部分由企業提供,一部分由企業的住房公積金提供,一部分有政府補貼。(沒有企業單位的農民工可以參考關于農村宅基地使用涉及的做法。)
[責任編輯:唐守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