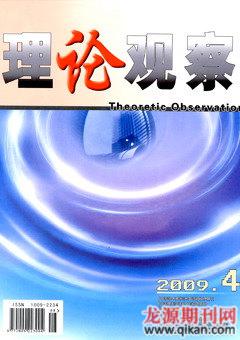屈騷批評與漢代儒道思想
王凱波
[摘要]漢代的屈騷批評使先秦古籍中不見記載的屈原登上了歷史的舞臺,確立了屈騷的經典地位及屈騷精神的基本品格。而儒道思想作為通貫漢代的兩大學術思想和社會思潮,必然要作用于漢代這場關于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評,與此相應屈騷批評的發展又充分顯示了漢代儒道兩家思想動態的演變過程。
[關鍵詞]屈騷批評;儒道思想;嬗變
[中圖分類號]1206.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2234(2009)04—0132—02
儒道思想是通貫漢代的兩大學術思想和社會思潮,漢代關于屈騷的批評也正是在儒道思想的支配作用下而進行的。正是看到二者之間的關聯,李澤厚、劉綱紀先生在《中國美學史》中指出:“圍繞著對屈原及其《離騷》的評價,可以看出漢代美學思想的變遷”。漢代屈騷批評的發展充分顯示了儒道兩種審美意識絀補兼綜的過程。
對漢代屈騷批評的過程,以往學者多按劉勰在《文心雕龍·辨騷》中對漢代屈騷批評的簡述,基本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西漢初年到西漢中期,以賈誼、劉安、司馬遷為代表,他們對屈騷是持肯定態度,并給予了崇高評價。第二個階段是從西漢末年到東漢前期,主要代表是揚雄和班固,對以劉安、司馬遷為代表的第一階段評價提出了不同意見,對屈原及其作品進行了貶斥和批評。第三階段以王逸為代表,通過對班固的駁斥而給予屈騷以積極的重新的肯定。然而若從儒道思想的演變與屈騷批評的發展關系的角度去研究,我們亦可以把其劃分成以下三個階段。
一
第一個階段為西漢初年,這一時期學術思想以“君臣俱欲無為”的道家(黃老)為主體,在意識形態上處于主導地位的黃老思想也必然要影響此期的屈騷評價。賈誼拉開了漢代評屈的序幕。他感嘆自己在政治遭遇上與屈原的相似。故作《吊屈原賦》,傷屈亦自傷。他在這篇作品中說“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風伏竄兮,鴟梟翱翔。闖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對屈原之正道直行而遭貶的遭遇深表同情,對屈原捐介剛直的人格表示敬慕,并用一系列對比鮮明的比喻來揭露批判造成屈原不幸的那個世道。但另一方面,賈誼對屈原眷懷故國、守志不移思想行為也表現出了不解和責難,他認為屈原可以“隱處”、“自藏”、“遠離濁世”,“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這一批評,顯而易見,是在漢初黃老思想的作用下,所表現出的道家全身遠害、消極避世的思想觀念。故蘇軾《賈誼論》云:“觀其過湘,為賦以吊屈原,縈紆郁悶,超然有遠舉之志。”
此一時期對屈騷認識和評價的還有嚴忌的《哀時命》。王逸《楚辭章句》中認為此作傷悼屈原,故編入《楚辭》專書之中,今觀此賦,并不專門是為傷悼屈原而作,而主要是抒發賢者不遇于時的傷感和憤懣,但可以反映出這一歷史時期漢代士人對屈騷的認識和評價。“鸞鳳翔于蒼云兮,故增繳而不能加。蛟龍潛于旋淵兮,身不掛于罔羅。知貪餌而近死兮,不如下游乎清波。寧幽隱以遠禍兮,孰侵辱之可為?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沉于汨羅。雖體解其不變兮,豈忠信之可化?”此賦和賈誼賦一樣,表達的主要是明哲之士應遠濁世而善自處的思想。
以上這些評論屈騷的作品,都以賦的藝術形式呈現給讀者,聲情并茂,并融入了作者個人境遇的自述,充分反映了西漢初年盛行的黃老道家思想對此一時期屈騷批評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正如許結在《漢代文學思想史》中所說賈誼、嚴忌的辭賦“為楚文化精神與黃老道家思想在文學領域的有機結合,其‘本道家之言的自然心態與特殊的抒情形式,構成了漢初黃老道家文藝觀的重要方面。”
二
第二個階段為西漢中后期,在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儒學作為國家政治指導思想開始占據著主導地位,然而思想領域的更替和轉化是一個緩慢演變的過程,此時漢初的道家思想與武帝所倡導的儒學還處于一種共存互補的狀態,而這一狀態的發展趨勢是由以道為主的本道兼儒發展到以儒為主的本儒兼道。而此時漢代士人屈騷批評所呈現出的特點與這種變化相和,反映著由道而儒的轉變。
據目前史料記載,劉安是第一個對屈原及其作品的思想和藝術作了全面而深刻評價的人,他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主要是從道家思想出發的,但在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政治文化背景下,奉召而作的《離騷傳》也同時表現出了儒家思想的影響。“濯淖于濯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這顯然是與道家的處世態度一致的。劉安正是從道家自持高潔,對污濁現實的棄絕態度這個角度,贊美屈原之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但同時,我們也看到在其評價中所反映出的儒家思想。“《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把屈原的作品比附儒家經典。以儒家詩教作為評判標準,既是對武帝的重儒思想的應和,也是其本道兼儒思想的體現。
司馬遷把劉安評屈騷的話寫進《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并表達了對屈原遭遇的同情,但是對于屈原最后所選擇的人生道路表達了與賈誼相類似的看法,“太史公日: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對其作品的評價,他在劉安評價的基礎上又作了重要的發揮,更加突出了《離騷》“怨”的特點,這與他的“發憤著書”說是完全一致的。但另一方面,司馬遷對屈騷的評價也以儒家詩教為準則,強調屈騷的諷諫精神,“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表現了儒道結合的傾向,這與他“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的思想是一致的。
西漢末年,在儒家思想日益深入人心,逐漸內化為士人思想品格之后,揚雄對屈騷的評價與之前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在《反離騷》中,他雖然也表達了對屈原的敬仰、惋惜之情,對屈原的人品才能仍極為推崇,把屈原比之為“鳳皇”“神龍”“驊騮”,用“芳酷烈”“揚之芳苓”來狀屈原的品德。但是揚雄對屈原還是發出了批評,“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從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角度來對屈原加以指責,并認為屈原為人缺乏儒家的“明智”,不能明哲保身,他不應該對統治階級采取決絕態度,自沉汨羅江。此外,在《反離騷》中又認為其不能隱德,不能守道自保,責怪屈原是“棄由聃之所珍兮,礁彭咸之所遺。”揚雄這種隱德自珍、全身遠禍的思想,又是道家的清靜無為、守道保身思想的反映。揚雄對其作品的評價同樣也充滿了矛盾,他從儒家思想的角度評價屈騷,既肯定屈原作品“體同風雅”,符合儒家標準,具有諷諫精神。但同時也對屈騷提出“過以浮,蹈云天”的批評。但揚雄又認為“屈原文過相如”,“賦莫深于《離騷》”,用“深”字
概括屈騷的特點,又是其道家思想的反映。從上我們看到了揚雄評價屈騷的矛盾性這是與其思想存在雙重主旋律的矛盾交互相應和的,但從揚雄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中我們可以看到揚雄徘徊與儒道之間時,始終堅守著儒家的根基。
從劉安到司馬遷再到揚雄,都是從儒道的立場來評論屈騷的,但漢代士人對屈騷的評價還是可以看出這期間儒道思想對這一時期影響的細微變化,即從以道為主的本道兼儒發展到以儒為主的本儒兼道。從中我們看到了文學思想發展從量變到質變的痕跡。
三
第三個階段為東漢時期,西漢儒道思想經激烈沖突至東漢終歸于“獨尊儒術”的完成,道家思想作為附屬被潛移于新儒體系。而此時對屈騷的評價也由儒道兼用而演化成完全以儒家思想作為評判標準,無論是班固父子、還是王充、梁竦、王逸,無論是持肯定觀點,還是持否定觀點,雙方都以儒家思想作為立論的根據,而此期也正是對屈原及其作品評價最為激烈的時期。其中以班固和王逸的論爭異常激烈,成為屈騷批評的高潮。
班固對屈騷的批評承接揚雄,同樣也是處于矛盾之中。但不同的是,他則完全以儒家思想作為自己評判的標準。對于屈原其人,他一面評價其“忠”“賢”,而另一面又指責其“露才揚己”“非明智之器”“”對屈原的“為人”進行非議。其思想不僅來源于揚雄,也與其父是一致的,班彪《悼離騷》:“夫華植之有零蒙,故陰陽之度也;圣哲之有窮達,亦命之有故也。惟達人進止得時,行以遂伸,否則詘而坼蠖,體龍蛇以幽潛。”同樣,班固對屈原的作品,一方面給予了否定,認為屈原《離騷》中描寫的乘虬龍至昆侖、懸圃,以及叩帝閽,求宓妃等都是“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另一方面在《離騷贊序》中說屈原作《騷》的原因有二:一是“忠而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二是“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在《漢書》中將屈原作《離騷》與《小弁》之詩作相提并論,肯定其義同詩雅,有側隱古詩之義,具有怨刺諷諫的精神。即使在否定屈原及其作的《楚辭序》中,他也毫不保留的充分肯定了屈作,“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
王逸是漢代楚辭集大成者,他在《楚辭章句》中以肯定劉安的《離騷傳》駁斥班固對屈騷的批評為基點,對屈原及其作品給予了全面系統而極高的評價,但其立論根據卻與劉安相異與班固相同。他以“忠正”“伏節”為宗,標舉孔子“危言危行”“殺身以成仁”的思想作為評價屈原思想行為的總綱,闡釋忠信名節的“人臣之義”。以此反對班固的“全命避害”的思想。他高度贊揚屈原的人格品德“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對屈原作品的評價,則針對班固的“虛無之語”“皆法度之政”“非經義所載”的批評,從屈騷立意到取興作了符合儒家經典的比附。在論及屈原的創作動機時指出,屈原“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決不象班固所說,屈原是為了“露才揚已”而作《騷》。王逸認為屈原的人品和作品均為人敬仰,影響深遠,不僅“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而且“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由此可見。西漢中后期的由以道為主的本道兼儒發展到以儒為主的本儒兼道評屈騷趨勢的發展,標示著在東漢儒家思想獨尊局面的真正意義上的確立。東漢儒家思想滲入人心的狀況在屈騷評價中,展露無疑,無論是班固的否定,還是王逸的肯定都是以儒家思想作為評價的唯一標準。
縱觀兩漢關于屈騷的評價,可以演繹出這樣的基本線索,屈騷評論受制于漢代的整個思想領域的變遷,同時也反映了兩漢文學思想在四百年漫長的時間段里所經歷的一個不斷發展、演變的過程,即是由西漢初的道家文學思想占主導地位,轉而在武帝罷黜百家之后進人了儒道互補的階段,然而在這一階段中又有分期,前一階段是以道家為主的儒道共存(劉安、司馬遷),而后期則是以儒家為主的儒道互補(揚雄),這一細微的前后轉變也標示著進人東漢之后,以儒家文學思想為主的確立,此期的文學思想可以說是“百家騰躍,終入環內”。這一動態的嬗變過程糾正了以往對漢代文學思想過多關注儒家而易導致的偏頗,從漢人對屈騷評論可以清晰看見漢代儒道思想對其的影響及儒道思想動態的演變過程。
L參考文獻]
[1][2][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李誠,熊良智,楚辭評論集覽[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1,1,2,2,3~4,6,7,8,9,7,17,11,17,17,23,23,23,24
[3]張峰屹,西漢文學思想史[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l:50
[4]楚辭[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257
[5]許結,漢代文學思想史[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39
[責任編輯:李姝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