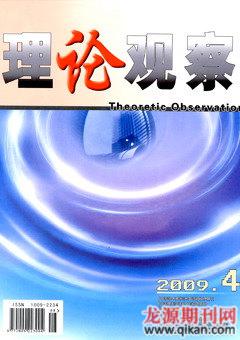人身傷害賠償案件中的“城鎮居民”如何認定
張 澍
[中圖分類號]D923.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2234(2009)04—0155—01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傷害解釋》)從頒布到實施的過程中,對正確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傷害解釋》對城鎮居民的定義缺乏統一的標準,給司法實踐帶來了很多不便。本文擬簡要分析當前的理論爭議和司法實踐的做法,并對“城鎮居民”的認定提出自己的思考。
2004年5月份頒布的《傷害解釋》中在確定人身傷害的賠償上,區分了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兩種的不同的標準。按照這兩種標準進行計算兩者之間的金額差別巨大。比如殘疾傷害賠償金一項如果以黑龍江省為例,根據最新頒布的《2008年度黑龍江省分行業在崗職工平均工資》,2008年黑龍江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1581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4856元,如果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同時有一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被撞成一級傷殘,那么城鎮居民的賠償金為231620元,而農村居民的賠償金為97120元,兩者之間的差別竟有近14萬元之多,且隨著我國城鎮和農村差距的進一步擴大這種差距將會越來越大,“同命不同價”這種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現象引起了學者的廣泛注。
由于這種差距的存在,少數人為了在賠償上享受到與城鎮居民真正一樣的事故賠償待遇,一些事實上確為農村居民的權利人利用法律實體及程序上存在的漏洞和缺陷,在一些律師、法律工作者等訴訟代理人的教唆和指示下,利用親戚、朋友關系等不正當渠道公然違反法律弄虛作假,偽造或捏造符合城鎮居民性質的證據材料,以期獲取非法賠償利益,這也給司法界造成了混亂。
對如何給“城鎮居民”下一個準確的定義,不但目前理論界存在分歧,而且在司法實踐中,對城鎮居民的認定也存在著三種不同的標準:一種認為,在中國人權平等是實質上的平等,農村和城鎮居民的差距是客觀存在的,法律所追求的也是一種實質意義上的平等,因而直接采用戶籍管理的相關標準,這種采用一刀切的辦法遭到了學者的批評;第二種以經常居住地結合固定收入適用相關標準,這種做法直接來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于2006年4月在答復四川省高院《經常居住在城鎮的農村居民因交通事故傷亡如何計算賠償費用的復函》中的規定,此規定現在成了絕大多數法院適用的標準,關于這方面的論述將在下文中予以說明;第三種是采取的以經常居住地結合固定收入適用相關標準,這種折衷的辦法看是很完善但對另外兩種的不足處沒有予以解決。
就目前人身損害案件中關于“城鎮居民”的認定在司法實踐中的做法,筆者認為采用第一種做法雖然合法但是嚴重背離事實,無法顧及個案受害人現實的收入差異,弊遠大于利,且目前有很多被依法征用土地但尚未辦理戶口變更登記的農村居民,他們的權利無法得到保障。而采用第二種做法雖然在形式上這種方式容易為多數人理解接受,但問題是經常居住地如何區分城、鄉,以及固定收入需要符合怎樣的標準。就拿固定收入這一項來說吧,什么樣的標準才符合擁有固定收入目前在司法界也采用不同的解釋。有的地方認為是指擁有固定的職業并擁有合法固定的收入來源,而有的地方認為固定收入的外在表現就是生活的相對穩定,有自己的勞動力之運作,其構成要件上并非要求職業之固定性,只要受害者在城鎮依靠自己的勞動取得相對穩定的合法收入能夠維系自身生活的,應視為“有固定收入”。由于這種解釋上的不同觀點給司法審判在實際中的操作帶來了很大的不便。比如在黑龍江地區一些鄉鎮被劃分為街道辦事處,居住環境根本沒有發生任何變化,是否就發生城、鄉更替?看似合理的方式在實踐中操作難度太大。若采用第三種往往可以較為靈活的適應具體問題,但在這里同樣行不通,理由不再贅述。
綜上,筆者認為在認定“城鎮居民”時應該從立法的目的的角度出發結合受害人的生活場所,生活環境等以及實際操作等因素來綜合考慮。死亡賠償金是賠償義務人對受害人之法定繼承人因受害人死亡而遭受的未來可繼承的受害人的收入損失的賠償責任,對于受害人的賠償特別是對受害人戶口在農村,但經常居住地在城鎮的,在確定死亡賠償金標準時,應結合受害人在城鎮生活的時間、背景、勞動能力、年收入狀況等因素綜合認定,而不是局限于對“固定收入”的字面理解。事實上,社會生活中很多長期生活在城鎮的人,從事著自由商業或以零散工的形式維持生計,但從整體判斷其每年均有一定的收入,因此如果對“固定收入”作機械理解,顯然不能真正實現死亡賠償金填補“收入損失”的價值理念。對于殘疾賠償金,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在《傷害解釋》中的相關可看出殘疾賠償金是對受害人因為在交通事故中身體受到損失而造成的勞動能力減弱導致未來收入減少的一種補償,對于這部分賠償金額與受害人當時居住、工作、生活環境以及受害人的年齡、實際勞動力損害的程度有關,在司法實踐中應該從受害人的實際情況出發,綜合考慮各方面的因素。
總之,筆者認為最高人民法院應就如何認定“城鎮居“民”提出一個明確的標準。如果因為政治經濟等原因而不好界定詞語,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針對司法實踐提出指導性的意見,各省依法進行相關規定,以便與于法官量裁。當然在制訂標準時應該從立法的目的出發結合實際情況進行,這樣更有利于實現社會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