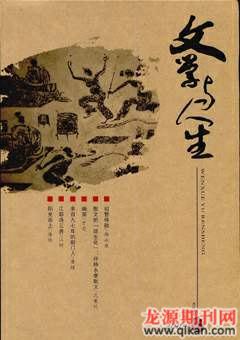散文的“陌生化”
沈榮均
需要承認,漢語散文寫作在經歷“新散文”大規模拒絕體制寫作的努力后,大量“美化鄉村”、“美化庸常”的“偽抒情”和“泛文化泡沫”的存在,無時無刻不在提醒我們——現在仍然沒有步出“公共寫作時代”。鄉村正在向自認為正確的方向前進。城市化正在制造無差別世界。這很可怕。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作家,需要為此保留一份清醒。“文學的作用不是為了消除差異,而是為了突出差異”,這便是拒絕“公共寫作”,潔身自好的“楊永康式”氣質——陌生化、差異性、我行我素甚至為所欲為。“新散文”之后,一些作家妥協了(“被主流招安”),一些作家被拒絕(“向民間轉移”)。楊永康屬于被拒絕的那一部分——自覺與“公共寫作”劃清界限。對于這樣的作家,我表示景仰。對于這樣的散文,我保持期待。
讀楊永康的散文,我是以后退的思維進行的,從《信仰史》(《再往前走》代后記)開始。在這篇可看作楊永康散文信仰自我清算的文章里,始終流淌著一股孤獨悲壯的血液——散文的血液——拒絕“公共寫作”的決絕姿態以及對散文前景的擔憂。楊永康顯然是個散文的冒險主義者。因為冒險,制造“陌生”;因為“陌生”,付出代價。于是,有評論家一面對他的冒險氣質大加褒揚,一面又對其冒著犧牲換來的“陌生”不以為然。對于散文,評論家免不了易犯一廂情愿的錯誤,希望對象能按照自己的經驗出現。這會不會導致某種誤導——從一種體制進入另一種體制?作家的想法往往不是這樣。謝有順認為,散文應“寫給身邊熟悉的人”;楊永康則認為,“作家寫作的終極努力和原初動力來自作家本身”,甚至干脆發出了“公共寫作時代”的散文“完全依賴于個人的覺醒和發現”的感慨。
應該說,《再往前走》在給評論家制造麻煩的同時,也給散文制造了麻煩。克羅奇說,“文學本身是個錯誤”。面對現代化的無序、不可預見和無所適從,楊永康保持了警惕,“我們無法接受這種亂,卻無法阻擋這種亂”。這與我的理解是一致的。現代化制造了諸多困惑,比如“誤會”,比如“偶然”,比如“錯位”……于此背景下的散文,不得不放棄原來諸多崇高、宏大、美好的“想法”,低下目光來關照矮小、細部,以及堅硬、后退、背離和駁雜等。這本是世界的秩序常態,作家要做的不是整理、規勸、修正和提純,而是讓它呈現出曾被大多數忽視的本來“陌生”。
——“誤會”與“偶然”。現實之所以陌生,是因為世界變化太快,而時間以及緊隨其后的我們“慢了”。好不容易跟上來,忽然發現,等在我們前面的是更多的誤會和偶然,無半點嗔怪,還溫情脈脈——熟悉的漸漸遠去,陌生的愈加澄明。《找不見的人》中,羅圈腿的黃書郎演洪常青是個誤會,黃書郎的槍走火傷人是個誤會,最后“找不見的人”葛老十自己開槍了結這場誤會是更大的誤會!誤會的意義在于,它以幽默的力量,成功抵御了冷漠和麻木,放大了潛在于心靈深處某種溫暖的東西,以此賦予我們重拾未來的信心。“外面的世界是太吵,外面的世界是太鬧。我還是希望它們的生活中能出現一些美好的暈眩與一些美好的意外。”(《世界上最小的口袋》)當小偷把手伸過去的時候,一聲清脆的咳嗽,小偷只好把手縮回;當“我”胡亂猜測的時候,又發出一聲同樣的咳嗽;當“我”不由自主地把手伸進口袋,“我”意外地摸到了一朵玫瑰……“我真想告訴杰西:走著走著花就開了。四月的花。我們在花下等啊等,一會兒就是一大群。”(《走著走著花就開了》)許多的意外,都是小人物的意外,雖然僅是“過渡、短暫和偶然”,但它卻通過放大“小”的“誤會”與“偶然”,謀劃了某種“大”的“本質”——極度彰顯小人物的生命體驗。韓國的金圣坤認為,“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本質差別在于前者到頭來還是相信恢復總體性——把秩序與和諧賦予片斷性——和頓悟的一瞬”,而“后現代派,以對矛盾、不連貫、無所作為和偶然性的欣賞來代替對總體的追求,以贊美過去的滑稽模仿的形態。”照此觀點,對比楊永康筆下的“誤會”與“偶然”,我們似乎已察覺到楊永康散文的某種追求。
——“錯位”與“間離”。《再往前走》、《陰影里舞蹈輕》、《生命中的細節和秘密》、《天國里的雜質和曖昧》、《愛整個世界及你的左肩》……還有很多。這是一組洋溢著濃郁的“楊永康式”氣質的散文。很“陌生”,很難讀,就像閱讀那些大師一樣難讀。要“深入”大師,僅僅靠閱讀難以實現。楊永康的高明在于,他不負責消除讀者和大師之間的閱讀障礙,但他可以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提供另一種理解,甚至不惜“把兩個互不相干的截然不同的東西放在一起”。乍一看,好像有些突兀甚至不可理喻,但你不得不承認這樣設置帶來的意外力量——“有沖突就有震撼”——“錯位”與“間離”最后制造了“陌生化”。“即便是聰明的驢子,也無法讓這個可疑的季節、細碎的季節‘站住。即便比我聰明的母豬和葡萄,也無法讓這個可疑的季節、細碎的季節‘站住。但我們可以短暫地回到海鷗相館和童年。”(《可疑的細碎的》)如果事物不能隨著我們的愿望而改變,那么我們能做到的也只是換個角度去看了。換個角度的效果是,“我”和對象彼此成為對面的“另一個”,雖感“陌生”,但互為風景。
——“鏡像”與“符號”。如果說“鏡像”還保留現實僅存的模糊和混沌狀,“零零碎碎,未作出總體歸納之傾向”(麥克黑爾),那么“符號”,最終完成了楊永康散文的“陌生化”——在虛實相間與真偽并行中,文本與世界、藝術與生活以極端的“短路”方式實現對接。對此,楊永康頗為得意,“我慣用的伎倆是,用一個真實的東西(現實物景)證實另一個并不真實的東西(非現實物景或者夢),這樣做的好處是,你根本沒法分清哪個是真實的東西,哪個是不真實的東西,結果都成了真實。”我的理解,這樣做的本質是一次充滿冒險的“證偽”過程(制造識別的混亂)。還好,文學不是邏輯,散文的“證偽”同樣具有“陌生化”的力量。“現代主義的必然趨勢是象征性,一方面涉及某一具體的情形,另一方面又通過象征來反映更廣泛的意義。”(杰姆遜)在楊永康看來,這種象征性似乎就是“作家與事物之間肯定存在一個秘密通道”——從“鏡像”到“符號”(從捕捉現實困惑到把問題抽象)。“鏡像”(畫面感、流動性、記憶片段、毫無拘泥的夢境、時空轉換,以及那種陌生的、奇特的甚至是想象力也難以觸及的世界等等)在時間上,是不完整的片段,保存了作家的記憶。文學不解決問題,但揭示問題;散文不解決問題,但預示生活。而生活尤為欠缺“形式”。這個形式就是隱藏在日常生活經驗當中的某種秘而不宣的符號,只不過我們沒有“看見”罷了,散文的目的就是把它揭示出來。《睡吧,床》、《露在外面,許多年》、《千萬別碰上伊萬》中,大師眼里的床、露在外面的屁股、二丫碰上的那個伊萬,這些“鏡像”并不“清晰”,但通過作家的抽象,人與床的問題、屁股問題、伊萬問題,等等,儼然成為某種“符號”(正是生活所欠缺的“形式”)。現實的“形式”不是單數,世界的“形式”也不是單數。在楊永康的作品里,我們時常看到界線隱退、空間消失,問題和沖突交疊,秘而不宣,卻分明昭然若揭。如果說,散文一定有“意義”,這就是楊永康散文的“意義”所在。
因為自身身份、經歷、處境、生活方式、趣味、個人經驗、價值判斷等因素,楊永康的散文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顯著的“楊永康式”烙印,這既是楊永康散文需要警惕的問題,也是楊永康保持敘述定力的優勢。當代漢語散文作家要走得更遠,恐怕需要在每次提筆的時候,像楊永康一樣自覺地去思考身邊那些“陌生的熟悉”(在別人看來,接近于孩子天真無邪的“撒謊”),而不是抱以漠視,或者對日常的經驗盲目樂觀。生活中,我們往往毫無成功、喜悅、幸福可言。那些津津樂道于各種感悟、經驗的,與散文無關。散文本質是“小”的——通過敘述小個體形形色色的遭遇,揭示我們共同的命運。從這一點講,我有信心對楊永康的散文前途一如既往保持閱讀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