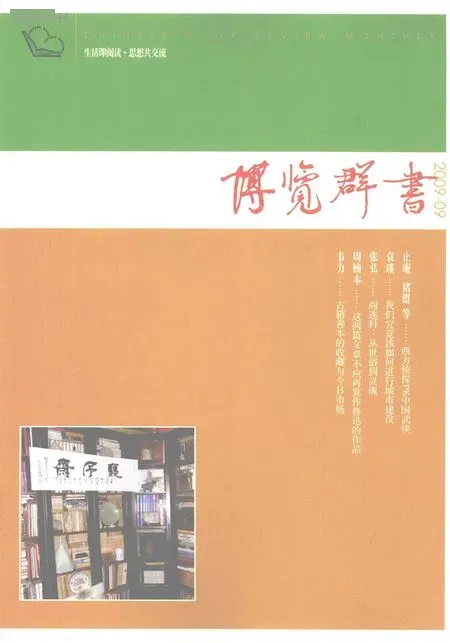張世英:復返其根 會通創新
趙 濤
著名哲學家張世英早年以對德國古典哲學的研究享譽海內外,尤其是他對黑格爾哲學的精湛研究,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國內學人。值得關注的是,及至晚年,張先生卻回復到關于中國古典哲學的研究上,結合對西方現當代哲學的學習與思考,逐漸形成并系統地提出了新“天人合一”、“萬有相通”這一可以“與熊、馮、金的體系比肩”的具有原創性的哲學體系。
復返其根,會通中西。在新體系的觀照下,年近九秩的張先生再次煥發出驚人而旺盛的學術生命力,談虛擬,論想象,言境界,說希望,以不能自己的創造激情,連續出版了《天人之際——中西哲學的困惑與選擇》、《進入澄明之境——哲學的新方向》、《哲學導論》、《新哲學講演錄》、《境界與文化——成人之道》等一系列詩史思結合的學術精品。
一
有人說:“哲學是反體系的。”但黑格爾認為:“哲學若沒有體系,就不能成為科學。沒有體系的哲學理論,只能表示個人主觀的特殊心情,它的內容必定是帶有偶然性的。”新“天人合一”、“萬有相通”哲學體系的提出,既是中國傳統哲學智慧的當代開顯,無形中又契合了西方后現代哲學轉向的內蘊與大勢,為當前漸趨碎片化的理論思考提供了一個綱舉目張、渾然有體的參考鏡像,傳統的本體論、認識論、美學、倫理學、歷史觀等在新哲學體系的燭照下獲得了全新的闡釋,帶給廣大讀者耳目一新、圓融無礙的澄明之感。
由是觀之,張先生的《歸途——我的哲學生涯》一書,作為個人自傳性文本,就具有獨特的學術價值。它不僅是了解張先生生平及其半個多世紀學術心路歷程的最佳窗口,也是直接把握其學術思想內核,以便較為快速地進入其哲學新體系的理想指南。張先生以“歸途”二字來概括其哲學生涯,固然如其所描述的,“就像我的哲學足跡,雖然遍歷中西古今,最終還是向往少年時期所迷戀的老莊家園一樣”,是個人回歸自我精神家園的真實寫照,但這一回歸及其晚年所發生的重大學術轉向,對當代中國哲學研究不無借鑒與啟示意義。
這部篇幅不長的自傳由正文和附錄兩大部分組成。正文部分包括16篇回憶文章,附錄部分則收錄了張先生不同時期發表的相關隨筆、代表性論文和若干記者訪談資料。
在回憶文章中,張先生以清晰簡明的筆墨,生動地講述了他從啟蒙階段以至西南聯大求學期間的問道生涯,對他60年來的學術發展道路做出了嚴格的自我解剖和深刻反思,特別是對改革開放近30年學術轉型的心路歷程作出了說明。
和許多會通中西的學術大家一樣,童年及青少年時期的張世英熟讀中國典籍文獻,自小就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進入西南聯大后,張先生先學經濟,后出于對宇宙人生沉思默想的偏好,也由于受哲學家賀麟的巨大影響,轉入哲學系,在馮友蘭、賀麟、湯用彤、馮文潛、吳宓、金岳霖、聞一多等諸多學術大師的指引下,踏上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上下求索之路。
是時的西南聯大名家薈萃。在張先生的筆下,每一位聯大名師無不才情充沛、性格迥異、風采斐然。賀麟以“荷花出污泥而不染”詮釋黑格爾的“絕對精神”,解說辯證法,通俗而新奇;講授英國詩歌的吳宓,卻重中國經典,給學生推薦的參考書大多是關于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邏輯的沈有鼎和專治文學的聞一多同開“易經”課,卻還像學生一樣彼此旁聽對方的課程,課后兩人常比肩而談,進行嚴肅的學術爭論。前輩學者由博返約的大家氣象、會通中西的世界眼光、崇尚學術的名士風范無疑對張先生日后的治學態度及治學方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張先生當時看一些講中國哲學史的書,常常覺得理論分析少,不甚了了,并因此而歸罪于中國人的傳統思維方式:籠統、混沌。但聽過馮友蘭的課后,覺得他對許多中國古代的思想學說解釋得那么清晰,評論得那么近情近理。當時張先生敏銳地意識到,“中國傳統思想缺乏分析和邏輯論證,許多內蘊很深厚的東西都被掩藏了起來,可以玩味,卻難于解說。”張先生認為這與中國傳統哲學不重主客二分的“天人合一”,少有認識論與方法論,更缺少演繹法有關。張先生日后關于中國哲學發展道路的許多思考,所闡發并系統提出的新“天人合一”、“萬有相通”哲學體系,其實就包孕和涵攝了西方“主客二分”思維方式的積極因素。作為一位受傳統舊學影響頗深的學者,張先生及至晚年都強調學習西方特別是學習西方哲學的重要性,希望用西方近現代哲學的認識論與方法論來激活、驚醒中國傳統哲學這頭“雄獅”。
思想的發展總是在正反合的辯證之途中曲折演進的。如果說馮友蘭講授中國哲學史,更多地將張先生引向了對邏輯推理和概念分析的重視的話,那么,西學造詣極深、西方哲學功底“如撒鹽水中,化影響于無形,不露任何痕跡”的佛學大師湯用彤,則將張先生帶入了一個高深莫測的“玄遠之境”。湯用彤講授魏晉玄學,在課堂上強調最多的是“物我兩忘”和“即世而出世”、“應物而無累于物”。湯先生說:“笛卡爾明主客,乃科學之道,但做人做學問還需要進而達到物我兩忘之境,才有大家氣象。”他所強調的大家氣象,給張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張先生后來經常強調的既要重主客,又要超主客,強調科學與哲學的結合,就與湯用彤當年的教誨有一定的聯系。
在張先生的新體系中,哲學的根本問題被概括為人生的“在世結構”問題。所謂“在世結構”,是指人與世界相結合的關系和方式,這又可以粗略地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主體——客體”的追問方式,一個是“人——世界”(“天人合一”)的追問方式。前者以我為主體,以他人、他物為客體,兩者是相互外在的東西;后者把人與世界萬物看成是息息相通、融為一體的內在關系。相應地,上述兩個層次在中外哲學史和個人精神發展史上大體表現為三個階段:“前主客關系的天人合一”階段;以“主客二分”為主導的階段;最后是經“主客二分”式思想的洗禮,包含“主體——客體”在內而又超越之的高級的“天人合一”階段,又可稱之為“后主客關系的天人合一”。這樣,“天人合一”、“萬物一體”本是個人和人類精神發展的邏輯起點,又成為其最終歸宿。
二
真正的哲學創新從來都不是積累性的,它歸根結底是元哲學層面的重建,可謂“一是皆是,一非皆非”,而一旦取得突破,就為哲學的未來發展開辟了廣闊的空間。張先生的新哲學體系沖決了主體性哲學狹窄眼界的限制,從元哲學層面揭示了西方現當代哲學轉向的本質與趨勢,為中國哲學的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
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張先生強調“由‘在場的形而上學到在場與不在場相結合的思想轉向”,從“有底論”向“無底論”轉向。在張先生看來,任何一個事物都有其出場(在場)的方面,又有其未出場(不在場)的方面,在場的東西以不在場的東西為根底,彼此一體相通。由于這種根底是無窮無盡的,所以這種根底也就是無底之底。既然當前在場的東西總是以隱蔽在其背后的不
在場的東西為根源或根底,那么人類認識的目的就絕不能僅僅滿足于求真、追求主客觀相一致,局限于眼前的在場之物,而更重要的是求新和創造。在一場《超越現實性哲學的對話》中,張先生就現實與虛擬的關系做出了全新的思考。他批評傳統的現實性哲學框架,強調“哲學要創新,必須把想象、虛擬放在核心地位”;“想象把人的注意力指向不在場的領域,它是創造性和虛擬性的源泉。”
在審美觀上,張先生強調審美意識在存在論上的根據就是“萬物一體”、“天人合一”。“按主客關系式看待人與世界的關系,則無審美意識可言;審美意識,不屬于主客關系,而是屬于人與世界的融合,或者說天人合一。”為更深刻地揭示從主客關系的在世結構到超主客關系的在世結構,從重在場到重不在場的當今藝術哲學新方向,張先生結合中國古典詩論中的“隱秀說”,引用了元稹、柳宗元、杜甫等詩人的著名詩篇,闡幽抉微,妙語解頤。以詩意的語言生動地敘說了中國詩歌注重“意在言外”、“言約旨遠”、“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含蓄之美,讓人讀后既感新奇信服,又倍覺親切有味。
在倫理觀上,張先生認為對“萬物一體”的領悟是提高道德水平的基礎,并呼吁在重視經世致用的同時,更多地提倡詩意境界和“民胞物與”的精神。在張先生看來,今天弘揚“萬物一體”思想,更多提倡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中的“一體之仁”的觀念,人與人之間能夠多一分一體同類之感,會多一分愛的溫情。毫無疑問,這樣的倫理觀為當前的和諧社會、和諧世界建設奠定了哲學本體論上的依據,值得進一步研究與弘揚。
在歷史觀上,張先生力主從傳統的歷史還原論到現代的古今融合論的轉變。“萬有相通”、“萬物一體”,這是古今融合、傳統與現代融合歷史觀的存在論依據。“過去與未來,古與今都是唯一的宇宙整體自我展開、自我發展的不同階段和不同狀態。所以,過去與未來、古與今雖不同而又能相通,歷史的昨天和今天是一個相互貫通的有連續性的整體。”在歷史研究中,有必要把古今溝通起來,而不是使古與今彼此異己,相互隔離。
顯然,作為一位對主體性哲學有長期的深湛研究,對其利弊有著十分清醒的認知的哲學家,張先生晚年所闡揚的新“天人合一”、“萬有相通”的哲學體系絕不能被視為是對原始的“前主客關系的天人合一”的簡單回復,而是一種辯證的更高層次的回歸。張先生對主體性哲學既有熱情的肯定與吸收,又有獨創的超越與發揮。把哲學規定為以進入人與世界融為一體的高遠境界之學,在張先生看來,這種境界“不是拋棄主客關系,而是需要和包括主客關系卻又超越之”;“不是不需要知識和規律性、必然性,不是‘棄智,而是需要廣泛的知識和規律性、必然性而又超越知識、超越規律性、J必然性”;“不是不需要功利追求,而是既講功利追求又超越功利追求”。因此,與傳統的帶有相當封閉性與停滯性、缺乏認識論支撐的舊“天人合一”體系相比,張先生所提倡的毋寧說是一種既有“萬物一體”高遠精神境界,又強調發揮人的主體性、奮發有為的積極進取之學。在張先生晚年的代表性學術著作《哲學導論》一書的結語中,他更將自己的新“天人合一”、“萬有相通”的哲學體系命名為“希望哲學”,“希望就是虛擬”,“希望就是戰斗”。這樣的哲學,極目無限,元氣淋漓,不曾見半點倦游歸來的頹唐心境。可以說,新“天人合一”、“萬有相通”哲學體系與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理論相比,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都已躍升到一個嶄新的思想層次。
張先生晚年的學術轉向及其所取得的重大學術成果,不僅對中國哲學具有方向性的指導意義,是中華民族傳統智慧的當代延續,而且為我們提供了西方現當代思潮在中國語境中的現實出場路徑,對我們高屋建瓴地理解與把握西方現當代哲學的未來走向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它是漢語圈學者對世界哲學做出的獨特貢獻。可以說,“歸途”既是中國哲學的歸鄉之旅,也是民族思想原創的超越之途。
毫無疑問,當代的中國哲學建設不能固守中國傳統的思想視域和方向,只有在和世界哲學、特別是西方現當代哲學這個他者的對話中才能形成與發展。不過,中國哲學的未來發展更需要實現一種真正的自覺,中西的會通與交流還亟待改變目前以西學為體的傾向。“穿越西方是為了更好地閱讀中國”,西方的他者鏡像構成了我們認識自己的必要前提,認識自己成為遍歷西方的最終歸宿。我們固然需要在與西方哲學的視界融合中拓展我們的思想起點,但我們研究西方哲學的目的,最終還是為了發展自己的哲學和文化。誠如張先生所言:“我也認為中國傳統哲學固有的優點也只有在與西方哲學結合的條件下,才能重振自己的活力。中國傳統哲學中有很多可貴的東西似乎尚處于沉睡中,需要用西方的思想來激活它們,而它們一旦被激活,就比西方的哲學思想更具魅力。”我們期待有更多的中國學者踏上這樣的“歸途”。中華民族的學術還鄉之日,也就是中華文化在世界上大放異彩之時。
作者單位:《江海學刊》編輯部,副研究員,博士
(本文編輯喬向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