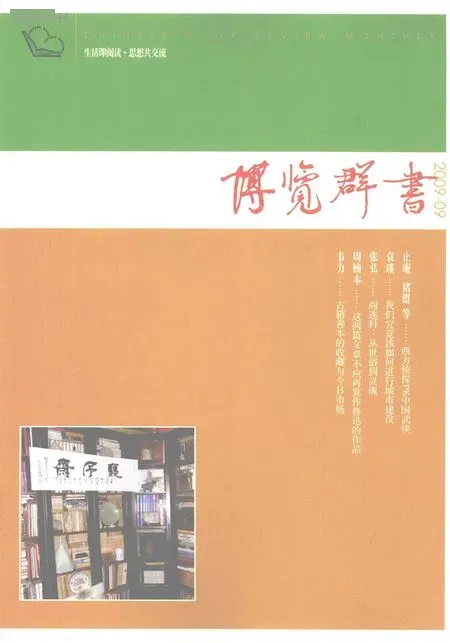黃苗子和邵洵美文圖同題的《真心話》
綃 紅
上世紀30年代的《時代漫畫》沉寂了70年后,影印出版了。它是當年發行量以萬計的一份期刊。提到《時代漫畫》,曾為之投入無數心血的老畫家和當年喜讀此刊的老人至今猶喜形于色。十多年前,我在圖書館也覓得此物,翻閱中獨自偷樂。那時,我正為寫《我的爸爸邵洵美》和出版爸爸的文集而搜集資料,匆促之間,只顧復印爸爸登在其中的3篇文章而沒能仔細欣賞其他作品。如今,上下兩冊的選印本在手,我再細讀第21期(1935年9月20日)中爸爸那篇《真心話》,發現就在它后面的一頁有一幅漫畫,題目也是《真心話》!它是爸爸的好友黃苗子的作品。我實在好奇,不禁想問個究竟。去歲,我身懷此卷拜訪黃苗老。他笑著回答:“時隔太久,記不得了。”
刊物同一期的作品,前后同題,為什么呢?這個問題一直在我心里盤旋。近日,我恍然大悟!
詳讀《真心話》這篇文章,作者先講真心話與真話的不同,而后舉例,從人際交往到要人言論。接著重點談文學雜志上有人五論“文人相輕”,又評說林語堂自我矛盾:他在《文飯小品》發表的《說本色的美》要求說真話;又在《人間世》提倡“特寫”要求說真心話。文章看似針對文人,其實不然。
常讀邵洵美的文字、熟悉他的文筆的人,可以了解他那種迂回筆法。這也是他后來在《論語》寫“編輯隨筆”所慣用的“春秋筆法”:說東道西,點到主題,猛擊一掌,轉身而言他。譬如,1936年西安事變后的第106期他的“編輯隨筆”:談談過年陰歷陽歷不能統一的問題,忽然說:“我想,或者會影響到那個‘統一救國吧?因為在這一點上我們便很不容易統一的。”當你還沒看明白,他轉而談自己是“天天在過年三十”。自然談起欠債,又講到“親兄弟,明算賬”,“只要看前幾天報紙上有大喊‘清算張學良,而綏遠那筆交易則大有情愿吃倒賬的形勢,便可以明白”。隨后,他講起“半本賬簿治天下”。講起治天下的人像是一爿公司的經理,“百姓雖有一股股權,卻連發言權也沒有。”剛觸到政治,他又回過頭來說,編《論語》是“一種快樂債”。他就是這樣聲東擊西。到了1949年,在《論語》的173期“逃難專號”,他寫的《逃亦有道(復友人書)》,他還是圓兜圓轉地寫。先答復友人關于逃難的觀念如何與時變更。“……在抗戰初期,政府搬到重慶,大家跟著一起逃,最先大家還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后來才明白是長期抵抗,在大后方工作是最值得仰慕的英雄偉績;勝利了,‘重慶人便大出風頭。”筆鋒一轉,針對當下,“只要看我們的蔣總統,在南京的最后一個月中,一般人都感覺到他的威風已遠不如前。但是自從他‘引退以后,一般人又感覺他‘余勇可怖,連最近共產黨的宣傳,也說他正在訓練二百萬新軍,預備卷土重來,好像是一個莫大的威嚇!”后面,他忽然大談逃難于個人種種的好處。有幽默有諷刺,令人忍俊不禁。
這一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呢?還是先來看漫畫《真心話》。黃苗子畫的是小記者在采訪要人秘書。墻上掛著一幅人像,其下有文字,歪掛著。似乎是孫中山遺像和其遺囑。秘書坐著,一副官架子。漫畫有文字說明:
記者:請問某某的病狀,最近有什么變化?
秘書:這兩天因某項事件還未解決,故某某的身體并沒有完全好。
這是指何要人?又是指什么事件?想到邵洵美在其《人言周刊》上的短評往往緊跟時聞,我找來同一時期的《人言周刊》二卷二十四期(1935年8月下旬)郭明(即邵洵美)的《汪院長辭職問題》一文。文后的“編者座談”寫道:“關于汪精衛先生辭職問題的稿件,本刊收到口鴻章先生的《汪院長辭職》一文,據最后消息,汪院長已有打消辭意可能,故將該文抽去了,由編者寫《汪院長辭職問題》一篇,以表示對此事之意見。”
稿件這樣處理,可見事件至關重要。文章是這樣報道和評論的:
蔣員長于十九日凱旋首都;而屢次辭職的汪院長亦于二十日接蔣委員長來電當晚晉京。此次全國人之目光。無疑地群集在汪蔣會晤之結果上;蓋汪氏若辭職實現,則對內對外之政策,多少有變動之可能,而各部人員亦必有所更動。……但讀二十一日報,則中央社電謂政院各部會長官現決定,如汪氏仍不能打消辭意,即提總辭職,以示堅決挽留之意;記者不禁大駭。若政院各部會長官群以總辭職為要挾,則一方面不顧人家性命,一方面亦太嫌情感過于理智矣。大人物舉足輕重,國事友誼,政見病狀,務須分得清楚;此種堅決挽留之表示,實使我輩小百姓惶恐不知所措矣。但愿中央當局能迅速權衡輕重,決定行止;并望汪院長亦細量病體,弗過憂慮,為國犧牲,固大丈夫份內事也。
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汪蔣之間的矛盾,以及汪的作態背底里有意圖。事態嚴重,不可等閑視之。
此漫畫明顯指的是這個事件。邵洵美的文章卻沒有明說,但圖文同題,就告訴我們兩個作品是同一題材的。邵文里涉及政治的只簡略地說:“再如申言為國為民,繼以埋頭苦干,這句話也可以當作真話;但若說出我們一舉一動不過是掩人耳目,威信既失,大事也許反而不可收拾。”我明白了!邵洵美是輕輕幾句揭示汪精衛的為官之道;黃苗子則是借那秘書之口吐露真情。
這樣,我們就不難重現當時場景:時代圖書公司幾個刊物的編輯部在一個大辦公室里。可以想象:那一天(1935年9月21日),幾個畫家、編輯和邵洵美都在編輯部。眾人讀報,對這個議論得沸沸揚揚的事件很有看法,邵洵美決定在《人言》上做篇文章。黃苗子決定畫張漫畫來諷刺一番,邵洵美為之捧場,再來一篇呼應。《時代漫畫》的主編魯少飛頗有同感,特地把這兩個作品編排在一起。如此,我就破解了這個“圖文同題”的謎。
從圖文同題的《真心話》,我得到啟示:讀者如果只看文章的文字描述,圖畫的藝術,而不去聯系作品創作的時代背景、新聞人物、政局動態,是難以理解一些漫文漫畫個中的真意的。
邵洵美在這篇文章里何以寫得如此含蓄,在《時代漫畫》里的文章都不像他在《十臼談》和《人言周刊》上發表的文章?他是不想讓心愛的《時代漫畫》也受到像那兩份刊物同樣的傷害。在當時惡劣的政治環境里,刊物不時遭到新聞審查的刁難。《十日談》和《人言周刊》都曾遭禁罰停,《十日談》為此曾以“開天窗”抗議。他甚至為了保護時代圖書公司其他書刊的正常發行,特地另設第一出版社來發行這兩份言辭激烈的刊物。
《時代漫畫》是輕松的讀物。為了刊物的生存,主編魯少飛不得不插入一些軟性的作品(后來曾有人批評這本刊物帶有色情)。其實,這些人不了解這位備受漫畫家尊重的主編。他當時編《時代漫畫》的宗旨是:“有不平我們就要講話,有丑惡我們要暴露,有戰爭我們要反對。”“漫畫是為正義活著的,為公道拿畫筆是我們的天命。”歷時3年出版39期的這份刊物,其中許多作品在引人發笑的同時,傳播了藝術理念,發出了正義的呼聲。1936年2月,魯少飛因為在第26期的封面上,刊出他畫的《晏子乎》,諷刺了對曰屈膝外交而被關押,刊物罰停3個月。大家一面營救他,一面把刊物改名為《漫畫界》繼續出版,由王敦慶主編。直到6月,《時代漫畫》才復刊。
邵洵美在時代圖書公司辦了3份畫刊:《時代畫報》、《時代漫畫》和《萬象》月刊。他欣賞畫家的藝術、創意以及以畫代言的各種風格,愿意開辟場地讓那些有才有藝的畫家任意馳騁。《時代漫畫》是成功的,在它上面發表作品的有名的無名的畫家多達百人。這些畫家擔負起當時籌備全國第一屆漫畫展和全國漫畫家協會的組織、參與的任務,同時也培養了許多漫畫家,促進了漫畫的發展。1937年,日本侵略者把戰火燒到上海,他們義無反顧地組織起各地救亡漫畫宣傳隊。邵洵美在孤島上海出版的抗日雜志《自由譚》及其英文姐妹版Candid Comment(《直言評論》)里都刊有這些藝術家的宣傳抗日救亡作品。這些藝術家之間的友情一直維持到幾十年后。1984年,他們聚會在老畫家胡考家里,特地請了主編魯少飛,共慶《時代漫畫》創刊50周年。
一份普通的畫刊,70年后重現,其價值不言而喻。它不僅記錄著漫畫的技術和藝術的發展,可供后來者學習參考和研究;也記載了上世紀30年代的歷史人文經濟道德各個方面,對當時的社會風貌、民間疾苦、官場腐敗等的深刻描述,可供今人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