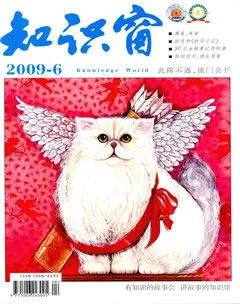“作秀”的鴛鴦
甕彥君
“鴛鴦”一直是夫妻恩愛的代名詞。以鴛鴦比作夫妻,最早出自唐代詩人盧照鄰的《長安古意》一詩:得成比目何辭死,愿作鴛鴦不羨仙。崔豹的《古今注》中說:“鴛鴦、水鳥、鳧類,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者相思死,故謂之匹鳥。”鴛鴦最有趣的習性是“止則相偶,飛則成雙”。在鴛鴦成雙成對、形影不離的“愛情組照”中,最淋漓盡致地彰顯其恩愛纏綿之狀的,莫過于鴛鴦戲水。戲水時,雌雄雙雙互相追逐,游來游去,時而引頸擊水,發出歡快的叫聲。歡愉之后,再雙雙游到岸邊,交頸而眠。其繾綣之情,令人嘆為觀止。
而事實上,鴛鴦并非是動物界“夫妻恩愛、不離不棄”的典范。據動物工作者觀察,鴛鴦在平時不一定有固定的配偶,只是在交配期才表現出那種成雙成對、柔情綿綿的模樣。而一旦到繁殖后期產卵孵化時,雄鴛鴦便不再露面,抱窩和撫育后代完全由雌鴛鴦來承擔。甚至,雌鴛鴦抱窩孵化期間,連吃的食物也要靠自己尋覓。而且,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趕緊另結新歡,成雙配對。
如此說來,鴛鴦不僅算不上彼此忠貞,甚至可以稱之為薄情寡義。可是,人們為什么會把鴛鴦作為恩愛夫妻的象征呢?其一,雄雌鴛鴦外表迥異。鴛鴦給人的印象總是成雙成對。與許多水禽類動物不同,雄鴛羽毛華美,五彩光亮,雌鴦毛色蒼褐,樸素單調。鴛鴦同戲雙棲,觀者一眼可辨雌雄。至于明察此鴛鴦非彼鴛鴦之眼力,卻非常人所能具備。其二,鴛鴦善于“作秀”。無論是水中交頸相歡,還是水邊抵頭“濕吻”,抑或是岸上疊翼雙棲,哪一幅圖景不是愛情的絕美演繹?又怎能不令歷代文人墨客心潮起伏、思緒翩躚?于是乎,借物抒情,吟詩作對,留下了不少傳世佳句。“盡日無云看微雨,鴛鴦相對浴紅衣”、“鳥語花香三月春,鴛鴦交頸雙雙飛”,無一不是鴛鴦恩愛有加的生動寫照。
事實上,無論是愛情忠貞的傳說還是薄情寡義的真相,都是鴛鴦的生活習性使然。對鳥類來說,忠貞不渝是一種危險的生存方式。所以,鴛鴦的負心與薄情,有利于自身的生存繁衍。道德范疇的意義,都是人們賦予的,與鴛鴦無關。不過,從人們對鴛鴦的褒獎可見,即使是在動物界,善于作秀,也是可以換得一時的美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