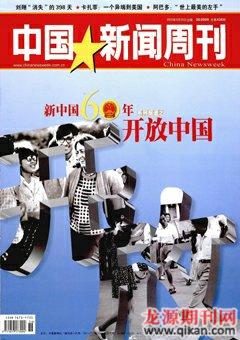一個甲子:完成的和未完成的
李泓冰
共和國滿了一個甲子,這當然不是終點。而是新的起點。站在這個起點上,我們站在先輩的肩上,矚望著那個可望而尚未能及的目標:人的現化代。
按國人傳統的紀年習慣,60年為一個甲子,是天干地支循環的起點和終點。我們一直念叨的“新中國”,也滿了一個甲子。圍繞這個甲子的盤點、贊美及歡呼,時下鋪天蓋地兼歡天喜地。是的。家人滿了一個甲子,也要隆重祝壽,何況一個大國。有這樣的機會,站在一個歷史循環的起點和終點,安靜下來,后顧前瞻兼東張西望,絕非多余。
60年,對美國人而言,很漫長,是該國獨立建國歷史的四分之一;對中國人而言,很短暫。對有文字可考的歷史長達近3000年、且文明從未中斷的古國來說,60年真如白駒過隙。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計算,美國現代化歷史的起點與它獨立建國的起點是相一致的,在美國《獨立宣言》中,這樣的表述顯然十分現代:“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建立起來被管轄者同意的政府……”而在中國,一般認為現代化進程的起點,是1840年的鴉片戰爭,國門被西方炮火轟開,沉醉了兩千多年的“天朝意象”戛然而止,中國的現代化開始得被動而屈辱。從這個意義上說,剛剛完結的這個甲子,對走向現代化的中國舉足輕重。
我們不妨假設自己是“戊戌六君子”的譚嗣同們,是辛亥革命的孫中山、五四時期的魯迅或陳獨秀,甚至是為了共和國光榮獻身的江姐和許云峰,倘若用他們的目光穿越這個甲子,在“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究竟有哪些完成和未完成的事業呢?
顯然,最讓先輩們欣慰的,是中國人民終于“站起來”了。中國的現代化,首先是“中國民族自求解放,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這個目標,在新中國完滿實現。
上世紀30年代,《大公報》社評《孔子誕辰紀念》曾哀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力,既已蕩焉無存,不待外侮之來,國家固早已瀕于精神幻滅之域。”而今,在金融危機席卷全球時,非盟主席讓·平的話在國際上頗有代表性:“中國是世界經濟的主要拉動者之一”“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如果沒有中國的積極參與,世界經濟的恢復將是不可想象的”。
試想,如果譚嗣同聽到這樣的話、看到這樣的情形,會熱淚長流的吧!
思想解放大潮激蕩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民生問題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農民免除了持續數千年的“皇糧國稅”,社會保障之網漸次籠罩城鄉的草根百姓,中國的人均收入、人均壽命、人均受教育程度,都以驚人的幅度提高。對一個長期以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受教育權和話語權一直由統治階層壟斷的古國來說,民生水平的提高,是百姓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享受到的最看得見和摸得著的實惠。
還有先輩們魂牽夢縈的民權和民主。剛剛慶祝了60周年的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開創性地實踐了中國式社會主義民主的議政模式。最大的成就,則是數億工人農民人身自由的解放,是小人物以五千年來有的主人翁姿態走上歷史前臺,這一“解放”翻天覆地。當年的掏糞工人時傳祥,能夠和國家主席平起平坐,“同樣是革命工作,我們只是分工不同”。而農民工代表也走進了中南海,與總理議政;農民工人大代表也出現在莊嚴的全國“兩會”……凡此種種,如果放在唐宋元明清,足夠驚世駭俗。
然而,先輩的夢想,也不乏尚未完成的。民主精神和科學精神這兩塊基石,在共和國大廈上,尚未牢固地奠定。
所謂民主精神,在民眾層面,至少意味著公民受法律保障的平等、自由等權利被充分尊重;在決策層面,意味著決策過程的充分討論與公開透明。但是,類似網民發帖批評基層政府官員千里被拘和“躲貓貓”“俯臥撐”“做惡夢”一類離奇事件的頻頻發生,足證我們在民主方面還有諸多的“未完成”。
所謂科學精神,針對的是滲入國人骨血中的封建主義和蒙昧主義,倡導用理性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認識自然,認識社會,認識人自身。然而,像“大躍進”的荒謬、建設決策的唯上與隨意、青山遍布的豪華墳塋……也足證我們這個民族還遠未完成科學精神的塑造。
事實上,我們尚未完成的,一言以蔽之,是人的現代化。是國民素質的現代化。此起彼伏的陣痛和人禍,告訴我們,相當多的國民、特別是不少基層官員的心理和精神,還被禁錮于封建主義的枷鎖之中,已經構成了對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嚴重障礙。
人的現代化,極難。用鄧小平的話來說,還得“殺出一條血路”。民主精神、科學精神的生根開花,要從執政黨做起,從制度性反腐做起。深化改革,進一步解放思想。那么,改革什么?解放誰的思想?恐怕要改的是既得利益者,解放的首先是官員的思想。用自己的手給自己動手術,所以極難。
念及人的現代化的艱辛與迫切,孫中山的話,至令仍然足以激勵我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評《中國現代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