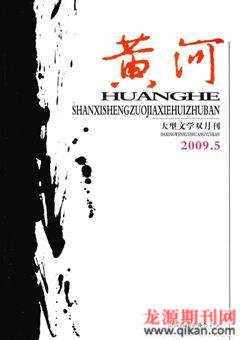沸騰和迷亂
畢星星
回望牛吃臺
戲迷屬于一個奇異的人群。他們為一個虛擬的世界而陶醉,為那個角色的表演唱腔而迷狂。既然稱為迷狂,就不能以理智的常人常態來衡量評價。名角培養戲迷,戲迷捧紅名角,兩者之間,相互依存,相輔相成。戲迷因為有自己的偶像,因而迷之有道;名角因為有自己的戲迷群體,有一種獲得肯定的成就感。在長期的“互動”過程中,名角逐漸有了自己相對固定的戲迷群體和演出區域。戲迷也由于偶像的反復培養,形成了某一方面的欣賞偏執。梅尚程荀,各有所愛。蘿卜白菜,口之于味,各不同嗜。馬克思說,欣賞音樂,先要有一個懂音樂的耳朵。戲迷們豈止有一雙懂音樂的耳朵,他們更有一雙嚴格選擇、無端挑剔的耳朵。只有自己喜好的,才能入耳,一旦不合口味,即嗤之以鼻。各有所崇,各不相讓,看似對立,水火不容,倒也影響和促進了戲曲流派的發展形成。蒲劇是一個地方戲,但是流派紛呈,演唱風格各異,引領了形形色色的戲迷。在戲曲發展的歷史上,這也是一道奪目的景觀。
現今的歌星,多有自己的崇拜群體。在一波一波的時尚更替中稱為“粉絲”。粉絲們對自己的偶像無由崇拜,狂熱追逐,報刊多有記載。歌星們凡有演出,歌迷蜂擁,人浪如潮。打出大標語,狂叫“我愛你”,時常由擁踅聚變成騷亂。蘭州一名劉德華的粉絲,搜集影像,購齊音響,多年追蹤,傾家蕩產只求一見。這些當代的粉絲莫要忘記,他們并不是藝術史上追星的始作俑者。戲迷們當年的擁踅一點不比他們遜色。而且,當年粉絲們瘋狂崇拜,要發泄,只有戲劇一條渠道。如急流倒灌錢塘江,掀起滔天巨浪一點也不奇怪。
只是當年的戲迷,表達的方式更為古典。由于演出地點的原因,戲曲喧騰和迷亂大多嘯聚在鄉村。不似現在,歌迷粉絲幾乎全是城里的小青年。
兩者的區別還在于,戲迷的成分,以成年人居多。過去這樣,現在也這樣。可見一個戲迷的誕生,要接受更多的影響和熏陶。成功地塑造一個戲迷,分明也要比今日的歌迷來得日久,來得沉緩,來得繁難。
民國年間的蒲劇鄉下演出,場面都很簡陋。路臺是舞臺的一種,臺下空出一個門洞,留好槽口,劇團演戲了,搭上模板,嵌進槽口,一頁席鋪上去,平展的臺面就成了。臺上演戲,臺下照樣過人。它顯示出設計的精巧,看周圍環境,好多其實也是不得已。舞臺在路口,只得演戲通道兩用。戲臺設頂,是為演出著想的。好一點的戲臺,能想到觀眾,為觀眾席也設個頂。一般來說,這種設頂不筑圍墻,只用柱子撐起一個屋頂,好似一座遮陽避雨的涼棚,當地人叫它“卷棚”。加蓋卷棚的戲臺,當然比普通的戲臺效果好多了,刮風下雨也照樣能演出。戲臺設置卷棚,是明代以后的事。當時,戲臺帶卷棚,那是非常闊氣的建筑。一直到現在,大部分鄉村還都是只建戲臺,不設卷棚的。講究一點的,可以在臺口搭建一個木頭框架,釘上竹席,刷上黑漆,平時放下框架,從檐口到臺口遮蓋嚴實了,叫做苫子。劇團來了長桿子撐起,兩頭都有鐵角鐵隼咬合,十分牢靠。五十年代,鄉下還能經常見到這種黑蓋頭式的戲臺。很明顯,撐起苫子,遮陽遮雨的地界有限,主要的作用,還在于保護臺上的演出不受風雨侵擾。
最簡陋的臺口叫“牛吃臺”,最熱鬧的演出也在“牛吃臺”。
晉南河東一帶,中部平闊,四圍山隔河侵,偏僻荒涼。在一些偏遠山鄉,地廣人稀,戲班也難以光顧。三戶五戶人家,星星點點撒落在大山的溝凹里。從溝這邊到山那邊人家,動輒有幾十里的山路。村子小,一家請不起戲班,只好聯合起三鄉五里的鄉親,公推糾首,聯合請一臺戲。沒有戲臺,找出一塊平坦的高地,劃出臺界,四周抱來高粱稈、玉茭稈搭成圍墻,堵成臺口。來看戲的鄉民,大多家住幾十里甚至百里之外,日場戲晚場戲,根本趕不回家。為了看戲,為了這難得的數年一度的大節,鄉民門舍了田禾舍了家,一家一家,推起小車,搬著鍋灶,遠遠地對著戲臺,幾個高粱玉茭捆子斜了一靠,就是一個窩棚。一家人白天看戲,飯時了窩棚外頭隨便挖一個坑,點一把火,啦啦燒熟了飯,吃了接著看晚場。散戲鑼鼓敲響,全家鉆進窩棚睡去。三天或五天,一臺戲唱完了,他們收拾起家當,推起小車,哼唱著戲文上路。逶迤的人流緩緩地向四方的深山游動,星星點點地消失在樹影里。
這時,搭臺的村子放出牲口來,牛羊一群一伙圍住戲臺,把一堆一排的秫秸吃光。田野里的窩棚,也被牛群羊群掀倒吃凈。幾天的狂歡,仿佛了無痕跡,深秋的原野,只見無邊的黃土拱衛著土臺,那曾是田野釋放歡樂的地方。
牛吃臺,似乎平平常常,仔細想來,卻有一種驚心動魄的感覺在心頭。我們或許驚異于國外的狂歡節,卻不曾把偏僻山鄉的狂歡節放在心上。追溯我們民間的戲劇集會,它可說是我們底層民眾早期的狂歡節。十里搬家,百里跋涉,他們聚攏到一個演劇中心。放下農活,放下家事,他們一心一意到陌生的田地住幾天,頭頂著日光月光,點點灶火環繞著舞臺的聲色光彩。一年中間,這是他們最開心的日子。舞臺簡陋,擋不住發自心底的喜悅。這是最原始的戲劇節,也是那個時代的鄉村狂歡節。一臺村戲,一箅窩頭,一壺老酒,至死不忘其樂。在極其貧窮的山鄉,戲班招來大聚會,一場空前規模的歡樂盛宴,來自世代相傳的梆子腔。
蒲劇,帶給他們歡樂的源泉。河東大地的老百姓,他們是蒲劇的群體戲迷。
形形色色的戲迷(上)
唱戲以技藝出名,在情理之中。戲迷以看戲出名,就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了。不過在河東大地,出了名的看家也是歷歷可數。每一地都有鄉親們掛在嘴邊的戲迷。說起他們來,有時是調笑,卻也有幾分羨慕在里頭。
解縣四大名人解放前后,運城解縣一直流傳著本縣“四大名人”的說法:孫楚剃頭王,廣勝薛子良。孫楚是當時閻錫山手下的軍長,孫廣勝是蒲劇著名花旦,薛子良時任陜西省財政部長,而這個剃頭王,是當地一個以戲迷得名的剃頭師傅。
河津常好堡孫狗子。河津坡上坡下,哪一個不知道老戲迷孫狗子?民國時期一直到解放初期,外出看戲不管多遠,孫老漢都要靠兩條腿走去。只要方圓二十里有戲,老漢場場不誤。為了看好戲,老漢將一套用具常年預備著。老漢一出門,一把傘,一只手電筒,一把馬扎子,還有一雙高筒雨鞋。那只馬扎子很特別,一尺七寸高,放開和條凳一般高低——座位太低人頭遮擋,就看不好了。這四件寶老漢常隨身帶著,不管路遠天黑,只要戲好,就撂下手里的活兒,先看戲。村里鄉鄰一看老漢全身披掛,就知道一準是看戲去了。看熟了,坐在前排,能和著演出背臺詞。那個演員唱錯了,老漢會惋惜地嘆氣糾正。有一年王秀蘭劇團到河津,扎戲當天晚上,演出中間來了大雨,長展檐的雨柱,一會兒工夫,臺下的積水就淹到了半腿。場下人走光了,老漢卻不走,打傘穿靴,硬看到底。全團感動得不行,王秀蘭見老漢這么愛戲,就叫過老漢聊了幾句家常。這可了不得,從此老漢腰桿挺得更硬了:王秀蘭和我諞過閑話!
王泉永的火燒爐子。安邑縣嶺下一帶,有個打火燒的王泉永,他打火燒,多半為了趕戲。方圓三十里只要有戲,臺下肯定有他的火燒爐子。他的趕戲日程是這樣的:那個村子扎了戲,王泉永就騎著個嘀里當啷的舊車子,后架斜挎一口小鏊,懷揣一把小搟杖,準在開戲頭一天趕到。在當地供銷社買好白面、油鹽、花椒、小茴香,盤起旋風爐子,生意就開張了。邊賣火燒邊看戲,他也不圖掙錢,能看戲比啥都強。就這樣,像游民一樣,戲走到哪里,他就攆到那里。劇團沒來他先來,劇團走了他才走。生產隊管得緊了,他白天封火下地,晚上照樣趕到戲場操持他的火燒爐子。一個人一輛自行車,一年在外游蕩大半年,有名的劇團尾巴。
老漢最迷閻逢春。知道老漢脾氣的都心里明白,在老漢的火燒爐子邊,不能說閻逢春半個不字。后生們摸著了老漢的癢處,時常喜歡逗逗他。一邊看戲,裝著沒有瞅見老漢的樣子,幾個人議論:“人家閻逢春那把式,世上沒有!”老漢聽得受用,揪兩個大大的面劑子,狠擱了油鹽小茴香,烤得焦脆黃亮,遞給小伙:給老人帶兩個火燒回去!要錢?要啥錢哩,對勁就行!也有人說反話,故意在一旁撂涼腔:“閻逢春那破喉嚨爛嗓子日巴能聽么?誰看上那把式是瞎了眼!”老漢一把拽住就要理論:“這娃是哪個村的?回去問問你先人看過戲沒有?”旁邊的連忙勸架:“耍笑哩,不要當真。”老漢余怒未息:啥都能耍笑,這不能耍笑!一邊吵著,有人就聞著了焦煳味,叫住老漢:火燒烤煳了!老漢連忙掀開小鏊,白面餅子烤成了木炭。起事的一見不妙,起身就要溜走,老漢還要趕著磕打一句:“火燒糟蹋了不要緊,閻逢春不能受一點傷損!”
牛籠嘴的傳說。村里晚上唱戲,太陽下山,鑼鼓叮叮咣咣一響,一老漢就聽得心急火燎的,急急忙忙給牛添了草,拌好料,坐到場子里等著。看了半夜戲,第二天早上起來,到牲口棚里一看,頭天的草料一點也沒動。糟糕,這牛病了。連忙牽了韁繩,找到獸醫:“給咱看看是咋啦,這牛一口草也不吃。”獸醫說:“你給牛卸了籠嘴,我掰開嘴看看。”什么,卸了籠嘴?老漢一扭頭,不看啦!牽了牛轉身就走。獸醫還在發愣,老漢心里清楚,只顧了看戲,忘了給牛卸掉籠嘴啦。
王存才戲迷的傳說。存才師傅是蒲劇名家,民國年間,山陜一帶頂數他的名氣大。關于王存才的傳說也最多最有趣。民謠說:“誤了收秋打夏,不誤存才《掛畫》。”“寧看存才《掛畫》,不坐民國天下。”“寧看存才《六月雪》,哪怕賊偷得沒一屑。”“趕著看《殺狗》,銀子掉了不瞅。”都是關于存才師傅“追星一族”的形象寫照。
有的戲迷傳得更邪乎,叫作“寧吃存才巴下的,不吃豬肉扎下的”,“寧喝存才尿下的,不喝茶壺倒下的”。
早年戲班不帶食堂,鄉下唱戲都是家戶分開管飯。有一家分管存才師傅,飯做多了,存才師傅吃不完,剩在碗里。做飯的婆娘一看,存才師傅吃剩的,哪能隨便倒了,連忙倒在鍋里攪和勻了,想讓全家都嘗嘗味道。男人回來了,婆娘興沖沖地說給男人,男人卻沒好氣,粗喉嚨大嗓門責罵:憨婆娘,咋不倒在水甕里,咱全家能吃一個月哩!兩口正在爭吵,村長來了,問明事由,村長氣得跳腳大嚷:吵球啥哩,還不趕緊端鍋倒到村頭那眼井里,夠咱全村嘗一年!
有一個段子,有點葷,卻是頗能入骨三分地道出戲迷對王存才的仰慕著迷。說是村里有一個小伙,看存才的戲迷了竅,臺上臺下追著看,心里發了狠誓:我非和存才說句話不行。可存才師傅不認得他,兩人根本沒機會搭腔。一天看到存才師傅卸妝上茅房,小伙子一看機會來了,連忙跟到茅房,沒話找話地問:“存才師傅你尿哩?”存才回頭一看是個生人,就沒好氣,狠狠地回罵了一句:“日你媽,你管球我尿不尿哩!”小伙子不但不惱,反倒心里暗喜:不管怎么說,總是和咱說過話了。回到家連忙告給他媽:“媽呀,我今兒個和存才師傅說話了。”“說啥來著?”“我問他尿哩,他說日你媽。”他媽也不惱火,長嘆一聲說:“唉,你媽哪有那個福氣喲!”
四看王秀蘭。幾個老婆婆聽說鄰村王秀蘭劇團唱戲,唱四天,約好去看。想著頭一天名角要出臺,擰了十幾里小腳,誰想一個晚上沒見王秀蘭。那肯定第二天出場,又跑了十來里,還是沒有看著。這下肯定是最后一天了!第三天晚上他們沒有去,誰知道王秀蘭的戲恰恰排在第三天。第四天她們趕來了,又沒有看上王秀蘭。幾個老婆婆難受極了,找到團里,“我們一毛五的票買了幾天,就是想看看王秀蘭,可跑了幾天,花了幾回錢,也沒見上王秀蘭,這可咋辦呀?”王秀蘭一看這樣,當場給幾個老婆婆表演了一段清唱。老婆婆們高興得逢人就說,這下可好了,看了這么近的王秀蘭!
形形色色的戲迷(下)
上面所說戲迷,多是一種淳樸的熱愛,感情深摯,神話崇拜,但戲迷多屬于鄉村不識字的農民。有些戲迷就不是這樣了,他們有文化,有身份,對戲劇有理解有研究,但這一點不影響他們著魔。他們是一群理性的崇拜者。因為有分析,有頭腦,這個群體在蒲劇發展過程中的特殊作用,不可小視。
鄉野有遺賢。河東地區大點的村子,都有鬧家戲的傳統。所謂家戲,就是老百姓自己演出,自娛自樂的文化活動。沒有專業演員,不求報酬,仿佛票友班子,一般在春節期間鬧紅火時候演出幾天,本村和鄰坊村子聚來看一看,也就圖個熱鬧。農民自發鬧戲,可見蒲劇的根子扎得深、扎得牢了。
高頭村是個大村子,兩千多人口。五六十年代,高頭村的家戲遠近知名,不僅在自家村子演,也時常被請到外村,走起了臺。有一年幾乎轉了半個縣,主要演員在縣城大禮堂登過臺。這個家戲班子演員行當文武場家伙齊全,能演全本的《秦香蓮》、《訪馮彥》、《白玉樓》、《庚娘傳》,現代戲有《三世仇》、《苦菜花》等,小折子戲更不在話下。文革期間排演了《白毛女》、《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音樂唱腔全部從地區蒲劇團移植,拉開一個正經劇團的架勢,扎下臺,演三四天不成問題。
高頭村的家戲能排成個樣子,全靠有個李立。
李立家寒,念到小學就停了學。人聰明,全靠自學,卻也天文地理、歷史沿革、縣志村史,無不爛熟于心。當村長時,他在村里發現過仰韶文化時期的文物,報送到文化館。縣里普查地名,他曾經考證過涑水河一帶村落的村名,和專家口舌往來,最終在縣志上自存一說。早在1958年公社組織文工團,把他抽了去,時間不長解散,李立卻從此熟悉了蒲劇,以后不斷鉆研,啃著厚厚的《蒲劇音樂》、《蒲劇唱腔》,竟然學成了半個專家。
李立的特點是不但懂門道,拿起來也樣樣趁手。他能演各種角色,會全套的文武場家伙。演《舍飯》,他會學閻逢春甩帽翅,演楊子榮,他會蹁馬。村里排戲,他自任導演,兼打板鼓。他識簡譜,從各個劇團搞來唱腔,取長補短,安排設計音樂過門,指導本村臨時抽來的年輕人練功,硬是把一個鄉村劇團搞得像模像樣。一般村子演出幾個小折子不難,像李立這樣,全套的蒲劇板式,全套的音樂伴奏包括全套的鑼鼓經,那可不是小打小鬧能比的。
近幾年李立漸漸年長,也有劇團拉他出去,他都謝絕了。喜愛蒲劇,關心蒲劇這一點可說是沒有變。
市里蒲劇團一個演員有一年和我一起去高頭,和李立聊上了。演員不知深淺,賣弄他知道的那些蒲劇常識。李立一開口,從蒲劇起源談到民國楊老六的戲改,再到解放后的蒲劇名演,無不頭頭是道。話題扯到著名導演韓剛,李立笑了,他不想說,看樣子又忍不住,終于說:“韓導演不懂武場家伙。”
“有一年在高頭演戲,一天下了雨,演不成了,劇團在咱村臺子排戲,我在邊上看。幾個過門,韓導演叫帶家伙,那邊鑼鼓點根本沒法帶。”
我們又扯起了電視《蒲鄉紅》的蒲劇大賽,有一個評委點評臺上演員的唱腔,對選手說:“你那個唱,彎兒拐得好。哪里學的?學得好。”
李立又笑了,說這個評委不懂,這是蒲劇的老腔十三彎,民國時候常唱哩。
這下可把客人鎮住了,忙問,你是哪個劇團的?
李立還是悠悠笑著:我就是這個村里的,種莊稼的。
客人出門還在感嘆:這村里還有這人,以后誰敢到這村來唱戲?
李立的事情可不是傳說,李立是我的表兄,我們這一輩都叫他立孩哥。
四大金剛拔刀相助。1989年,地區蒲劇團由陜西韓城演出歸來,按照預先安排的路線,在萬榮縣還有一個點,演出三天。團長興致勃勃打前站來,才知道事主想毀約不演了。雙方爭執不下,來了縣計委主任馮九夫,馮主任路見不平,指責事主背信棄義。接著,又來了農行行長王思恭,農牧局長黃殿棟,石油公司經理黃仁生,四人一齊指責事主變卦,要求按合同正常演出。四大局長都是戲迷,哪能讓劇團受了委屈?事主一看招架不住,連連道歉:“好家伙,先不要說蒲劇團,光這四大局長,一個比一個厲害,我哪里敢不演!”
戲迷領袖之一。民國年間,河東一帶的蒲劇班子要進西安,都要尋找老鄉薛紹生。
薛先生年輕的時候,在陜西一家銀號當差,后來學過會計,不管做什么事,戲迷這個身份伴隨了他一輩子。他能拉會唱,是西安有名的票友。講理論他懂得戲曲史,扮裝上臺也滿可以交代了觀眾。由此他在戲曲圈子廣結善緣,也由此他實實在在給隔河的家鄉戲做了貢獻。
閻逢春在西安的“倒倉”經歷,相信了解蒲劇那一段歷史的人都知道個大概。這個時候,伸出援助之手的正是薛先生。薛先生一直支持鼓勵閻逢春苦練功夫,以圖東山再起。在閻逢春沉潛苦修之時,他和筱蘭香、閻逢春等人叩頭拜把子,結為異姓兄弟。后來閻逢春練出一身絕活重登舞臺。開場戲定為《新忠義俠》,薛先生欣喜萬分,他自家出錢連買了三天全場戲票,全城請人看戲。一時間閻逢春聲名大震,迅速啟動直攀頂峰,不能說不是薛先生之功。閻逢春紅了西安,梨園行秦晉兩家少不了一些是是非非,薛先生親自出面和李逸僧老人一起調解彌和,秦腔蒲劇從此兩下相安,外來戶也由此如魚得水。文革中閻逢春遭難,被開除公職,薛先生把他接到西安家里,一住就是幾個月。這該冒多大的風險,老人不在乎。
蒲劇的著名須生張慶奎在西安起家,同樣得到薛先生的大力襄助。抗戰后期,張慶奎決意離開西安回臨汾另起爐灶,薛先生和他一起商議搭班演出的路線,介紹他先到朝邑,后到韓城,邊演出邊后撤。兩人的交情一直延續了數十年。文革中張慶奎患腿病無法登臺,薛先生把張慶奎接到西安,管吃管住,整整治療四個月,直到好利索了才回去。2001年張慶奎病逝,臨終留下遺言,一定要通知薛老。薛老已經年高體弱,還是帶著小兒子趕到臨汾,參加了張慶奎的葬禮。
薛老接濟過的蒲劇朋友,多得數不過來。五十年代初期,他用自己的全部積蓄,在西安鐘樓街附近買了二十多間房屋,他說,自己要這么多房子干啥,就是為了接待戲曲界的朋友。他的家,實際上也就是蒲劇朋友的“聯絡站”和“接待站”,是他們走進西安的水陸碼頭。停泊一下,有的是休養歇息,有的也許就此出發,開始了人生道路的一個新航程。
1949年以后新政權建立,蒲劇全部撤回河東,但薛老為蒲劇的服務并沒有終止。他牽線搭橋,為王秀蘭所在的大眾蒲劇團移植劇目,為運城各縣的劇團移植劇目。臨猗眉戶劇團為了移植陜西的現代戲《梁秋燕》,劇組就住他家,請專家,包吃住,一直到新戲排成。河東的戲到陜西去演出,他也樂于介紹推薦。1978年,筱蘭香帶著新絳縣蒲劇團,先在渭南,后進西安,在幾大劇院連演一年,此舉也全靠薛老大力舉薦,本來,西安有關領導對這個縣團的水平是不怎么放心的。
如今薛老已經八十多歲了,依然一如既往地熱心為“蒲劇過河”服務。
只是他早已沒有了那二十多間房子。拆遷時,子女們都希望老人跟他們住單元樓房去,老人卻沒有答應。蓮湖區公安局樓下,留了一間開雜貨鋪的門面房,老人說,我就住在這里,不圖別的,只圖蒲劇的朋友來了,好找。
戲迷領袖之二。運城后一代的戲迷領袖,大伙兒公推農業銀行的副行長王思恭。
王思恭其人,在運城可說是個奇人。
他干了一輩子銀行,從基層一直當到地區農行的行長。要說喜好,卻是愛了一輩子的戲。他的家鄉運城上段村,就是遠近聞名的戲窩子,男女老少都好鬧戲看戲。他們全家都是戲迷。王行長曾經繪聲繪色地給我們講述他年輕時看戲的經歷。五十年代初期沒有自行車,出門全靠兩條腿硬走。他和本家一位叔祖,有一年看王天明的《空城計》,天降傾盆大雨,劇團都不打算演了,他和叔祖以及其他觀眾沒有一個人離開,齊刷刷站在雨地里,像一支待命的軍隊,于是劇團堅持在雨里唱完了一出。年輕的王思恭為了看專區青年團的《馮彥上山》,步行五十里趕到夏縣水頭,才知道因為下雨,演出推遲了一天。五十里路又沒吃上飯,王思恭頓時癱軟在地,即使這樣,第二天他又趕了去。他的伯父,聽說夏縣西下晁演好戲,約好三個人,犁完地就走,二十五里地要走三個鐘頭,剛到劇場戲就散了。三人又商量,第二天去早點。一晌干完兩晌的活,下午就往夏縣趕。不料那天是末場,比平時開戲早,他們剛進了場子,看到琴師已經把板胡裝進套袋,正拿起嗩吶準備吹奏終場曲牌。三個人真是傷心!伯父跑到后場找到團長,訴說自己二十五里,連跑兩天的苦命,感動得團長當時拿出戲折子,讓他隨意點一出,臨時加演。這幾個戲迷終于遂了心愿。由三個農民點戲,臨時加演,在這個劇團演出的歷史上,也是一次意外的破例。
參加工作以后,王思恭和劇團來往更加方便,看戲的機會也更多了。他依然是一個瘋狂的超級戲迷。臨汾眉戶劇團來運城演出《兩個女人和一個男人》,演出一個月,他能連看十七場。機關幾個小伙子說看戲沒勁,不去。王行長買票送他們看,幾場過后,年輕人自己買票去看,擋都擋不住了。王思恭很高興,逢人便說:誰說戲曲沒有年輕觀眾?全看你是不是好戲。這件事情他后來反復提起,他說這是戲曲征服青年觀眾的最有力的例證。
王思恭有學歷,會寫作。他發揮自己的特長,多年以來關注劇團演出,演員演唱技巧的新進,劇作的長短,樂音的順逆,他都有專門的文章記錄研究。得了空,他自己也寫劇本。對于蒲劇名家的演出研究,從老一輩的鄧焰、趙乙、張峰、康希圣,到五大名演,到承前啟后的王天明、裴青蓮、張保這一代,到任跟心、武俊英、王藝華、景雪變這一代梅花獎得主,再到下一代新秀新苗,他的文章無不涉獵,幾乎覆蓋了整個蒲劇演藝圈。他出版過幾本創作集子,其中涉及到蒲劇人物、蒲劇史料、劇本劇評的足有一百多萬字。長期的跟蹤寫作,使他修煉成了內行專家,戲行內外都認可他的劇評。憑著他的劇評,劇團得以抬高戲碼;他寫了角兒,角兒因此走紅;他評了戲,戲立馬漲價。他的文章,很多都是蒲劇行進的重要歷史記錄。
但是,如果僅僅以一把“筆桿子”來評價王思恭對蒲劇的貢獻,那就太不全面了。寫文章,不過是他和蒲劇結緣的一個方面。他不是一個外在的記錄人。他是和蒲劇一同前進,一同走過風風雨雨的貼心朋友。劇團的發展規劃,他要建言;劇團排戲,他有點子。劇團的所有事情,他都關心;劇團的所有人員,他都交朋友。從團長到拉大幕的,到鍋爐工,他沒有不熟的。依靠自己在運城的地位和影響,他盡心竭力幫助蒲劇圈里的朋友。有時候,一些困難怕是劇團的領導也難以解決的。比方說,排新戲,置辦服裝,要貸款,他總是全力幫忙成全。劇團置地搬家,他熱心從中斡旋。他多方籌款,在運城設立了一家藝文教育促進基金會,專門獎勵有前途的藝術新苗子。所有這些,人們說,除了王思恭,別人誰也辦不成。
劇團好多事情,看似難,以他的身份出面,立刻迎刃而解。他是蒲劇活動的組織者,也是一個圈里圈外交流溝通的聯絡人。
他是戲迷領袖,在戲迷和名角之間穿針引線,這類故事不知有多少。運城當紅的小生王藝華,去年冬天下鄉回來,妻子遞給一封信,是永濟電灌站一個退休職工寫來的。這個老戲迷熱捧“蒲鄉紅”,學詩詞,鉆蒲劇,迷上了王藝華的表演。寫信來傾訴衷腸,愿結忘年交。王藝華讀罷信很激動,想著聯系一下,可那陣子下鄉演出忙,就放下了。元旦回來想起這事,他按照信上留下的電話號碼打過去,說忙過這一陣一定到家里登門拜訪。對方沉默了好一陣,終于開口,是一個孩子的聲音,說就在前幾天,老人過世了,安葬好幾天了。王藝華痛悔不已。他后來和王行長談了自己的心病。正月初七,王行長陪著王藝華趕到永濟鄉下,和老人的全家一起過年。正月天,名角到一個戲迷家里過年,王行長又促成一曲功德佳話。
王行長很忙,不全是為工作的事,他還為劇團操勞。劇團班子幾個領導有了摩擦,他要去調和;演員鬧意見了,他去評理;劇團誰家的夫妻不和了,他也要熱心解疙瘩。一年到頭,單是為劇團朋友家里的事,他就不知要跑多少趟城里鄉下。我有幾次打電話過去找他,他都在張羅劇團朋友的家事。這一方面是因他熱心,另一方面也是非他不可,別人不頂事。
他是王行長,朋友卻戲稱他王團長,二團長。有人甚至說,他這個團長比蒲劇團長要大。在蒲劇團,文工團,藝術學校上頭,還有一個團,他是這個團的團長。有些事情,文化局領導出面也未必能解決,這個時候只有請王團長出面了,他一出面,事必圓滿。比方說,想促成運城三朵梅花同臺演出之事,只有王團長出馬,才能皆大歡喜。“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群峰并立,三江合流,運城蒲劇名家的群英會,只有王行長出手才能玉成。不管誰都看他的面子。
他從來不贊成人家把他和薛老先生相提并論,他在文章里說:如果把薛老比作一座高山,我們這些人充其量不過是山腳下的小土丘。
不知我是否拂逆了他的謙恭,在這里還是把他和薛老并提了。
也不是我一人這樣看,蒲劇名編劇楊煥育常說:蒲劇有兩大戲迷,陜西有個薛紹生,河東有個王思恭。運城一幫戲迷成立協會,公推王思恭為名譽會長。
公家的銀行行長,民間的戲迷領袖,這兩個身份哪個對社會貢獻大?我看還不好掂量。
迷亂的鄉野
戲迷們聚到一起,本來是為了過癮,聽一聽看一看自己向往的名角。這是一群因為崇拜和仰慕聚集到一起的人。但是劇場是一個大眾聚會的場合,尤其是過去的鄉下演出,露天舞臺,進場人數不受座位的限制,全看場子大小。有時來了名角,成千上萬的人擁擠進來,局面失控,時常會形成騷亂。這種瘋狂,看似溫柔,殺傷也很強烈。失控的崇拜者從四面八方匯集來,一個狹小的地域無法抵擋,秩序開始崩毀,騷亂蔓延放大,一場悲劇便不可避免。在蒲劇演出歷史上,戲迷觀眾擁擠造成的公眾事件,屢屢發生,多年以后依然歷歷在目。
鄉村沒有英格蘭足球流氓,所以即使釀成事件,也是因愛而起,出現騷亂,不是他們的本意。那時又沒有建立應對突發事件的機制,沒有進入緊急狀態的意識,完全依靠道德倫理約束,好在越軌時間很短,處理也不復雜,很快煙消云散,鄉野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很少有人再提起那一場悲喜劇。
鄉村唱戲,一般自己搬凳子,占坐位。正對戲臺的中間位置好,大家依照先后次序擺放自家的小凳或條凳。兩邊是“站票”,年輕的小伙或是沒有座位的中年人站著看,自然地形成了兩邊高,中間低洼的形狀,黑壓壓一片人海。中間的低洼地帶秩序好。兩邊站立的年青人,本來就血氣旺,好個熱鬧。角兒出場了,架勢一拉,你擠他擠,隊伍不由得就騷亂起來。人流一涌成了浪。民國年間,戲臺兩邊專門安置兩條壯漢,看見人浪忽涌,掄起兩丈長的竹竿就甩打過去,一見竹竿舉起,就有人喊:“小凳擱到頭頂!”以免摑著了腦袋。嘩啦啦摑打一陣,擁擠平息了,接著看戲。五十年代,偶爾還能看到扛竹竿的大漢,少了。鄉村有了新政權,各村都有民兵組織,有了亂子,“叫民兵來,誰搗亂,綁了!”帶槍的民兵一旦登臺,有時也能把混亂彈壓下去。
1967年,我在泓芝驛鎮看《沙家浜》,親眼看到王秀蘭出臺,唱到“智斗”一節時,舞臺兩邊的“站票席”開始忽悠,幾番此起彼伏,靠近的老弱婦孺受不了,就開始哭叫。臺下大亂,演出中斷。幾個前排懷抱小孩的婦女擠得受不住了,只好爬上臺口。王秀蘭接過一個中年婦女懷里的孩子,替她抱著。那時的王秀蘭,讓我感到美麗極了,親切極了。
還是這個王秀蘭,八十年代初在河南靈寶縣演出《西廂記》,聽說王秀蘭出臺,觀眾早早地從四面八方趕到。扛著板凳,帶著干糧,都想占個好位置。離開戲還有兩個鐘頭,場子里就擠滿了,場外的人群還在一個勁往里涌。眼看化裝時間到了,王秀蘭卻被隔離在場外了,根本沒有辦法擠進去。當地的村長想了一個辦法,扛來一架梯子,對王秀蘭說:現在只有一個辦法,把梯子搭到舞臺后墻,你跳墻過去進后臺。一丈多高的土墻,王秀蘭還從來沒有這樣為難過,不過沒有其他辦法,心一橫只得跳。這樣,當晚的《西廂記》,張生還沒有跳墻,“紅娘”倒先跳了一回墻,多年過去,依然是戲外有趣的花絮。
騷亂總不是那么可親的,它更多露出的是殘酷的一面。
五十年代,閻逢春的《周仁獻嫂》已經相當紅火。鄉村百姓,能看到閻逢春演的周仁,那是一份驕傲的本錢。那天戲扎在馮村,園子里早擠滿了人,外面的觀眾不問情由,依然還要擠進去。把門的擋住不讓進,人群頓時大亂。四面八方涌來的人流根本阻擋不住,他們開始爬后院,翻圍墻。鄉村的土墻年代一久,雨水就沖開了豁口子,這時,豁口成為翻墻進戲園的最好進口。一會兒終于擠倒一堵土墻,局面更加混亂,民兵也鎮壓不住了。隔了一天,傳出了驚人的消息:昨晚馮村戲臺踩死一個老漢。
成千上萬的人們在一塊小小的地段擁擠、踩踏,他們用血淚、狂熱甚至生命危險,譜寫了一頁“史詩”,上面寫滿了虔誠、崇拜、信仰等愿景。這是農業文明背景之下,鄉村精神生活的一個恐怖和幸福交織的范例。
那時腦子里沒有法律一說,沒有索賠的念頭。死了就死了,家屬自認倒霉。好在,老漢是沖著過癮去的,臨死之前還看了一場好戲。
文革中間,樣板戲聽多了叫人心煩。1972年天,政策略微松動一些。各地可以根據當地情況,排演一些地方戲。運城蒲劇團排了個小戲《把渡》,由王秀蘭王民孝合演。戲是配合當時的“割掉資本主義尾巴”,把住渡口,不讓投機倒把過河。演員卻是一流的名演。幾年了,由于隔離審查,王秀蘭很難出臺。消息傳出去,好多人私下都在等待這一天。戲排成了,決定先在鹽化局禮堂給黨代會演一場,也算是審查演出吧。不知誰打探到了消息,一傳十,十傳百,禮堂外邊很快聚集了上千人。沒說的,要看戲。把門的工人糾察隊態度蠻橫,猶如火上澆油,矛盾激化,千余人在門外和糾察緊張對峙,沖突一觸即發。鹽化的工人大喊:我們掃硝擔鹽,你們看王秀蘭,這是欺負我們工農兵!把門的解釋以后會公演,人群大叫:不行,今黑了非看不行!后面有人喊:不要跟他們講理,進!面對一群怒火燃燒、面孔因憤怒而扭曲的人群,把門的早已嚇破了膽,哪里敢阻擋,于是人流一涌而進,千余人把禮堂團團圍定,進去的靠墻根站著看,或者蹲在過道看。進不去的,就圍在禮堂外。隔著窗玻璃看個燈影。不一會兒,外面有人叫喊:打板的劉雙虎師傅進不去了,沒法開戲,大家讓一條路!哪里有路,眾人把劉師傅舉起來,傳進了禮堂。開戲了,一張一張憤怒扭曲的面孔才松弛下來,沒事了,看戲。
文革中間社會治安那么嚴酷,當局也沒有抓捕“搗亂分子”,畢竟是為了看戲么。
事隔幾十年,當年的當事人依然難以忘掉那一刻的群情激憤。說起來,已經成了趣聞。當年擠進去以后,隔著玻璃窗,多數人只能看到舞臺的一角。演員轉到臺口左首,右一側的人群才能看見有身子舞動;轉到右首,再輪到左邊的看那么一剎那。其他時間,就看著光影聽曲子,即使這樣,也沒有一個人離開。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蒲劇一代新人長成,以武俊英為代表的一批唱家迅速在運城家喻戶曉。《送女》、《蘇三起解》唱到了北京,北京的專家都拍手叫好,評了梅花獎,運城的老百姓一聽說來了武俊英也是擠破腦袋的看戲。這年秋日的一天,地蒲的臺口安在峨眉嶺半坡的上郭鎮。天陰沉沉的,濃云密布,像是要下雨。似雨非雨的,真難為人,戲還演不演?看,還是不看?王思恭行長從運城請戲回來,離上郭還有十五二十里,就看見公路兩邊三三兩兩一堆一伙的人群。他們走走停停,不時停下腳步互相打聽什么,從坡下往上遠望,黑色的人影逶迤十幾里。十幾里的人群,十幾里的猶疑。王行長知道這是想看戲又怕劇團不來,鄉親們正在被兩難折磨著。他告訴身邊的行人:有戲,劇團在后頭,來了。身邊的馬上告訴同伴:來了。立馬,歇息的起了身,行走的步子緊了,騎車的蹁腿上車,帶人的躍上后坐。不停地聽到后面給前面傳遞:來了。像一支行軍部隊傳口令一樣,從峨眉嶺下二十里一直傳到上郭鎮。
上郭鎮位于運城、萬榮、臨猗三縣交界處,大路通衢,四通八達。到了上郭,又是一聲“來了”從這里傳出,向三縣邊區十多個鄉輻射。條條通往上郭的路上,都有“來了”在口口相傳,就靠這口口相傳,當晚上郭鎮涌來一萬多人。街巷密密麻麻到處是人,涌動的人頭像水開了鍋。劇團通過,人們伸長了脖子尋找武俊英,吃飯的端著碗湊過去。演員蹲下吃飯,圍觀的人群立刻層層包圍了,圍起看你咋個吃飯。上郭解放以來,從沒有召集過如此規模的盛會。
來了。
來了。
行路人之間的相互傳話,聲音不大,但一會兒能把天地響徹。如沉雷滾過,在大地不脛而走,穿越黃土鄉垣,引發的是欣喜和想望。仁慈的地母有靈,也會為之動容。他們的奔走,他們的聚散,就是為了看一回蒲劇。值得嗎?值得。他們的勞苦,他們的辛酸,他們的災難,他們的幸福,哪一宗和蒲劇無關?他們的千古疑問,哪一條不是從蒲劇中尋找答案?一聲來了,扣響了心扉。大地飛掠過一片“來了”,是蒲劇對鄉親們最親切的回應。
任什么時候想念蒲劇,都會聽到天地之間有一個聲音在輕輕回蕩,在人心漾出美麗的花紋。你呼喚他吧,他會鄭重地應答:
來了——!
關于“十九世紀的感動”
我的鄉親面對蒲劇的著迷,看戲的動情,常被稱為“十九世紀的感動”。
人類的藝術欣賞歷程,大體上經歷了十九世紀以前的古典主義現實主義,二十世紀前半頁的現代主義和后半頁的后現代主義。具體到各個國家地區,又各有前后不同。
“十九世紀的感動”所指為何,沒有具體界定。不過以通常的理解,這肯定不是一個時間概念,它是時代的概念,是商品經濟沒有發育沒有發達的時代的感情,是工業時代以前的感情。
那么,在我們,改革開放以前,都可以包括在“十九世紀”這個時間段落。
那么,它是指一種過時的感情。
忠君保國,孝悌仁義,重義輕利,誠實守信,朝堂的忠奸對立,夫妻關系中的絕對忠貞,朋友交道中的自我犧牲,為一個然諾不惜重創,等等,這些顯然是過去時代的東西了。
我們眼前更多看到的是:政界的權力爭斗,商場的輸贏轉換,情場的得意失意,股票走勢,地產起落,還有小資情調,流行時尚等等。
工業時代的感動,消費時代的感動,往往是利益驅動下的感動。力量決定勝負,勝負生產感動。感動少了,遺留的那些感動,也往往變了味。
看傳統戲,我們經常能夠從慘烈的犧牲中領會一種神圣的崇高。我的鄉親們,當年粗糧加菜葉,徒步行走十里百里,為的就是在這種精神世界超升一回。吃不飽穿不暖,奔一出戲而去卻沒有任何猶豫,相比之下,淳樸的鄉民,浮華的成功,精神世界,誰家豐富,誰家貧瘠呢?進步發展,我們同時也失卻了什么?
由于地理的偏遠,一個失傳的精神世界往往在窮鄉僻壤得以保存。到那里去,你能找到那些失傳的感動。
鄉村記憶中經常包含著寶貴的古典元素,我們沒有必要斬草除根,連這些古老的種子也徹底殲滅。傳統文化的載體,現在只留下這么一點可憐的地盤,如果連這一點也要徹底剝奪,那么它真的就一無所有了。
面對傳統戲,我們能感覺到莊嚴上升,神圣上升,品質升華,人性升華。
上世紀,留下了多少懷戀和悵惘……
(本文為作者長篇散文《大音絕唱——蒲州梆子敘事》中的一章,全書即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