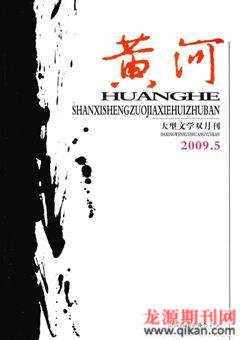對鄉村世界的“生活流”展示
張玲玲
打開王秀琴的中篇小說《閘門》,一股鄉村原生態的生活洪流就會撲面而來,雖然,其中肯定難免會出現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的現象,但也正是由于這些與正面道德價值、品質相對應的負面因素的存在,才使得小說具備了可貴的真實性和原創性。作者很顯然把小說變成了展示生活的舞臺,一個故事接著一個故事地娓娓道來,一個人物接著一個人物輪流出場,其內容之豐富、敘事之流暢,全然沒有了一般小說中以一個事件為中心或一個人物為敘述視角的緊湊和凝聚,也缺少了運用巧合、偶然等手法而形成的戲劇性效果。小說更多的,是把正在變化和流動著的生活長河中的無數個片段交織在一起,從而組成一個流線式的藝術文本。可以說,這種鄉村生活的展示,是與作者的敘事方式,與作者的主觀意圖緊密相關的。有什么樣的寫作意圖,便會有什么樣的敘述方式,表達的主題,總是在呼喚與之相對應的語言形式出現。所以,在進入小說文本內容之前,我們首先應該對小說的情節結構做一整體的把握,從而厘清這種敘事效果和特定敘事方式之間的暗合關系。
不管王秀琴是否已經意識到,小說實際上采用的是一種“去中心化”的敘事策略。所謂“去中心化”,便是指:“一部具體的小說文本中,作者既放逐了中心情節,也放逐了中心人物。這樣出現在讀者面前的,就是一部既缺乏中心情節也不存在核心人物的小說文本。”(王春林語)在《閘門》中,沒有特別突出的情節和事件,甚至沒有特別突出的主人公。小說中的人物,似乎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存在理由,都在一定意義上承擔著作者的藝術思考和價值訴求。在閱讀《閘門》的時候,如果讀者是帶著一種獵奇或者體驗式的心理狀態進入文本的,那他一定會大失所望。因為它給讀者提供的是另一種閱讀享受,在這里,作者直接連接起了生活和藝術之間的生命臍帶,從而展示出了一種平淡樸實,但卻活生生的眾生百態。《閘門》一共二十二節,作者在每一節的設置上似乎都有一個拐點,從而把藝術觸角伸向了生活的另一領域。可以說,這樣的一種敘事策略,與讀者習慣于集中緊湊,習慣于圍繞一個事件、一個人物來展開敘述的審美期待和閱讀習慣是背道而馳的,即使是對作者而言,也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挑戰。如果處理不好,小說便會淪為生活現象的羅列,使讀者產生內容繁復、冗長之感,進而失去小說應有的藝術品格和內在品質。但是,王秀琴的這篇小說,卻應該說是談得上成功的。雖然我們不得不承認,小說確實缺少了傳統小說以故事情節取勝的緊張刺激和現代小說中以意境取勝的詩意氤氳,但這種“去中心”的敘述方式,卻無疑可以被看作是作者對現實進行藝術關照的另一種方式,是其審美旨趣和藝術態度的具象體現。
具體來說,小說的敘述時間是從“晚秋”開始,直到次年“二月二沒幾天就到”的前后幾個月的時間,但實際上,小說從第四節便進入了臘月人事的描寫,這樣的描寫一直持續到小說的最后一個章節。因此,可以說作品基本上敘述的,是從農歷臘月與正月這兩個月時間內發生的鄉村故事。在這段敘述時間中,作者囊括了比一般“中心化”敘述的小說要多得多的情景內容:既包括了高福由于帶領村民作務梨樹致富后樹立起在全村的威信,以及由此而可能發生的金明與之產生的選舉之爭,雖然對于高福來說,這是無心插柳的事,但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鄉村的政治斗爭和權力爭奪;同時,小說還描寫了高福與蘇蘇之間的私情、高福妻子子丑與蘇蘇的爭斗以及子丑對高福的寬容大度,從兩個側面刻畫了子丑的性格特征;此外,九叔對大局的把握和對人情世故的洞察,以及以秋根和德富為代表的農村多樣化的經濟發展方式,也都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與此同時,作者還借金明妻子的死亡,而對農村喪葬儀式進行了描寫,借高福的女兒丟魂一事,揭示了現代農村所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思想,等等等等……雖然這里已經列舉了這么多內容,但仍然不能窮盡作者給讀者提供的全部信息。但是,從上面的羅列中,我們已不難看出作者試圖在這篇并不算很長的小說中展示鄉村世界全貌的努力。正因為她把如此眾多的情節匯入了生活的洪流之中,因此,小說帶來的就是鮮活而混沌的鄉村生活圖景,它是一種濾去了粉飾和雕琢的生存真實。在其中,我們既看到了鄉村鄰里之間的互幫互助,和睦共處,同時也看到了存留在民眾中的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和農村中的權力斗爭。很顯然,作者是在以一種“生活流”的敘述手法結構情節的。作者包括敘述者都似乎已經“退出”了小說,似乎在對生活進行一種客觀、全面的描繪和展示。相對于傳統小說慣用的“焦點透視”的敘述視角,那么作者在這里采用的便是“散點透視”的敘述視角,即不再圍繞某一事件做集中描寫,其他一切情節都為這一中心事件服務。在小說《閘門》中,我們看不出哪個事件更占主導地位,甚至主要人物也變得有些模糊不清,作者似乎是對每個事件都是“平分秋色”,盡可能詳盡本真地描繪出民眾的生活狀態,呈現原汁原味的鄉村風土人情,從而使眾多的情節內容都交織在“生活流”這一網絡之中。
非常明顯,“去中心化”的敘述方式帶來的一個必然結果,就是主要人物的不確定、不明晰。有時,一個反復出現的人物形象,也并不是作為小說全部意義的主要承擔者,他在文本中起的只是一種結構性作用,是作者選取的一個敘述視角。同時,“去中心化”的主要特征,本就是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盡可能真實地反映現實。因此,作者的態度更傾向于客觀、冷靜、理智,“不虛美,不隱惡”,用克制的情感面對作家所置身的現實生活。然而,再怎么克制,一種思想傾向的存在也是必然的。在小說《閘門》中,不管作者采取了怎樣的一種敘事策略,都不能抹殺一個清晰的思想藝術主旨的存在。說到底,小說旨在表明的,就是存在于底層社會中厚重而混沌的人情人性。小說中的人物身上都帶有鄉村天然的樸實、真誠、善良的美好品質,都散發著充滿溫情的人性光輝。
高福是一個首先在讀者腦海中刻下印象的人物形象。在小說開頭,他一出場作者便賦予了其精明、有頭腦、有威信等正面特征,這一正面形象在隨后的敘述中更加得到強化。他本無意于村主任一職,但卻由于有經濟頭腦,通過種植梨樹帶領村民發財致富而深得村民的擁護和信賴,最終陰差陽錯地被選為村主任。但在面對自己的政治競爭對手金明的時候,他卻還是毫不猶豫地愿意慷慨解囊幫助其妻子看病做手術。由此可見,高福在權力和人情的對立下仍然能堅持道義的可貴品質。同時,雖然他與蘇蘇的婚外情有悖于傳統倫理道德,但是在小說中仍有著內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正如子丑在與兒子文興的對話中說到的:“男人有本事,才敢紅杏出墻,也才敢做哩。沒出息、窩囊的男人,連自己的老婆都攏不住,他敢想嗎?芽你爹干了那事,娘生氣歸生氣,可心里不記恨你爹,我知道他的心還在咱這個家里。娘也老了丑了,還能不叫你爹走一走神兒?芽”而事實上,也是蘇蘇先主動出擊的。她“戀高福,粘高福,喜歡高福,是因為自己丈夫秋根身上沒有高福那股子勁”。她不僅看重高福身上的橫勁兒、闖勁兒、韌勁兒、鉆勁兒,而且更看重高福骨子里那份風情。面對有著苗條身材和如雪肌膚的蘇蘇的攻擊,高福自然是難以阻擋和不可抗拒的。即便如此,他對其三角關系的處理方式,也能夠取得讀者同情和理解。在面對秋根用自己的妻子和女兒作為交換條件要求高福替他償還貸款時,高福表現出了讓人敬佩的男人氣概。他雖然對秋根的無恥所不齒,但卻同情蘇蘇,慷慨地拿出自己的存款作為對蘇蘇的補償。在對子丑的態度上,也表現出了男人可貴的責任心和道義感,他“邊摸邊想,子丑的皮膚就是不如蘇蘇的細滑。這個念頭一起,高福便趕快彈壓住了。他告誡自己,這樣對子丑不公平”。最終,高福在子丑的感化下與蘇蘇斷絕了關系,這足可看出“他的心還在咱這個家里”。
如果高福的形象還帶有一點現實的因素,還有一點“人間煙火”味道的話,那么九叔更像是作者刻意造出的道德化身。他閱歷豐富、洞察人情,作者對他的身世、經歷并未作介紹,他的形象是在與子丑幾次打交道的過程中逐漸清晰起來的。他先是幫助子丑處理羊下水,后來又幫子丑的女兒雯雯招魂,最后,還用日子如放調料的深刻寓意別出心裁地化解子丑和高福之間的矛盾。作為村里經驗最豐富的老人,他便成了子丑的依靠和信賴對象。子丑把九叔定義為“玻璃人”。但僅僅在生活中“身懷絕技”卻并不足以承擔作者所要寄托的思想主旨,實際上,更重要的是其身上所具備的道德力量和人性品質。在子丑發現了高福與蘇蘇的不正當關系時,適逢高福剛剛被選舉為村主任,在子丑聲淚俱下的哭訴下,九叔勸告子丑要顧全高福的形象,“男人的心不是想拴就能拴得住的……你給高福留條回家的路,心有多寬路也有多寬哩”。雖然是很樸實的幾句話,但我們都可以感覺得到作者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時,所采用的是一種感化、包容的態度,即使是子丑自己,也認為“家丑不可外揚”,“只是跟九叔說說罷了”。可見,雖然作者盡可能地如實展現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作者的價值立場和道德判斷并未“缺場”,她并非像鏡頭一樣對生活作一“鏡像式”的描繪。縱觀全文,九叔的出場次數并不多,相對于高福、子丑、蘇蘇甚至秋根來說,都并不占優勢,但他卻像是個幕后的觀察者,一直貫穿于情節發展的始終。小說中哪有爭奪,哪有斗爭,哪就有九叔出場,而九叔的出場實際上也就是作者態度的到場。通過九叔的“點化”,人物之間的矛盾都得到了圓滿的解決。他不僅化解了高福與子丑的疙瘩,就連高福和秋根之間,九叔帶有“玻璃人”性質的啟發姿態也適時出現。秋根向高福下了戰書之后,在他們會面的地方出現九叔的一副對聯:“名場利場無非夢場何必做出一副醉樣,冷藥熱藥總是好藥終醫不盡遍地炎涼。”對于這副對聯的存在和對全文的作用,我們不能視而不見。九叔就像一個看破俗世凡塵高高在上的老者,在用一種通透的先驗性的姿態俯視人生,并引導人們走向相互理解包容充滿人性溫情的和諧狀態。這副對聯也正是小說敘述的全部核心,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藝術上都使小說有了一個質的提升,把小說的藝術主旨推向了高潮。這,或許也正是作者的根本用意所在。
最后,有一點不能不提出的是,無論作者運用了哪種敘述手法,表達了怎樣的藝術旨趣,小說在結尾的處理上可以說是不盡人意的。我們看到,作者有意安排了一個皆大歡喜的大團圓結局,因為這本身就不符合人物性格的發展邏輯和生活的實際。尤其是,這篇小說作者還是按照“生活流”的方式進行敘述的。因為“生活流”這一創作原則的內在規定性,即是盡可能地做到客觀、全面地呈現生活的全貌。但是,王秀琴的這種結尾方式,卻明顯地背離了她的“生活流”敘事原則。結尾的這種處理方式,帶給讀者的感覺,就是強行加進了作者個人的情感意志,因而使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受到了一定的影響。實際上,在前面的章節中,一些人物形象已經成功地承擔這一任務,比如子丑(由于篇幅原因所限,這里沒有展開討論),比如九叔。因此,作家完全沒必要專門設計這樣一個失敗的結尾方式。但即便如此,《閘門》仍然是瑕不掩瑜,總體上說是一篇比較好的小說。正因為如此,我們期待王秀琴會寫出更加優秀的小說作品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