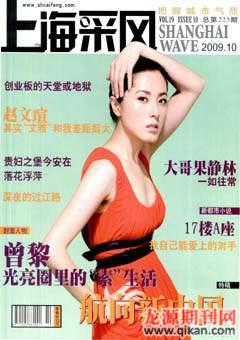顧曉鳴:上海大市民文化的涅槃之路
胡凌虹
顧曉鳴
現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旅游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敘事文化傳播公司總監、上海市信息化專家委員會委員、上海群眾文化學會副會長、上海電影評論學會副會長。2003年為IBM的ThinkPad X系列筆記本電腦擔任一年的形象代言人,此舉開了中國學者拍廣告的先河。在學界顧曉鳴被稱作“學者型的文人”和“文人型的學者”,能夠非常敏銳地發現科技和商業的前沿,思維發散,想象力豐富。主要代表著作有:《追求通觀》、《我走路還是路走我》、《猶太充滿悖論的文化》,主編了《中國的智慧》、《世界的商人》、《中國傳統商人》、《網界辭典》、《網址導航》等叢書。
上海大市民文化的內涵在于雜
記者:顧老師,今天想請你談一下上海文化這個話題。首先請問,你認為什么是上海文化?
顧曉鳴:上海文化有兩塊,一塊是大市民文化,一塊是小市民文化。上海的大市民文化首先體現在楊樹浦那一帶。開埠以后,英國革命、乃至更早的文藝復興的第三波來到第三世界,上海承接了這一波,形成了上海的大市民文化。上海的開發首先沿著黃浦江往楊浦區方向發展,電力、電燈、橋等一大批基礎設施建立,跟世界技術同步。除了楊樹浦,還有浦東一塊,倉庫、船塢等率先在浦東出現,宋慶齡也生活在川沙。其實浦東大道有一批比浦西更早的東西,只是現在這些原來的建筑被拆掉了。上海的石庫門和新式里弄相當于以前“外資企業”的宿舍,其中也是當時高級白領的住所。還有虹口、閘北那一帶,1910年左右,已經形成了很深厚的文化土壤,比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更加厚重。總體來看,全國很多文化是從上海文化里滋生出來的。白話文、漫畫、寫實畫、《資本論》、《共產黨宣言》等先在上海出現。上海話成為了國語和外文之間的橋梁。從浙江以及沿蘇州河一帶過來大量的文人,如李叔同、魯迅、陶行知、周韜奮等,發展了上海的文藝、理論、教育、出版等文化事業。上海的新式大舞臺,把全國最好的人才、最好的戲都吸引過來,這些草臺班的戲劇經過上海這個大舞臺,通過上海優秀的觀眾完成了現代戲劇的轉型,有了全國性的影響。同時,開埠以后外國流行的東西也涌進上海,如好萊塢的熱門電影、爵士樂等,電話系統和電臺等傳媒也與世界同時建立。上海出現了很多中西合璧的好房子,如朱家角富豪民居、圣約翰大學(華東政法學院前身)等。在這個大文化背景下,共產黨在這里成立,三次工人運動、五四運動、五卅運動都在上海舉行,這不是偶然的。1927到1937年間,上海和南京比較發達,商業方面上海又超過南京,當時強生出租車公會等已經建立;和帝國主義有聯系的資產階級開始了城市規劃和城市新文化運動,提倡講衛生講文明講禮貌。所以今天講的城市運動、社區建設、城市居民的自我教育運動,已經在當年做了嘗試,更不要說像外白渡橋市民自發斗爭那樣的市民運動了,在全國范圍內具有先導性的意義。

記者:上海大市民文化的內涵或核心是什么?
顧曉鳴:上海文化的多樣性和雜糅性。全世界最厲害的文化是英國文化,英國地理偏遠,不像法國那么優雅,英國人吃飯其實比較粗陋,但為什么英國工業、文官制度等,直到晚近的創業產業那么發達?因為英國是一個多種族民族,生活著各種族的人,彼此容納融合。上海跟英國有相似的地方,在上海的大文化里,雜交是天然的,上海的學科之多,僅次于北京。在上海,各種文化藝術都有,上海話南腔北調。上海人本身是雜融的,以前根本沒有你是外地人、我是上海人的思想,但是后來慢慢封閉了,本性上開始排斥外地人。你看馬路上那么多的雕塑都是模仿外國人的。之前我寫過一個方案,主張在上海豎立56個少數民族的雕塑,以前上海的同鄉會太多了,今天也要讓從全國各地來上海的人感覺上海是第二故鄉。上海人應該以雜為光榮,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是《阿拉不是上海人》。
上海不要變成外國摩登的傳聲筒
記者:剛才說了上海的大市民文化,那么你說的上海小市民文化又指什么呢?
顧曉鳴:上海沒有真正的本土文化,沒有根。在成都、杭州、長沙等城市的公園里,經常可以看見一些老大爺在唱京劇。但是在上海,沒有這些老的文化底蘊,對洋的東西抵抗力很小,一進來馬上就模仿了,上海變成一個國際文化的前沿,外國摩登的傳聲筒。在過去封閉的條件下,上海借著開放的優勢,可以稱老大。但是現在西湖旁邊國外的頂級店都陸續開張了,成都舉行的咖啡師比賽上海尚未舉行過,上海這方面的優勢越來越小。同時,廣州的高級賓館,老百姓能進去喝早茶,但是上海的大賓館,普通老百姓是走不進去的,外灘X號之類更是拒老百姓于千里之外。在上海,一部分人依附于外國,走在世界文化的前沿,使勁吹噓著上海的豪華;但是另一端,老百姓過著簡單的大餅油條的生活,呆在上海時尚的屋檐下,不是房子里面。他們實際的居住條件很差,心態很小,跟鄰居斤斤計較,形成上海特有的小市民文化,以及特有的自卑心理。
記者:長此以往,這種小市民的文化或心態會有怎樣的負面作用?
顧曉鳴:深層次的自卑以后會產生一種反常現象,一方面斤斤計較,另一方面要充作老大,要去掙一個面子,凡事都命名為“第一XX”。結果看到富人、洋人不由自主會軟,同時又覺得我跟富人在一起了,對于別的地方的人,認為我比你們闊了,我跟你們不一樣了,不跟你們比高低了。這種所謂的“巴”文化,延伸到城市建設中,就恨不得把所有的街道都變成外國版的。比如現在的淮海路,居民遷走了,留下的都是手表店等品牌店,這樣的淮海路與老百姓有什么關系?但是現在還是不斷地引進外國的東西,像阿瑪尼這些店在國外都是“沖頭”去的,上海卻仍在山寨版地克隆人家。新天地是“田螺里面塞紅腸”,把外國廉價的東西都塞進去了。如今杭州西湖全開放,外地有這個自信,但是上海還是盼著迪斯尼,模式也是克隆人家的。湖南臺搞超女,上海臺也跟著學。于丹、小沈陽紅了,上海就跟著起哄。上海沒有辦法創造出自己的東西,一方面想做老大,一方面老克隆人家。這種淺薄的小市民文化很危險,第一心態不放松,第二為了保險系數大,綁人家成功者,模仿多、山寨多,結果喪失了文化的創造力,沒有主心骨,跟大上海不相吻合。
記者:幾十年來,上海有著非常好的大市民文化的積淀,為何現在小市民文化卻越來越彰顯?
顧曉鳴:一方面是因為上海存在一個誤區,以為把東方曼哈頓,東方好萊塢弄起來就是現代化了;另一方面,解放前有一些西學的底子,但是建國后中斷了,現在電影業的領頭地位中斷了,廣播、電視業的全國影響中斷了,市民文化的“夜總會”——“大世界”也沒有了。早年傳教士進來的時候就把油畫引入上海,但是解放后上海很好的美術學院也沒了。幸好上海音樂學院沒有中斷,小提琴、鋼琴、聲樂等培養出了很多人才。上海有大聰明,上海還有著一個非常大的產業基礎,產業功能,擁有著很多學者,有新民晚報等媒體,這些表明大市民文化還在內部支撐。但是我們現在宣傳的往往是小聰明的東西,什么老年爵士樂隊、和平飯店、“夜上海”之類。1995年我做《當代電視》的改版主編時,就發表過文章,警告張藝謀他們,上海絕對不是妓女加流氓,他們搞風月,看到的恰恰只是小市民的東西。
上海要認認真真向全國、向國外學習
記者:既然有很好的基礎,上海文化要發展,你有什么好的建議?
顧曉鳴:上海要重建有全國各地文化雜交的真正的上海文化,做中國文化的特殊版,只有先做中國文化才有上海文化。一方面,上海一定要向全國學習,我的名言是:上海是長三角的兒子,不是去做老爸。另一方面,上海要認認真真地向國外學習,要真正地懂得外國文化。上海有這個基礎,但是上海人并不用功,現在一些全國的外語比賽中,上海的名次都不是很高。上海應該是講到韓國,就有懂韓國的人,講到土耳其就有土耳其通。全世界各種文化最懂行的,上海都有代表人物才好。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上海也不要妄自菲薄,以為外國人的都好,現在證明,外國的東西也未必好,像浦東機場,資源浪費得不得了,里面要走一里地,要用電瓶車,這就是太相信外國人了,沒有自己真正的眼光。此外,如果我們一直把垃圾式的外國交響樂、歌舞,或者老套的東西引進來,以商業化的形式來做,就會使藝術變成附庸風雅。最后講一點,成也商業,敗也商業。大市民文化為什么這么厲害?近代的全部秘密在于,商業真正造就了文化。美國文化的秘密就是美國的商業,消費主義,營銷、廣告、公關,都納入整個生產體系,民眾參與了整個創造。之前上海的戲曲、電影也是這樣,老百姓要看,就不斷改進。敗也商業,如果不吸納全國各地的文化,不懂得各種各樣的外國文化,而是簡單克隆人家,反而會壓制自己的文化創造力,使自己的審美趣味越來越淺薄。上海人懷里揣著顆大鉆石,但自己還不清楚,把周圍反射過來的光影當做寶貝,其實反射的光不是鉆石本身的,不要迷戀這些光,要看清懷里的寶貝。所以上海只有通過打造自己的文化底蘊,進一步改革開放,把真正好的東西引進來,增加自信心,自主更新,這才是大市民文化真正的鳳凰涅槃之路,上海大市民文化才會迎來新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