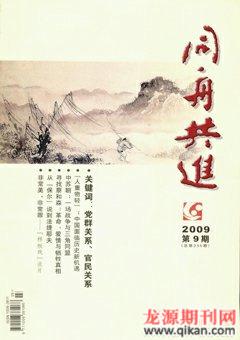尋找蔡和森:革命、愛情與犧牲真相
散 木
蔡和森(1895~1931),湖南人,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五四”時期旅法勤工儉學運動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之一。中共第二、三、四、五、六屆中央委員,中共第五、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革命烈士。
向警予(1895~1928),湖南人,土家族,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中國馬克思主義運動和婦女運動的先驅之一。1918年參加毛澤東和蔡和森領導的新民學會,1919年組織湖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并親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共第一位女中央委員和第一任婦女部長。革命烈士。
【“向蔡同盟”驚世駭俗】
蔡和森和向警予是一對著名的革命情侶和革命夫婦。他們的結合,曾被稱為“向蔡同盟”。
似乎是電視劇《恰同學少年》中的鏡頭:“五四”后不久,一批湖南青年男女登上“盎特萊蓬”號法國郵輪,赴法國開展“勤工儉學”運動。在一個月有余的漫長航程中,蔡和森、向警予兩人由一起觀看日出、討論和學習,最后談及婚姻問題。當年他們都反對舊式婚姻制度,尋求新式“愛情”。當郵輪停靠在終點站馬賽港時,他倆驚喜地發現愛情之舟原來已經揚帆啟航了。在蒙達尼,他們開始了“勤工儉學”的生活,同時,兩人經常交換詩作以表達彼此的“愛戀”及對“革命”的向往。1920年5月,在蒙達尼這個法國小鎮,他們宣布結合,隨之有了一本見證性的詩集《我們一起向上看》(一說《向上同盟》),分贈給大家,由此人們稱之為“向蔡同盟”。
兩人的好友毛澤東獲知這一消息后大為贊賞。1920年11月26日,毛在致羅學瓚的信中說:“以資本主義做基礎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絕對要不得的事,在理論上是以法律保護最不合理的強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戀愛……我聽得‘向蔡同盟的事,為之一喜,向、蔡已經打破了‘怕,實行不要婚姻,我們正好奉向、蔡做首領,組成一個‘拒婚同盟。”原來,革命者如毛澤東等,早年無一不是無政府主義者,這里的所謂“無”,是包括了人類“異化”的政府、國家乃至婚姻、家庭的。在他們看來,“向蔡同盟”似的男女結合,正是“拒婚同盟”的實踐。隨后,張申府和劉清揚,以及后來毛澤東與楊開慧、李富春與蔡暢等的結合,都是“向蔡同盟”模式的翻版。
早在向警予擔任長沙周南女校校長之時,人稱“女圣人”,是品學兼優的女子。有一位名叫周則范的軍官,支持女子教育,但條件是要向警予做他的二房夫人。向警予的父親懾于周的權勢,只得同意。向警予卻死活不肯,她只身沖進周家反抗,并發誓“終生不嫁,以身許國”,后來及遇蔡和森(當時長沙有“湘江三友”之說,即長沙城里有三位青年思想最為先進:蔡和森、毛澤東、蕭子升),又雙雙負笈歐土,這兩位志同道合的男女便發起了向封建制度和習俗的挑戰。他們宣布實行“同盟”式的自由結合,眾多青年紛紛引為先進而效仿。
【敢于打破“死亡婚姻”也需要坦蕩胸懷】
“向蔡同盟”的結局是讓人意料不到的。許久以來,這仿佛是一個禁區,被剝奪了“知情權”的人們,兀自沉浸于對“革命與愛情”的迷戀中,歷史的真相卻非如此。
1921年年底,蔡和森等因參加和領導學生運動被法國當局遣送回國,不久,已懷孕的向警予也回到了上海。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上,蔡和森當選中央委員,向警予當選候補中央委員。蔡和森擔任了中央宣傳部第一任部長,向警予則擔任了中央婦女部第一任部長。這對戀人實踐他們在法國結盟時的理想(當時他們雙手共持《資本論》拍攝了一張新婚照片,向警予將照片寄給家鄉的父母,在信中她說:“和森是九兒的真正所愛的人,志趣沒有一點不同的,這圖片上的兩小也合他與我的意。我同他是一千九百二十年產生的新人,又可做二十世紀的小孩子”),開始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奮斗了。為此,蔡、向還共用了一個筆名——“振宇”,在蔡和森主編《向導》周報期間,經常用這個筆名發表評論文章,而“振宇”就是“警予”的諧音。在此后的革命歲月里,兩人還生養了一雙子女:蔡妮、蔡博。
然而,時間到了1925年初,隨著另一個共產黨人彭述之(后成為中國“托派”的首領)的介入,“向蔡同盟”遇到了挑戰,最終宣告“解體”。對此,羅紹志在文章中說:向警予的“追求”,“不但表現在她對自由婚姻和美好愛情的向往,同時也表現在她對破裂婚姻和感情正視的態度。幾十年前,他們敢于自由戀愛結婚……為眾多國人不齒;而后又敢于打碎死亡婚姻,更是驚世駭俗。”這一番話,對不曾知曉其原委的人來說,想必會大吃一驚。
其實,“革命者”也是千人千面的,只是過去我們的描寫太刻板太單一,掩蓋了革命者鮮活的個性,久之則不免失真。比如蔡和森,曾與之同赴法國的冶金專家和僑民沈宜甲在《我所知道的早期之蔡和森》的回憶中說:蔡“受墨子影響很大,反孔反儒,又受家鄉譚嗣同影響甚深”。蔡的一位同窗評論其人云:“蔡先生為人莊重嚴肅,不茍言笑,說話條條有理,初很動人。但經久總是那一套,只可使中小學生愛聽,凡程度較高者則不見重。”這也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實際狀態,如蔡和森,“對本國人只有墨子、譚嗣同、毛主席三人,對外則每每提及列寧,甚少及馬克思,因那時中國尚無此資料。但最令我頭痛及生氣者,即他口口聲聲云,俄人為世界犧牲,乃中國最好的朋友,中俄永無大戰。我聽了厭煩。和森只偏—方:一為只問政治革命,不及其他;一為此革命只以取消地主為最要,對其他建國之事則向不及”。
從全面的“審美標準”來看,烈士蔡和森當然不可能是“完人”,性格上有缺陷的一面,所謂激進主義、破而不立等,這也難免影響到他的生活。據蔡和森的鄰居回憶:與蔡做鄰居是一樁苦事,因為“他有那么多干不完的工作、寫不完的文章,他的窗口徹夜燈亮著,使你不忍心休息”。蔡和森還不時忍受著哮喘病的折磨,加之生活窮困(為此李大釗曾寫信給上海的胡適,希望他幫助蔡出版書稿以救急),在這種條件下,“革命與愛情”也就有了變數。
中共四大之后,彭述之以中央委員身份接替多病的蔡和森,擔任了中央宣傳部部長(當時蔡和森專職主編《向導》周報)。為了方便工作,蔡和森夫婦、彭述之夫婦和秘書鄭超麟一起住在宣傳部的寓所。據說彭述之是一個“風流才子式的革命者”,不同于“枯燥”的蔡和森,彭述之有瀟灑的舉止、幽默的談吐,這竟使得一向不茍言笑、被人稱為“馬克思主義的宋學家”、“革命老祖母”和“女中墨子”的向警予有些動心了。
“墨家”蔡和森在工作上廢寢忘食,生活上不拘小節,為人父、人夫也未能盡到責任。向警予自己也不善理家務,思想上又崇尚婦女解放和個性自由。在“七年之癢”之期,蔡和森因領導五卅運動等過度勞累使哮喘病和胃病復發,離滬赴京療養,彭述之卻因兼管中央婦女委員會的工作與向警予有了更多接觸的機會,于是“向蔡同盟”趨于解體。等到病情緩解的蔡和森返回上海時,坦蕩的向警予對蔡和森坦白了一切。此后,同樣襟懷坦白的蔡和森要求中央開會討論這一問題。總書記陳獨秀認為這要由向警予自己決定,向竟“伏案大哭”,不能斷決。最后,中央主席團(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三人只好決定派向、蔡一同去莫斯科,希望這樣的“冷處理”會有個好結果。然而,最終兩人還是決定分手。
這段往事過去鮮有披露,只在若干當事人的回憶中有所記錄。這或許是為了不影響革命歷史的“莊重”,然而卻弱化了烈士的豐滿形象,阻礙了后人對他們的深刻解讀。革命者也有至情至愛,也有常人的悲歡和冀求,在“革命與愛情”的主題之下,他們的人生是色彩斑斕的,這絲毫影響不了人們對他們的敬仰,也絕不會因此而玷污他們毫厘。
【蔡和森對向警予的深切懷念】
中共六大結束,蔡和森在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心力交瘁之際,蔡和森在情感上需要寄托。當時也在莫斯科的,有他的湖南老鄉李立三夫婦。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純出于同情和關心,對病中的蔡和森給予許多照顧,慢慢地,兩人擦出愛情的火花。
“向蔡同盟”解體后,情侶或夫妻關系是不存在了,但廣義的革命同志(同盟)關系依然如故——所謂“革命與愛情”,有悖背,也有統一。
1928年“五一節”這天,國民黨湖南軍閥在長沙公開處決此前在漢口法租界被捕的向警予。得悉向警予被捕,蔡和森曾趕緊托舊友蕭子升出手相救,可惜未能如愿。這年7月,身在莫斯科的蔡和森含淚撰寫了向警予烈士的傳記,以此寄托他沉痛的哀思。
在這篇傳記里,蔡和森不僅敘述了向警予的成長歷史、性格特點,也記錄了他們之間的友誼與愛情。蔡和森寫道:向警予“忘寢忘食是她生活中的經常狀況。‘五四運動,她在鄉村號召廣大的群眾運動,終日講演,宣傳愛國主義。她感情熱烈得很,她為國家大事,常常號啕大哭。她相信所謂‘教育救國,她抱獨身主義,要終身從事于教育來改造中國。她絕對的與一般嬌弱的女學生不相同……她的言行完全像一個最誠懇的傳教師。她真實無比,她異常的勇敢,同時又很瑣細,她對于一點小小的事情,常常是要做徹日徹夜的去思想,去準備。她不知道別的欲望,唯一的欲望只是要她能干出‘驚天動地的事業,她是一個‘事業的野心家……她要到‘五四運動及‘新青年文化運動,在湖南青年急進分子中有很大影響。此時毛澤東、蔡和森等在湖南形成——‘新民學會,傾向于革命的社會運動……警予與和森多次談話之后,開始放棄教育救國的幻想而相信共產主義,同時警予與和森之戀愛亦發生于此。這是1920年1月15日在印度洋船中的事情”。
蔡和森繼續寫道:“警予與和森對于愛情的觀點,最初都是神秘的觀點,因此兩人之間,反因神秘的愛情而感到一種神秘的痛苦,1925年底同來莫斯科之后,遂至最后的分離。”
最后,蔡和森高呼:“偉大的警予,你沒有死,你永遠沒有死。你不是和森個人的愛人,你是中國無產階級永遠的愛人。”這泣血之辭,可謂痛怛徹骨,讀之令人動容。
“革命夫妻有幾人,當時蔡向各成仁。和森流血警予死,浩氣巍然并世尊。”這是詩人柳亞子悼念向、蔡的一首詩。1931年6月,蔡和森在香港秘密參加一個海員工會的會議,甫入會場,即受到叛徒顧順章的指認,當即被捕。不久,蔡被香港當局引渡給廣東的國民黨軍閥,隨即英勇就義。
【一樁歷史懸案:蔡和森烈士是如何犧牲的】
蔡和森是如何犧牲的?迄今說法不一。最有代表性的說法如《蔡和森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書所述:當時蔡和森秘密活動在香港,而與蔡和森比較熟悉的叛徒顧順章奉國民黨特務機關之令也秘密竄來香港,偵察蔡和森的行蹤。1931年6月10日中午,蔡和森冒險去香港海員工會參加一次緊急會議,臨行時,他抱著4歲的女兒親了親,然后對愛人說:“下午一點前我一定回來,如果到時沒有回來,那就是出事了。”果然,就在這次會議上,蔡和森被混入會場的叛徒顧順章認出,當即遭到國民黨特務的逮捕,當時被捕的還有施晃等5位同志。蔡和森被捕后,中共黨組織立刻派人進行營救,但他很快被引渡到廣州。此后,國民黨當局對蔡和森施用了各種酷刑,企圖逼迫他說出組織秘密。蔡和森大義凜然,橫眉冷對敵人,沒有吐露半個字,結果被打得血肉模糊。蔡和森受刑后被拖回監獄,躺在地上,動彈不得,難友們見了都傷心地痛哭,蔡和森卻鼓勵大家要堅持與敵人作斗爭,并說最后的勝利一定是屬于我們的。他還寫了一首詩,表示自己要為真理而獻身的精神。《蔡和森傳》這樣描述:“敵人的殘酷折磨,沒有摧垮蔡和森的堅強意志,他們想公開審訊,又害怕社會輿論的指責,于是決定把蔡和森殺害。這年冬初的一天,兇惡的敵人把蔡和森拉到監獄的墻邊,站著,在他面前擺上幾顆大鐵釘,對他進行最后的威脅。他巍然挺立,威武不屈。敵人咆哮著,將他的手腳拉開,用鐵釘把他釘在墻上。他痛得昏死過去,仍一聲不吭。愚蠢的敵人毫無辦法,便用刺刀一點一點地將他的肉割下來,最后一刀戳進了他的胸膛。蔡和森就這樣壯烈犧牲在敵人屠刀之下,充分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鋼鐵意志和堅貞的革命氣節。就在蔡和森被害前,共產國際已通知中共中央撤銷給蔡和森的處分,恢復他的政治局委員的職務,可是來不及通知,他就被捕了,直到壯烈犧牲,他自己并不知道這回事。蔡和森犧牲時,年僅三十六歲。”(編者注:1928年9月,劉少奇、陳潭秋以順直省委擴大會議的名義,批評蔡和森“組織上的極端民主化,破壞黨的集中制”等,并向中央提出處分建議。不久,向忠發和李立三再次點名批評蔡。此年11月,蔡和森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委員等職務)
釘、剮、戳,可謂殘酷之至,讀了這段文字,人們無疑對國民黨的殘暴有了更深刻的印象,也對壯烈犧牲的蔡和森充滿欽佩之情。在這里,無論傳記撰寫者的效果預期,或者讀者的閱讀期待,都融為一體。
但如果仔細審讀,在有關蔡和森犧牲過程的傳記書寫中,一些細節是不同的。最為“嚴酷”的一個版本云:“最后他被敵人用鐵釘將四肢釘在壁上,挖去雙眼,割去耳鼻,胸部被刺刀戳得稀爛,再用刑刀刺死。”這段描寫取自1936年(或1935年)莫斯科共產國際的一本刊物上署名“李明”的文章——《紀念蔡和森同志》,這里的“李明”,就是當時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李立三。
李立三的文字是在烈士犧牲后不久寫的,因而帶有一定的“權威性”,此后成了各種介紹和宣傳蔡和森犧牲過程的“母本”。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它并沒有引起人們的絲毫懷疑。
當年蔡和森的被捕和犧牲,其實都是在極端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的。國民黨當局從香港引渡蔡和森以及在廣州審問和處決蔡和森,都不可能對外聲張,更不可能刻意宣傳,這道理是顯而易見的。此外,迄今也未見有烈士犧牲時的見證人的回憶,于是,“蔡和森烈士是如何犧牲的”就缺少了最接近歷史現場的記錄。顯然,能夠說明問題的,只有歷史檔案了。
好在后來有黨史工作者發現了有關的敵檔資料,即國民黨廣東當局1931年8月關于蔡和森案的“原呈”密報,以及化名“胡世輝”的蔡和森的“供詞”,這也就成了最能說明問題的第一手歷史材料了。
在“原呈”密報中,有如下記述:“本年六月十日,梁(指特別偵緝隊的梁子光——引者注)由該員等合同港警探,在港洛克道四百六十四號三樓,破獲赤匪海委機關一起,拿獲赤匪要犯趙普生、方世林、李慶全、林劍彩、胡世輝(即蔡和森——引者注)、李丙等六名,并搜獲赤匪文件刊物,均留押在港政府。再經赴港交涉,旋由港政府通知,定于六月十二(日)晚,將赤匪首要胡世輝一名秘密遞解出境……”
密報中還有“并供開有在港澳各縣之赤匪姓名、住址,以及赤匪活動等情形”,但“業經密飭職隊派駐港澳密探等設法查拿,尚未查獲”等記述。顯然,這里所說的“尚未查獲”的原因,是由于蔡和森所供出的人名、地名等都是不真實的。蔡被捕后,堅不吐實,偶有一些“交代”,也是誑哄敵人。這份密報最后特別強調道:“除將該匪胡世輝即蔡和生一名,當經于(一九三一)八月四日執行槍決。并飭嚴緝供開赤匪歸案究辦,另據情分呈。”
論者謂:從上述摘引的“原呈”密報以及“胡世輝即蔡和生供(詞)”等敵檔資料中,可以說明以下幾點:第一,蔡和森是1931年6月10日在香港被英帝國主義當局逮捕的。第二,同年6月12日晚,他由香港被秘密引渡到廣州。第三,關于蔡和森最后被殺害的情況,并非像李立三文章中所說“敵人將其四肢攤開,釘在壁上,活活打死,胸脯刺爛”,而是1931年8月4日在廣州被“執行槍決”的。第四,從“胡世輝即蔡和生供(詞)”這份敵檔資料看,它不是蔡和森的親筆供述,而是審訊筆錄,“可以看得出,當時蔡和森并沒有主動向敵人供出什么真實情況”。
烈士們是值得人們尊敬和敬仰的,他們忍受了肉體的極度痛苦,卻讓信仰和精神升華,每一個后人都應該向他們致敬。
那么,討論“蔡和森烈士是如何犧牲的”這一話題有什么意義呢?在筆者看來,飲彈和被亂刀砍死等雖然都是壯烈犧牲,換言之所謂“歷史不重過程而重結果”,其實卻有不同。筆者雖然至今還不解當年在莫斯科的李立三通過什么渠道獲知蔡和森犧牲的具體細節,以及這些細節是否在傳輸時已有變形,或是否出于某種需要,但這種文字敘述實際上暗含了某種“革命邏輯”和“革命語言”,它在聲討敵人、褒揚烈士之余,也有一些帶有殘酷性質的“意圖倫理”成分。
老實說,我們寧愿歷史的事實是蔡和森烈士飲彈就義,而不是經受了人所不堪的酷刑(當然,如果這是事實,那只能說明敵人的極度暴虐)。
(作者系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