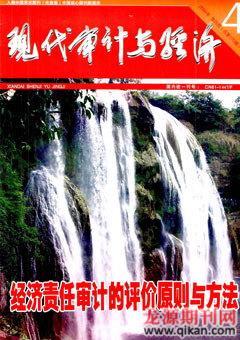“陜西冷娃”正解等二則
張 昆
“陜西冷娃”正解
張昆
關中、陜西人的身軀不亞于北方其他省市,比南方各省市要高大壯實得多。與身軀相關聯,關中、陜西城鄉男性居民中不少人是絡腮胡子(俗稱“串臉胡”、“毛胡子”),胡須垂胸的美髯公也不罕見。這些人的體格尤其強壯。關中、陜西人氣魄雄健、為正義而戰的勇武精神在全國最出名。所以,便獲得“陜西冷娃”的綽號。此“冷”的意思是冷靜、沉著、極少見,皆褒義,俗語叫“冷不防”(“冷門”、“出冷彩”)、“出奇招”、干別人不敢干的大事與實事,即所謂的“垤(干)冷活(事)、垤大活、垤實話”。最有名的例子是王鼎尸諫與張楊兵諫。鴉片戰爭中(1840-1842年),東閣大學士王鼎(陜西蒲城人)堅決主張抗英。聽到林則徐被貶新疆伊犁贖罪的消息后,當即上殿與道光皇帝激烈爭論,“力薦林公之賢”。《南京條約》簽訂前夕,道光決心投降、貶林。朝臣無人敢諫。王每日上朝都要冒死怒斥投降派頭子穆彰阿“妨賢(指林)誤國”。道光不聽。王毅然留下遺書:“條約不可輕許,惡例不可稱開;穆不可用,林不可棄。”閉目自縊,橫尸以諫,朝野震驚,國人敬仰。這種“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魯迅語)、“難酬蹈海亦英雄”(周恩來語)的剛烈氣概,在當時的中國絕無僅有。1936年12月12日,楊虎城(陜西蒲城人)與張學良將軍一起,“把天戳了個窟窿”(張學良語):扣留打內戰不抗日的蔣介石及其在西安的軍政大員,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兵諒)”,迫使蔣介石答應人民的抗日救國主張,促成了十年內戰向抗日戰爭的轉變。張楊成為中華民族的“千古功臣”,贏得國人無限敬仰與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高度贊賞。王鼎與楊虎城的奇智(出其不意)大勇(視死如歸)是關中、陜西人雄健氣魄、為正義而戰的勇武精神的集中體現。他們是“陜西冷娃”的杰出代表。就關中、陜西的普通百姓來說,他們雖沒有王楊這么驚天地、慟鬼神、名垂千古,但他們的雄健氣魄、為正義而戰的勇武精神與王楊是相同的。如:抗日戰爭中西安出版的《老百姓報》(李敷仁主編)特載《陜西冷娃》一首:“陜西冷娃,一千多萬(當時的陜西人口)。爭冷噌崛,膽大包天。一對拳頭,賽過老碗。日本小鬼,修得反邊”;中條山失守后,退到黃河邊的三十八軍(陜西軍隊)一擎旗手抱著日本兵跳入黃河,拼盡最后一絲勁,把旗桿插進鬼子的胸膛,黃水奔流,戰旗不倒。現在不少人把“冷娃”理解為“愣娃”是誤解。“愣”的意思是癡、呆、野蠻、魯莽等,貶義,即俗語“癡麻二愣”、“愣娃坯生子”、“愣頭愣腦”、“愣垤呢”(有暴食暴飲、蠻干、生整之義),是關中、陜西人勇武的負面。
“陜西冷娃”是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鍛造、熏陶出來的群體氣質與精神。陜西是漢王朝的發祥地(劉邦始封為漢王,都漢中),是漢民族最先形成的地方。漢到西晉,漢族文化是中華文明的代表;西晉末年到南北朝,鮮卑、匈奴、羯、氐、羌(簡稱“五胡”)等西北方少數民族大批進入關中。前秦等六個少數民族王朝在陜西建都,使陜西少數民族的數量超過漢族。陜西隋唐時的漢族是原漢族與少數民族融合而成的“新漢族”。他們的“胡氣”比其他地區都大。后世的陜西人是他們的后裔。所以,從遺傳學的角度看,“陜西冷娃”集中了原漢族與少數民族兩個方面的特點與優點,即:一方面,比之原漢族,氐羌“肥壯”,匈奴“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于氐羌”(《晉書*將統刊傳》)。羯人“多髯”(《晉書*載紀*冉閔》)。西北方少數民族毛發發達;一方面,原漢族自商鞅變法以來,崇尚公戰、獻身、大氣、剛勇。西安千年古都,西北重鎮,自周公制禮作樂以來,傳統文化積淀最深,英才輩出,足智多謀。這都是中國其他地區難以具備的。
戈壁荒漠不了情
如明
人和戈壁荒漠能有什么感情,作秀吧?
并非作秀。
一個離家出走的孩子,當精疲力竭時,才知:“走遍天下,家好!”;同樣,身處戈壁荒漠時,我曾詛咒它,詛咒它的暴虐、苦寂、荒涼和讓許多生命戛然而止的殘酷,于是,我想方設法的去逃離它,可真當離開后,日夜思念,魂繞夢牽的,卻是戈壁荒漠上空淡然的流云,千里戈壁上喜人的翠綠,堿灘上自我掩藏的土撥鼠,四季不斷施威的暴虐狂傲的烈風,以及一樁樁、一幕幕驚天地、泣鬼神,令人潸然淚下的故事。它們像電影鏡頭,歷久彌新,不斷出現在我的夢境中,出現在一切能觸景生情,生發回憶的片段中。離開戈壁荒漠已經整整40年,回頭品味,才知道,七年的戈壁荒漠生活,改變了我的性格,熔鑄了我的品質,我的生命因子中飽含著戈壁的生存密碼,濡染著荒漠的生命胎印。
那里被人稱作“世界風庫”。一年到頭刮著遮天蔽日的大風:那里極度干旱,常常經年不落一滴雨,即便下雨也從未濕過地皮;那里鹽堿深重,挖開戈壁荒漠的表層,地下幾米深竟然全是黑黃的鹽堿,那亙古的遺存是我們墾荒者難以逾越的壁壘;那里夏季酷熱,冬季苦寒,春季揚沙,秋季蕭瑟,生命的跡象只有那堅毅的紅柳、頑強的駱駝刺、機警詭異的土撥鼠以及我們這些“誓把荒原變糧倉”的開拓者。
開發沒有成功,不科學的決策讓我們把幾萬平方公里的河西大地斫成了禿子,以致風沙更加肆虐,鹽堿更加深重;墾荒者種不出糧食,只能自食惡果,成天餓肚子。大人餓、孩子餓、男人餓、女人餓,餓得發瘋!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卻孕育出了那么多刻骨銘心的故事!曾為愛殉情,九死一生的小芬姑娘,你還好嗎?幾天沒有吃東西,餓得幾乎昏厥的我,面前出現一位大姐,她塞給我一個窩窩頭。那位大姐,你如今又在何方?曾經追過我,卻被我屢屢傷害的那位叫小芹的姑娘,你能原諒我當初的無禮嗎?當我田間中暑不省人事時,背我去衛生隊搶救的那位大哥,你如今身體好嗎?還記得在那滴水貴如油的戈壁灘上,春灌時干渠決堤,為保水保田,三邊的兄弟們一個個縱身躍進冰河,用身體堵住決口,許多人被凍僵凍硬昏迷不醒,危急中三連的姐妹們將他們的衣服扒光,不顧女孩應有的羞澀,將他們一個個攬入懷中,用人性的光輝,用大愛和溫暖讓他們的身體和心靈復蘇,那是怎樣的感天動地啊!那些山東籍的大姐小妹,我祝你們這些好人一生平安:這里每次都能聽到原子彈試驗的爆炸聲,1967年夏天的氫彈試驗曾經地動山搖,我們當時躲避用的地窩子如今安在?……
當終于有一天我重新踏上這片魂繞夢牽的土地,迎著狂暴的烈風,迎著遮天蔽日的沙塵時,我的眼窩已溢滿淚水。當然不是風沙迷眼,我胸中的電閃雷鳴,比這自然界的風暴還要猛烈,我的心潮澎湃,我的激情噴發,除了眼淚,還能有什么?啊!這片鑄造我的土地,這片讓我從贏弱走向堅強的土地,就像一位虛弱不堪的奶娘,用她稀薄的奶水養育我的土地,我怎能忘記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