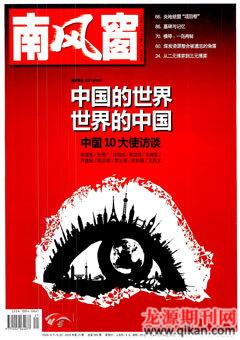奧巴馬:世界的“匹茲堡”?
錢克錦
匹茲堡的確是轉型成功了,尤其這次峰會期間更引起世界的首肯。但匹茲堡成功轉型背后還有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它在當地的影響力遠不如以前。奧巴馬要想成為世界的“匹茲堡”,的確要仔細考量他的這些“轉型”對美國傳統實力和利益的影響。
大國首腦有時候很忙,起碼從日程安排上是這樣。身兼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的美國總統貝拉克·奧巴馬當然更忙。9月22日~25日,他和中、英、法等大國的首腦一樣,走馬燈似地連續參加了在紐約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安理會核不擴散與核裁軍峰會,以及在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市召開的G20金融峰會。
9月是聯合國月,大國首腦到處“跑會”本也不稀奇,但因為奧巴馬上任8個月,基本還是個“新人”,關于他能否實現變革的理想,人們只能如盲人摸象般看他在各個領域的作為。而這次撞在一起的幾大峰會,讓人們得以集中觀察他的綜合表現,并從中尋找美國政府給世界未來帶來何種影響的蛛絲馬跡。
不可能出錯的立場
上任大半年來,奧巴馬的宏偉理想在國內已被現實糾纏得焦頭爛額。被視為其總統成敗象征的醫療改革,面臨的阻力越來越大。而在利益集團的壓力之下,白宮也出臺了不少有貿易保護主義色彩的政策。奧巴馬甚至被一些媒體貼上了“保護主義總統”的標簽。去年在人們心中激起的希望,如今已經縮水。
所幸墻里開花墻外香,總的來說奧巴馬的國際光環仍在。對奧巴馬來說,這次的系列峰會正是他刷新美國國際形象的良機。果然,他在聯合國氣候峰會上承認發達國家破壞環境的歷史責任,表示美國在環保方面負有帶頭責任,也應該盡力幫助發展中國家;在聯大發言中,他系統地提出了核不擴散和核裁軍、追求和平手段解決爭端、保護我們這個星球、平衡發展全球經濟這“四大基石”的外交構想;他主持了安理會核不擴散和核裁軍峰會,這也是第一次由美國總統主持安理會會議,展示了白宮新主人尊重聯合國多邊機制的姿態;而在G20峰會上,奧巴馬和其他領導人一起強調合作和溝通的重要性,并展望更加平等更加多元的未來世界經濟新秩序。
綜合4次峰會上的言辭,奧巴馬領導下的美國將會是個勇于承擔責任、重視環境保護、追求和平手段、注重國際溝通的美國,和前任布什時期那個一意孤行、不屑于同其他國家討論環保的美國不太一樣。雖然貿易保護主義的陰云仍沒有散去,但大致說來,這樣的美國還真可以讓世界比較滿意地接受。奧巴馬的立場幾乎沒有出錯。
奧巴馬能否成為“匹茲堡”
這一連串的峰會中,除了40年未踏足美國的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霸住聯大講臺,上演撕《聯合國憲章》這一鬧劇外,最吸引眼球的還數在匹茲堡舉行的據稱將從此取代G8峰會主要功能的G20峰會。盡管G20峰會明年還要在加拿大、韓國開兩次,后年起轉到法國后每年開一次,但無疑今年的匹茲堡峰會承前啟后——正值金融危機爆發一整年,各方該出臺的救市措施差不多都已經出臺,該評估這些措施的效果,甚至考慮某種“退出”策略了——因此這次金融峰會比此前的華盛頓、倫敦峰會更能顯出政策分水嶺來。
選擇匹茲堡作為主辦地,也的確更能緊扣主題。這個位于賓夕法尼亞州西部、市區人口只有30萬的河港城市,據說是美國老工業城市中率先完成轉型、浴火重生的例子。
筆者在匹茲堡待過大半年,這個城市在美國也算有點歷史,殖民地時期就是連接美國東西部的樞紐之一,南北內戰后的半個世紀內,更發展成為美國第八大城市,是名副其實的鋼鐵和制造業重鎮——鼎盛時期(20世紀初),其鋼產量占全美1/3到一半;二戰中為美國最終打贏戰爭出力不小。鋼鐵一度成為這個城市的標志,即使在今天也留下不少痕跡,比如它的有名的美式橄欖球球隊就叫“鋼人”;該市流行的啤酒有一品牌就是“鐵城”;因為地處三河交匯之處,上百座跨越三條河流的金黃色鋼鐵大橋也是匹茲堡的一道著名風景線。
當然,由于鋼鐵與煤炭工業,匹茲堡也是美國歷史上外來工人和資本家發生激烈斗爭的主要地點之一,還是污染嚴重的“地獄”。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鋼鐵工業面臨來自日本等地的競爭,逐漸衰落。制造業重鎮如匹茲堡、底特律和克利夫蘭等漸漸成為“生銹地帶”。
但匹茲堡卻借此機會,連續實行兩個“復興計劃”,十幾年內居然脫胎換骨。當外界對匹茲堡的印象還停留在“生銹”、“骯臟”、“沒落鋼鐵城市”上時,它已經發展為依靠醫療、高等教育、科技、體育、金融等新型經濟的“綠色”城市,被譽為“最適合居住”的地方。目前匹茲堡最大的兩個雇主是匹茲堡大學醫療中心(UPMC)(員工4.8萬)和匹茲堡大學(雇員1.07萬);位于此地的卡內基·梅隆大學的計算機科學居美國前三;本次峰會會址勞倫斯會議中心是世界上最大的“綠色”建筑。這些都可以看作是匹茲堡轉型成功的證據。幾年前,筆者一個在匹茲堡的朋友甚至說“有野心的人去紐約、華盛頓和洛杉磯,聰明的人來匹茲堡”。言下之意,此地生活的確不錯。而且,制造業等產業的大企業并未從匹茲堡完全消失,2009年《福布斯》公布的500大企業中,有8家總部位于匹茲堡。
有鑒于此,匹茲堡成為成功轉型的典型,在當今世界陷入經濟危機、人們痛感整個世界都需要脫胎換骨之際,世界都希望能成為“匹茲堡”;而被布什“弄糟了”的美國,國內國際都需要改變,人們自然也期望奧巴馬成為世界的“匹茲堡”——希望他把美國轉化得更環保、更合理、更有親和力。前景并不看好,棘手問題多
希望歸希望,奧巴馬要成為世界的“匹茲堡”頗有難度。誰都知道,美好計劃和設想是容易的;各國首腦聚在一起,簽署一些宣言、為世界指明未來方向也不是很難。問題就在于如何實現。比如奧巴馬宣布氣候變化為美國政府優先事項,但其10年內減排25%~40%的設想至今未能在參議院通過,甚至“年內絕不可能通過”,奧巴馬只能在峰會上空談減排。再如,奧巴馬曾表示要安排美國高級官員與伊朗就核問題開展直接談判,但最近伊朗被揭露在圣城庫姆附近秘密建造第二座鈾濃縮廠,引發外界極大憂慮,美伊談判的事也就只好靠邊站了。同樣,關于美俄“削核”談判下一步怎么走,奧巴馬在峰會前搬走了在東歐建反導基地這塊大石頭,但俄羅斯的回應卻顯得曖昧不清。最后,在美國動議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IMF的投票權由43%增加到48%以上,但發言權縮小的歐盟國家是否會轉而要求取消美國的一票否決權呢?所有這些問題,談到細節就是具體利益之爭,難度自然加大。而一旦這些問題不能深入,美國轉型、引導世界轉型就非常難了。
當然,奧巴馬掀起真正變革的最大阻力還是來自國內。拿減排問題來說,奧巴馬是
第一個堅決要求國會通過削減碳排放法案的美國總統,但是除非在未來兩個月國會出現奇跡,否則幾乎可以肯定,奧巴馬將會在哥本哈根大會上讓指望他帶來綠色革命的人失望。具體而言,對于民主黨自由派人士將在參議院提交“限量及交易”(cap-and-trade)法案,共和黨堅決反對,認為這會減少就業;民主黨內很多人也反對,例如來自弗吉尼亞、內布拉斯加和密歇根州的民主黨中間派議員,受到他們家鄉煤炭工業和農業集團的游說,反對這個法案,而來自中西部的一些民主黨參議員則聲稱,如果想讓他們支持法案,就必須加上一條,對有些國家的商品征收“綠色關稅”。奧巴馬正在試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醫保改革方面有所作為,此時哪有資本在減排問題上固執己見?
再說G20匹茲堡峰會上一直強調的金融監管問題。有分析指出,實際上,奧巴馬政府已經錯過了制定相關政策的最佳時期。換言之,金融巨頭們有求于政府時,政府沒有及時出臺監管法案。而參議院已經放出風來,說現在重要的是“做最正確的事情”,而不是圖“快”。畢竟,如果要實現匹茲堡峰會的目標,就意味著要對二戰以來的金融體系進行徹底修改。況且,美國對自由市場的信念遠強于世界其它地區,反對政府過度干預的聲音也比其它各地要大。奧巴馬要想和其他國家領導人一起修理金融體制,談何容易?
奧巴馬想給世界帶來普遍和平的愿望,實現起來也不容易。他自己承認,他首先是美國人的總統,實現美國人的利益是他最大的任務。但現在,他在核武器上的態度、同俄羅斯之間的協調、對伊朗的“軟弱”(右派媒體認為,奧巴馬對伊朗一直強調“外交大門敞開”、“伊朗有權和平利用核能”,態度很軟弱,遠不及薩科奇和布朗那種“伊朗別想獲得核武器”、“時間一到就面臨制裁”的表態來得痛快)、對朝鮮問題的束手無策,讓國內越來越多的人質疑他是否懂得美國的利益。奧巴馬在聯大發言時,稱“那些曾經指責美國實行單邊主義的人,現在不要袖手旁觀,指望美國一人可以拯救世界”,想來也是提醒其他有實力的國家,大家都要負起自己的責任,互相妥協讓步,共同解決棘手問題比如阿富汗)。不過,鑒于每個國家都要將本國利益置于共同利益之上,奧巴馬這個“和平之路”也必將坎坷不斷。
小結
提到國家利益,奧巴馬要想成為世界的“匹茲堡”,的確要仔細考量他的這些“轉型”對美國傳統實力和利益的影響。不錯,匹茲堡是轉型成功了,尤其這次峰會期間更引起世界的首肯。但匹茲堡成功轉型背后還有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它在當地的影響力遠不如以前。用一名在匹茲堡工作的記者的話說,“我們變得更干凈、更綠,電更小了”。1950年,匹茲堡人口68萬,2000年,這一數字是33萬。可以說,它的確適合生活,但如果說到實力和影響,畢竟還是紐約、華盛頓和洛杉磯這些適合“有野心的人”的城市。
所以,奧巴馬的一切變革思維,雖然目前還在國際上有號召力,也令人憧憬,但如果美國越來越多的人認為,這種變革影響到美國的相對實力,影響到美國利益,那奧巴馬的變革將會不得不屈服于輿論和選民的壓力。這種在國內輿論和國際期望之間的平衡保持得如何,保持多久,將決定奧巴馬的變革能夠持續多久,力度能有多大——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保持這個平衡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