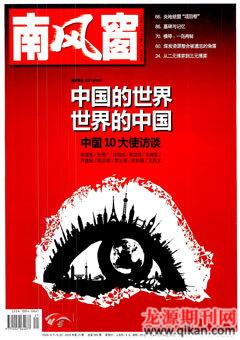話劇“舉國體制”怎樣謝幕
陳統奎
為什么“市場化的前景”一點也提高不起國有話劇院團長們的積極性?“事業轉企”改革,還需要包括政府下設基金會、企業捐贈免稅等改革配套措施之立法和實施,從而為這場改革注入強勁動力。
9月6日,上海話劇藝術中心一個小劇場里,今年新成立的國有控股北京演藝集團副總經理李龍吟“個人認為”:“可能經過一段時間,除非個別的,國有劇團可能不存在,國有控股有可能。”
誠如李龍吟所言,變革話劇院團“舉國體制”的力量蓄勢待發,箭在弦上。
話劇圈將這場變革稱為“院團改企改制”,官方用語是“文化體制改革”。在這樣一個何去何從的關鍵時刻,中國話劇圈的精英領軍人物們接連在北京、上海、沈陽召開了三場“中國話劇發展論壇”,他們最關心的問題是:未來話劇演出機構是什么樣子?怎樣讓話劇復興?
“舉國體制”到頭了
政治工具的角色,決定了話劇在新中國的命運。
上海戲劇學院湯逸佩教授這樣概述:新中國建立后,中央政府辦了一件從戲劇史角度來說可謂驚天動地的事,就是在全國范圍組建話劇演出團體,當時大致地級城市以上都有話劇團,數量驚人。然后,成立培養話劇演出專業人才的高等教育基地——中央戲劇學院和上海戲劇學院,此外還有大劇團辦的學館。60年過去了,除了上海、北京和遼寧以外,現在還有多少地方的話劇團能展開正常的演出呢?
江蘇省話劇院院長楊寧亦感嘆,自1980年代中期出現了話劇“低谷”,話劇圈有識之士就拿出渾身解數“拯救話劇于水火”,政府也不遺余力地激勵、扶持、引導話劇創作,舉辦各種大賽、展演、藝術節,設立了這個獎、那個獎,眼花繚亂,不計其數。然而“時至今日,除了京滬兩地,話劇依然‘危機,依然‘被冷落,依然‘沒有市場,這又是為什么?”

湯逸佩自有結論:“中央政府靠行政命令建立了一個全國性的大劇種,但是,它無法靠行政命令去建立足以維持劇種生命的觀眾群體。”一言以蔽之,根源在“舉國體制”。
事實上,這些年,政府和話劇圈基本上取得了共識,問題出在話劇演出團體的體制和機制上,其“事業單位”性質,扼殺了創作和經營活力。于是,“事業轉企業”的改革呼聲愈演愈烈。
但展望這場改革,前面是一片紅海還是一片藍海,全國各地條件不一樣,各地院團長們喜憂參半。在這種背景下,李龍吟告誡同行們“申請更多保護申請更多照顧的行業和部門死得最慘”,因此他鼓呼道:“話劇人在中國演藝市場重新洗牌的過程當中,重新強占話劇的市場份額,這就是機遇。”雖然李龍吟把話說到生死存亡的份上,但話劇院團由事業改企業,面臨的問題一籮筐,涉及觀念、利益、地位、成本……不僅需要改革魄力,更需要改革智慧。何況,目前關于改革方向和路線圖,各方并未形成共識。
對此,上海分論壇的東道主、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總經理楊紹林特別向與會者解讀7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在上海的四點講話——
一是改變黨委文工團的性質,成為文化市場主體。二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產權制度。三是構建法人治理結構,達到兩級法人、公司治理。四是做好資本經營、產品經營。
這些話在企業家們聽來就是ABC,但對話劇院團長們來說,是革命性的。從1980年代開始,他們就學習“面對市場、適應市場、占領市場”,甚至進行了“事業單位、企業管理”模式的探索,但招數用盡,卻見效甚微。因此,這場自上而下的改革,其關鍵詞就是“現代企業制度”,一個方向是營利性的企業,一個方向是非營利性的社會企業。核心是,領頭者都必須擁有企業家素質。
走向“社會企業”
依楊紹林的定位,盡管上海話劇藝術中心要轉為企業,但未來它一定是非營利性的,“不可能以追求利益為目的”。當然,現在市場不活躍的時候,需要國有院團們“下海”,去培育話劇市場,激活一潭死水。
這樣一個改革路線圖,以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為代表的國有話劇,將在未來變身為“社會企業”,而楊紹林們則蛻變為“社會企業家”,而不是“商人企業家”。盡管楊紹林沒有使用“社會企業”這個字眼,但他闡述了一個清晰的未來。
愿景歸愿景,現在話劇院團都還處在連飯都吃不飽的時候,因此“首先是要解決吃飯的問題”,為此楊紹林提出“多元化”發展的思路,其實就是多處籌資。請看楊紹林亮出的家底,2008年財政事業總收入為2978萬,其中政府補貼占37%,演出收入占29%,物業收入占23%,其他收入占11%。其中,“物業收入”這一塊,令人羨慕不已,這是全國其他話劇院團無法齒及的。
當年,陳毅率軍解放上海后,把很多市中心的花園洋房都給了文藝院團。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的前身上海話劇團被分到的是,民國時期上海市長吳國楨的官邸,安福路201號,當時這條路叫“巨潑賴斯路”。如今,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把花園洋房m租給別人用,加上部分出租90年代后期蓋的辦公樓,也就讓“物業收入”占到總收入的23%,加上政府補貼,擁有60%的“硬收入”。
按理說,事業單位的日子很安穩,哪來改革動力,不是這樣嗎?
事實是,得益于浦東開發后掀起的改革浪潮和改革干勁,早在1995年上海話劇團就變身為“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創立制作人制度進行內部激勵,成為話劇商業演出的開拓者,10多年來,不僅培養了人才,還培育了一個規模不斷壯大的上海年輕中產觀眾群,票房年平均收入增長率一直在20%以上。截至今年8月,演了收入已進賬2000萬,其中800萬元是全國巡演的收入。而1995年改革前,總收入只有139萬元。可以說,這場機制改革已經為上海話劇藝術中心迎來一個“小陽春”。
進入2009年,楊紹林再次主導改革,深化制作人制度改革。1995年設立的是同定制作人制度,兩個人,克服了以前劇團一人說了算的局面,但弊端是,一方面依然存在大鍋飯痕跡,另一方面在分配機制上制作人和普通演職員之間分配差距過大。早在2007年,楊紹林就決意以項目制作人取代固定制作人,但除他之外,另一位制作人還有一年就退休,他推遲了改革時間。
二者最大的區別在于,對制作人的考核起了變化,原先對同定制作人的考核主要是場次和新劇目,現在對項目制作人的考核主要是票房。如果連續兩個項目回收率都達不到60%,取消項目制作人資格。這樣“企業化運作”,有一天轉為企業,就能靠慣性運行,避免“休克療法”之痛。
另一個變化是,原先固定制作人一個人就可以決定上馬項目,現在增設藝委會對項目進行審查論證,所有員工都可以申請立項,公平競爭。項目管理是現代企業管理中的一大法寶,這是內容生產的機制保證,是“事業轉企”后,核心競爭力之所依。
事實上,楊紹林已經為“事業轉企”改革的平穩過渡,打下了基礎。
“政府也是有智慧的”
在上海分論壇上,記者發現,楊紹林還只是憧憬“社會企業”,但上海市靜安區常務副區長方世忠卻告訴大家,其實作為表演院團
轉型鋪路石的“社會企業”已經出現在上海地盤上。
為了打造現代戲劇谷,靜安區成立了一個公司叫“上海戲劇谷有限公司”。方世忠說,他不要這個公司去營利,它其實就是政府推進現代戲谷的專業服務機構,為各類市場主體做服務員,而不是做他們的競爭者,“為表演藝術機構、劇場經營者、票節機構、中介機構、藝術家做好平臺的服務,做好平臺環境的營造。”方世忠的思路確實新穎,就這么打造了一個“社會企業”。
靜安區打造現代戲劇谷有基礎,一是上海話劇藝術中心、上海歌劇院、上海戲劇學院等要素資源都在靜安區,二是上海劇場座位半壁江山在靜安,而且擁有10萬話劇消費熱情和能力的樓宇白領,被稱為“黃金谷底”。
在演講之前,方世忠特別問了一下楊紹林,一年交多少稅,答案是150萬元。“你對地方稅收產生不了作用的,150萬和150億差距太大了。實際上,政府并沒有想在現代戲劇谷這個平臺上賺錢。”方世忠說,現在最需要的是更多的藝術家和藝術產品,現代戲劇谷首先得打造一個現代戲劇的集聚區、一個劇場集群,當它達到一定的規模經濟的時候,就會產生價值。
以美國百老匯為例。“你投1美元產生的是5.4美元對區域的拉動,還不包括就業,所以百老匯的票房是9億,它實際拉動的是45億,帶來的是44萬的就業機會。”方世忠說,政府想要的是這些“附加價值”。
由彼及此,不難看出,搞現代戲劇谷對靜安區發展的戰略價值。
除了成立不以營利為目的的“上海戲劇谷有限公司”,靜安區還成立了上海現代戲劇谷專業引導中心,同時設立科創資金,面向科技創新和文化創意,對重要藝術家工作室、重要的核心劇目和戲劇推廣項目進行資助。“我們在資助的過程中,特別關注中國的民間劇社的發展,和中國戲劇大學生的創業。我覺得這是最具生命力的東西,這是我們現在一個很重要的政策。”另外,還有一項重要政策,稅收優惠。
在當過上海大劇院院長的方世忠眼中,靜安區所做的這一切,其實就是為文藝表演院團“事業轉企”鋪路。
營利與非營利
調任靜安區副區長之際,領導與方世忠談話,問他文化體制改革最需要突破的是什么?他答:其他都不重要,關鍵是我們的政府和領導對非營利表演藝術和營利的娛樂文化要有一個清晰的區別,我們現在就是把非營利和營利混在一起。這種觀念性束縛,正在阻礙著眼下這場改革。
楊紹林與方世忠所見相同。2007年,楊紹林在美國呆了一個月,專門研究這個問題。他發現,2006至2007年度,紐約非營利性表演藝術組織的營業收入與營利性表演藝術組織的營業收入基本持平。搞商業運作的劇院不過六七十家,而注冊的非營利性劇院劇團卻有400多家,包括最著名的百老匯賣折扣票的經營中心都是非營利機構。“正是紐約眾多數量的非營利性劇院和10余萬演藝工作者的參與,在把紐約締造成世界文化中心的同時,也支撐了其商業營利性劇院的繁榮。”
“同家實行‘軟實力戰略,文化產業的健康發展需要在營利性與非營利性之間找到均衡。”楊紹林說。
香港話劇剛改制便是一個典型案例。2001年,香港話劇團變身香港話劇團有限公司,并由香港特區政府稅務局長簽署文件,豁免交稅。根據其2007~2008年的收入來源分析,政府撥款占70.2%,票房收入占25%,外展及戲劇教育收入占2.1%,節目制作收入1.0%,其他收入占1.7%,政府埋單占絕大多數。顯然,改制是為了增添活力,按現代企業制度運作,非為減少政府投入。
更值得內地話劇院團改制借鑒的是,香港話劇團在改制后,設立了香港話劇團理事會作為最高領導機構,下屬藝術總監和行政總監,分管藝術創作和行政工作,理事會的11名成員均來自香港特區政府聘任的專業人員、社會名流和業內專家,每兩個月開一次全體理事會議,對香港話劇團有限公司的發展規劃和營運情況進行監督和指導。
不過,楊紹林曾被有關領導告知,在西方國家非營利性組織和非政府組織性質相同,其活動有背離政府管理之嫌。而美國10多家表演藝術非營利性組織的領導者給楊紹林的答案是:劇院的經營管理與政府沒有任何關系,但因為接受政府資助,政府就能安排代表參與表演藝術非營利性組織工作,并且對選擇劇院新的領導人擁有話語權。“有資本這只有形的手存在,何況我們還有堅持黨的領導,想必擔心是多余的。”楊紹林說。
專程從臺北趕來與會的李立亨,2005~2007年連續3年擔任臺北藝術節的藝術總監。李立亨介紹,現在臺灣只有一個劇團是完全南政府資助,叫國光劇團,臺灣政府曾經想過要由“中央”資助一個地方戲劇劇團,但批評和反對的聲浪鋪天蓋地而來,大部分劇團反對政府再完全資助一個劇團。1996年,政府下設一個基金會,所有劇團可以通過它來申請政府資助,“申請的過程是一個非常壯烈的過程”
這個制度剛開始執行的時候,罵聲一片,因為要申請資金就必須寫企劃書,大家就罵政府逼藝術家“寫作文”,但事實證明,好的企劃書會反映出一個劇團的流程工作狀態,這個過程反而提升了劇團的管理和運營能力,而評審團的專家級意見對劇團發展也起到了積極作用。現在臺灣劇團收入來源是1/3來自政府補助,1/3來自票房,1/3來自企業贊助。
環視世界各地,事實是,全世界舞臺表演藝術這一領域,實際生存狀況大部分不能單一依靠票房主營收入支撐起資金鏈良性營運,公共財政撥款補貼和各類基金會資助水平一般占其營運經費預算的40%至60%。
這就是為什么,“市場化的前景”一點也提高不起國有話劇院團長們的積極性,“事業轉企”改革,還需要包括政府下設基金會、企業捐贈免稅等改革配套措施之立法和實施,從而為這場改革注入強勁動力。
否則,“推動轉制,僅靠未來預期只有3至5年的優惠政策難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