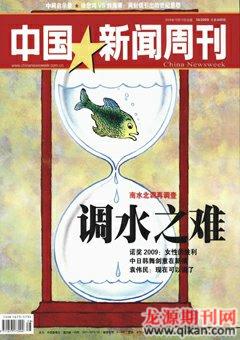經(jīng)濟學獎:向制度回歸的經(jīng)濟學
唐學鵬
奧斯特羅姆和威廉森的獲獎預示著,一種復雜的思想形態(tài)是如何被不同的團體各取所需、各安天命的

中文名“歐琳”的印第安納大學教授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在10月12日凌晨6點30分被一個電話驚醒,她以為這是一個尋常推銷員的電話,當瑞典人在電話那頭告訴她獲得2009年度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的時候,她感到非常吃驚和興奮,以至于不得不去廚房沖一杯咖啡來紓緩心情的巨大波動。
奧斯特羅姆的獲獎已經(jīng)不單單是理論的表彰,她改寫了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沒有女性獲獎者的歷史。在她之前,羅賓遜夫人曾經(jīng)是最接近諾獎的女性經(jīng)濟學家,但最終與諾獎失之交臂。
奧斯特羅姆和加州大學經(jīng)濟學教授奧利弗?威廉森分享了2009年度的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奧斯特羅姆獲獎的理由是,她揭示了“公共財產(chǎn)運作是如何通過自主(聯(lián)合)治理的方式獲得成功”;而威廉森獲獎的理由是,他揭示了“企業(yè)內(nèi)部是如何發(fā)展成不同的組織結(jié)構(gòu)來克服沖突”。他們同屬于經(jīng)濟學中的新制度經(jīng)濟學一派。
新制度經(jīng)濟學的又一勝利
但兩者勝利的深刻性,遠遠超過1991年制度經(jīng)濟學代表人物之一科斯的獲獎。如果說科斯以“交易費用”為新的坐標來革命性地重新定義市場和企業(yè)之間的關(guān)系,那么,奧斯特羅姆和威廉森則分別沿著“市場以外”和“企業(yè)以內(nèi)”的制度路線,重新延伸了傳統(tǒng)經(jīng)濟學的內(nèi)涵。奧斯特羅姆的著力點在市場以外的“組織可生長性”,即如何以自主治理方式解決公共物品效率難題上面,比如如何避免“公地悲劇”。威廉森則更深入發(fā)掘出企業(yè)內(nèi)部科層組織結(jié)構(gòu)變化的彈性和豐富性,豐富了“公司治理結(jié)構(gòu)”之說。如果分別用一個詞語來反映奧斯特羅姆和威廉森的學術(shù)風貌,則前者是“公共池塘里的自主治理”,后者是“縱向一體化”。
有趣的是,他們的勝利又在某種程度上是“含糊不清的派別”勝利。無論是西方世界的自由主義者(左派)還是保守主義者(右派)都可以將他們看作是本陣營的成功。
例如,對于奧斯特羅姆來說,她以研究哈丁的“公地悲劇問題”起家。傳統(tǒng)的觀點是,“公地悲劇”不可避免,人都是自私且短視的,總會存在“搭便車”的想法,所以公共財產(chǎn)的逐漸流失是必然的,個人理性帶來的是集體的窘境。一個無主的公共池塘,必定面臨著涸澤而漁的瘋狂、一片均可“啃青”的草地必定遭遇過度放牧的悲劇。于是,解決公有財產(chǎn)只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利維坦集權(quán)方式(例如國有化或者政府管制),一種是徹底的私有化。奧斯特羅姆發(fā)問:有沒有第三條道路呢?
奧斯特羅姆在讀大學的時候(1960年代),就已經(jīng)研究加州地下水(公共物品)的污染、水位下降和海水灌注問題,按照哈丁的“公地悲劇”、博弈論的“囚徒困境”和奧爾森的“集體行動邏輯很難達成”,加州的地下水系統(tǒng)應當是“崩潰”的。但是加州的社區(qū)民眾、組織、城市水供應商以及城市管理者在互動中不斷提供新的解決方案,產(chǎn)生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共識、自覺式守則和用水規(guī)制,靠的不是行政從上而下的強制力,靠的是分享、理解、合作、博弈和懲罰,靠的不是“單中心主義”而是“多中心秩序”。
作為一個酷愛田野調(diào)研、熱衷占有一手材料的“直面現(xiàn)象理論家”, 奧斯特羅姆繼續(xù)考察了阿爾卑斯山草地、日本公用山地、西班牙韋爾塔和菲律賓桑赫拉等案例,她發(fā)現(xiàn)“公地悲劇宿命”并非能統(tǒng)治一切,關(guān)鍵在于政府或者社會能夠容忍和鼓勵這些參與者能夠自發(fā)生長出不同的組織方式和談判方式,這才能保證公有財產(chǎn)能夠有效率地運作而不至于“坍縮”。奧斯特羅姆感嘆道,“既不需要迷信市場,更不需要迷信政府,因為還有個人生長為組織的過程,自由人的聯(lián)合和互動過程,它們更值得依賴”。

于是,對奧斯特羅姆的理解就有了兩個坐標。一種是“反霍布斯主義”的,她的學生喬治梅森大學Mercatus中心的Paul Dragos Aligica就認為,“她挑戰(zhàn)了那種自上而下的集權(quán)驅(qū)動方式”。Paul Dragos Aligica偏向于保守主義者,喬治梅森大學是右翼的大本營;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從“反私有化”角度來理解奧斯特羅姆,他說“那種將私有化和產(chǎn)權(quán)絕對清晰看作是解決公地悲劇的理論被奧斯特羅姆嚴肅地摧毀,奧斯特羅姆證明了某種社會規(guī)制機制可以讓‘公地運作有效”。從奧斯特羅姆本人的言論來看,她似乎樂于被歸納為右翼色彩的派別,但同時她也在“休克療法”“華盛頓共識”以及“援助非洲問題”等事態(tài)上面持一種異議態(tài)度。她認為,應當發(fā)揮制度和組織的多樣性和靈活性。比如“休克療法”就是一種單向的、強制式的從上而下推進方式,抹殺和阻止了民間和政府之間豐富的互動、妥協(xié)、權(quán)衡和必要的退卻。而“援助非洲”這一公共品的提供看上去已經(jīng)是一種“白人的道德負擔”,變成一個“扔錢行為”,忽略了援助是需要激活非洲的各種個人聯(lián)合、組織生長、因地制宜地發(fā)展解決方案和有效率和有策略促進社會健全和進步的行為。
她的想法啟發(fā)了納米比亞大象保護方式。納米比亞將很小比例的象變成旅游中的狩獵資源,然后用狩獵收入來加大對大象的保護以及對潛在狩獵行為的防范和補償。如果象進入居民領(lǐng)地,踐踏莊稼,那么象的受益權(quán)將同該居民分享。在沒有這一互動和分享的機制前,居民傾向于用獵槍將闖入領(lǐng)地的大象當場擊斃。
模糊不清的融合
奧斯特羅姆1933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亞,1954年獲得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學士學位,短暫工作后又回到該校讀書,并于1965年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有政治學背景的奧斯特羅姆有著一般經(jīng)濟學家難以逾及的視野。
奧斯特羅姆繼承了偉大的波蘭尼“社會秩序理論”的衣缽,突出一種參與者的互動過程中創(chuàng)立治理規(guī)則和治理形態(tài),強調(diào)一種“多中心秩序理論”——參與者在競爭中尊重對方、根據(jù)不同情勢發(fā)展不同的社會或經(jīng)濟合約,從而解決沖突問題。
例如,私人組織可以為公共部門生產(chǎn);城市可以將消防和安檢服務“私有化”(以色列);一個城市與一個私人企業(yè)簽約提供掃雪、街道維修或者交通燈保養(yǎng)服務(日本);政府向家庭簽發(fā)食品券和教育券,允許他們從任何授權(quán)的私人供給者那里購買(加拿大);甚至一個國家可以將自己的最高法院服務交給另外一個國家(新西蘭的最高法院在英國)??但如果政府是那種對社會組織的聯(lián)合和生長極端畏懼的,沒有科學發(fā)展觀,那么“公共池塘”將是一潭死水。
威廉森的組織理論,同樣可以為截然不同的陣營提供子彈和思想支撐。威廉森最核心的幾個詞語是“縱向一體化”和“機會主義(敲竹杠)”。我們以一個肉商故事為例,肉商原本只想專門賣肉,肉的保鮮服務則由跟凍柜商的長期合同來形成,但凍柜商發(fā)現(xiàn)肉商對其高度依賴后(脆弱的資產(chǎn)專用性),開始威脅(實施“機會主義”),肉商面臨巨大的外部風險,他一氣之下開始自己生產(chǎn)凍箱。隨后他想把肉賣到更遠的地方,卻又受火車運輸商的欺負,于是他又開始兼并火車業(yè)務,他在產(chǎn)業(yè)鏈上下游都進行了擴展。威廉森非常深刻地揭示出企業(yè)的科層結(jié)構(gòu)彈性變化是如何將外部風險不斷“內(nèi)部化”,而這個過程又提高了內(nèi)部官僚化和臃腫化的風險。
威廉森的理論必定和“反壟斷理論”有糾葛。盡管威廉森一直認為“縱向一體化”是商業(yè)組織正當而彈性地生長,而橫向一體化(例如同級兼并,肉商兼并肉商壟斷供應提高肉價)才有“壟斷地位的嫌疑”,在1973年他還為一家零部件實施專銷并訂高價的自行車產(chǎn)商辯護,認為他們通過這種專銷下游零部件的方式來保持商家產(chǎn)品的信譽和良好的質(zhì)量控制。看上去威廉森并不是一個反壟斷的愛好者。但諷刺的是,反壟斷學者例如羅伯特?博克(Robert Bork)以及鮑曼(Ward Bowman)都是從他那里吸取營養(yǎng),比如鮑曼開發(fā)的“傳導效應”——例如中國電網(wǎng)博弈,占據(jù)優(yōu)勢地位的電網(wǎng)公司開設發(fā)電廠,讓其自己的電優(yōu)先上網(wǎng),不僅獲取上下游利潤,同時也可以同非嫡系的電廠“壓價”,這就是所謂的利用原先優(yōu)勢進行縱向一體化后的“傳導效應”。這一思想已經(jīng)堂而皇之寫在了諸多國家的《反壟斷法》里面。而“傳導效應”的源頭則是威廉森的“機會主義”假說,即強勢的商人總是有動機,利用對手資產(chǎn)專用性的特征,產(chǎn)生“敲竹杠”行為,從而獲取利潤。“縱向一體化”既是一種規(guī)避機會主義的做法,同時也可以變成一種新的“敲竹杠”方法。
從這個意義上說,奧斯特羅姆和威廉森的獲獎不具備任何風向標和陣營的意義,它僅僅預示著一種復雜的思想形態(tài)是如何被不同的團體各取所需、各安天命的。左右互搏、陰陽之爭、對錯之察在這個時代已經(jīng)沒有太大意思,相反,自說自話、各說各理才是最主流的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