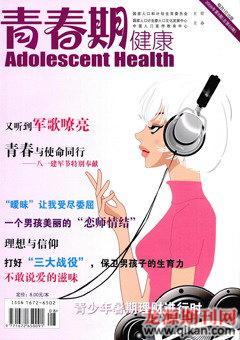不敢說愛的滋味
龍玉純
那時的我是個敢把地球也當足球踢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戰士詩人,整天滿腦子詩潮澎湃,滿眼洋溢著五彩詩意。早已被沖鋒槍磨出老繭的右手不時握緊那支父親送的英雄牌鋼筆,把隨時涌動的詩潮頓時化為稿紙上一行行蝌蚪般的文字,然后塞進信封交給翩然而去的綠衣使者,最后期盼著它們經過長途或短途的旅行之后在報紙雜志上變為一只只呱呱叫的美麗青蛙。有耕耘就必有收獲,我那有些俗氣的字隔三差五變成鉛字為我贏得了小有名氣的時候,我以優異的軍事成績和文化成績考上了北方一所有名的軍校,正式開始朝我的將軍夢進發。
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要想當將軍,先得上軍校。當我挺胸抬頭邁著神圣的步伐走進軍校大門時,我便在心底里默默發誓一定要爭當一名品學皆優的軍校學員。頭三個月,無論是軍事訓練還是文化學習,我始終一絲不茍、兢兢業業,給學院的首長和學友們留下了一個勤奮向上的美好印象,于是我被大家推選為學員干部。可惜好景不長,當我漸漸地適應了不同于野戰部隊的軍校生活以后,那洶涌的詩潮便又開始沖擊我的信念大堤。我不得不承認繆斯那不可抵擋的魅力,于是每當有靈感降臨,我便不管是上課還是下課,立即拿出紙和筆就大寫起來,有時上午的四節課就被一、兩首短詩給“報銷”了。這樣時間長了自然就會耽誤學業,我的成績開始下降。她——和我同桌的學員干部,看在眼里也急在心里,總是在課余主動給我補課并還委婉地勸導我,要我分清主次先把學習成績搞上去再寫詩。一個自己都控制不住自己的人是不會聽進別人勸導的,當我有一天又在高等數學課上寫詩時,她終于恨鐵不成鋼氣憤地搶過我的詩稿一下撕了,而且還狠狠地掐了我一把,用重低音罵了我一聲“沒出息”。
她是一位將軍的女兒,這是我后來才知道的。她爸爸早已是我心中的偶像,他發表在《解放軍報》上整版的理論文章曾是我們部隊政治學習的輔導教材,他發表在《解放軍文藝》、《詩刊》等文學雜志上的幾首長詩曾是我學習寫詩的藍本。她的學習成績在我們隊里總是名列前茅,自然不是憑老爺子的關系才走進這所軍校的。她也是學員干部,辦事說話給我的印象是雷厲風行、果斷潑辣,充滿了陽剛之氣,與那張微胖而且透著甜味的小姑娘似的漂亮圓臉很不相稱。
如果真有兩門功課不及格而被軍校淘汰,那戰友們肯定會毫不猶豫地叫我“窩囊廢”,再說我也無臉回見江東父老。高等數學課上她那一撕二掐三罵,頓時使我這快要走火入魔的詩人一下子從云中霧里跌落到硬地上完全清醒過來。我遺憾地收起了我的詩集和那還在騷動的詩心,從此每天上課心無旁騖認真聽講,課后能者為師請她補課。她對我的變化非常高興,除了熱心地在功課上幫助我之外,還不時和我談論當今的國際軍事形勢、高科技軍事技術以及她的人生追求。她的知識面很廣,特別是在軍事方面,讓我這個過去只熱衷于文學的人大開眼界。隨著時間的流逝,她和我的關系越來越好,我甚至還覺得安排她和我同桌是上帝老人家的旨意。我的成績也越來越好,第二學年期終考試我以優秀的成績終于第一次走上了學院的光榮榜。出榜的那天我和她剛好在一起打羽毛球,當她用球拍高興而且有些驚訝地指著排在她前面的我的名字時,我激動得用球拍愛撫般地連續輕輕拍了她好幾下,然后是睜圓眼睛微笑著盯了她足足一分鐘,她此時那稍稍泛紅的臉兒極其生動,竟看得我有些如醉如癡。
我得到學院表彰的那天,也就是有關我和她正在談戀愛的謠言四起的一天。大家都知道,軍校里學員是禁止談戀愛的,特別是男學員與女學員之間,發現一對就開除兩個,毫無情面可言。學員隊領導和系領導立即找我談話,問我是否有這么回事,我斬釘截鐵地回答他們沒有,他們也說其實沒發現什么苗頭,只是外面有謠言。當然,就算我在和她談戀愛此時我也不會傻乎乎地實話實說,因為只要一個“是”字,我那從小就開始醞釀的將軍夢瞬間就會徹底完蛋。領導們自然也問了她,她當然也會說此事純屬虛構。也許是為了平息謠言,系領導和院領導一致決定,讓我和另外幾位成績優秀的學員一道到下屬分院去當學員干部,我沒有理由不同意。在和她告別時她一臉的微笑,只是眼眶里波光粼粼。看她那樣子,我連忙在心里默念:千萬別哭,千萬別哭!你可千萬不能哭呀。
我義無反顧地打起背包來到了一千多里外的分院。在這期間,我埋頭讀書,積極工作,團結戰友,尊重領導,很快又找到了成功的感覺。我自始至終沒有給她寫過一封信,也從未給她打過電話,我知道讓我來分院是領導們“以觀后效”的一招,我和她的舉動躲不過他們的視線,我不能拿自己和她的前途開玩笑。當然,人是感情動物,我無法讓自己不去想她。思念是一種幸福著的痛苦,蓄積多了便自然地溢出變成了我筆下一首首精彩的情詩。我不能直接寄給她,便寄給了她愛看的報刊雜志,每發表一首詩我便覺得和她進行了一次幸福的對話。我用的筆名是她贈我的,外人只有那幾個編輯知道,不存在泄密問題。
這次重新拿起寫詩的筆并沒有像上次一樣影響我的學習,此時的我已經走過狂熱階段變得非常理智了。我的成績一直不錯,被分院的學友們戲稱為光榮榜上的常駐大使。我敢肯定寫給她的詩她都讀了,因為在發表第四首以后我莫名其妙地收到了一個從北京寄來的郵包,一個字跡陌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東西的郵包。那時我在北京沒有一個熟人,更談不上有人會給我寄東西了。打開一看,是一件很漂亮的羊絨衫,其中還夾了一張生日賀卡,卡片上寫道:“首先祝你生日快樂
這件羊絨衫是她委托我寄給你的禮物,她還說也是你的稿費補助。小伙子,你真幸福!一個你不認識的人。9月20日于北京。”多么讓人難忘的一個特殊補助!我情不自禁地又想起了我們在一起的日子……那天晚上我是穿著這件羊絨衫睡覺的。
四年的時光仿佛一晃而過,畢業的日子終于來到了。分院領導征求我對分配去向的意見,我回答說其實當兵在哪里都一樣,只是我不太適應北方的生活,還請首長們考慮一下把我分到南方部隊去。他們又說分院要派幾個代表到學院去參加畢業典禮,問我是否愿意去,我告訴他們既然我來到了這里,我就沒有想過再回去,還是另派別的同志去吧。說句心里話,我真想去看看她,看看她和兩年前有什么變化,是胖了還是瘦了?有人說她越來越漂亮,這是真的嗎?她被學院評為優秀學員,我真想親眼目睹她戴上大紅花后的風采。
分配結果很快就出來了,學院并沒有因為我也是優秀學員而給予特殊照顧,我被分配至駐南方一個小山城的部隊。就在要告別分院的那天上午九點,我正在宿舍忙著整理行李,突然聽到樓下一陣久別而又熟悉的腳步聲。她來了?我問自己,出門一看,沒錯,她提著個包正準備上樓。我急忙跑步下樓,剛接過她的包,背上便挨了不輕不重的一巴掌“為什么這次不去看我?真是個絕情的詩人!”
我乘下午16點10分的火車南下,她乘16點58分的火車去北京。她被分配至北京某部的機關工作。去送我和她的學友很多,在車快要開時我分別向他們敬禮握手告別,感謝他們幾年來對我的關心幫助。她替我提著包站在最后,當輪到我給她敬禮握手告別時,學友們一齊起哄:“嗨,就要開車了,你們還不抓緊時間唱一曲《吻別》?”我握著她的手開玩笑說:“都穿著軍裝那樣影響不好吧,還是先開張存折,下次好嗎?”“那得要問問利率高不高,”他們笑道。“小姐,你銀行的利率高嗎,”我接過她手中的包笑問道。她沒有回答,低著頭,哭了。這時開車的鈴聲響了,我立即掏出幾張面巾紙,一邊給她擦眼淚一邊輕聲說:“別哭了,好嗎?我愛你,我愛你!我的心里話早已寫在給你的詩篇里……”
火車漸漸地離開了站臺。我很遠還看到她右手在揮動著,左手在擦著眼淚。
(編輯趙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