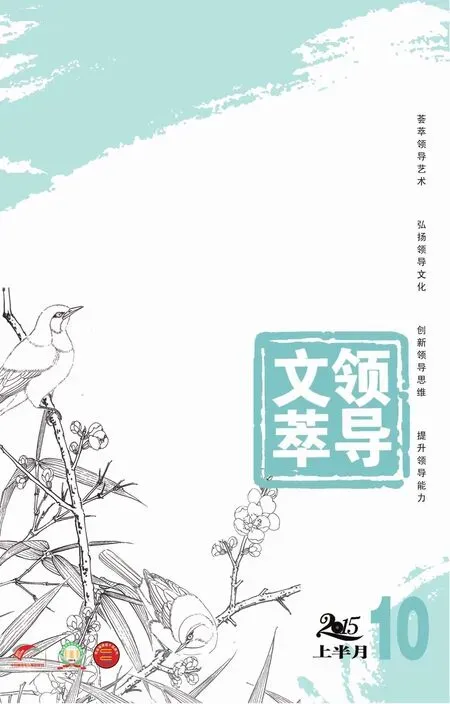問責制究竟問“什么”?
王曉杰
官員問責制的推行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亮點,特別是這些年來如此密集且大張旗鼓,令人耳目一新,也讓人充滿期待。但總體而言,我國的官員問責制還剛起步,還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需要進一步的探索和厘清。首先的一個問題就是,問責制究竟問“什么”?問責制本質上就是一種責任追究機制。我們今天所倡導的官員問責制與現代的民主政治內在要求緊密相連,更加強調對公共權力的控制與監督。民主政治是責任政治,責任政治的責任包括政治責任與法律責任兩個方面。因此,問責制所問的“責”也當然包括了政治責任和法律責任兩個方面。
政治責任與法律責任作為官員承擔責任的兩種主要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一般來講,問責制下官員的法律責任主要是政紀責任和刑事責任,官員違紀違法或犯罪所應承擔的個人責任,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黨紀政紀處分和刑事處罰。在法治社會,官員的法律責任應當明確、清晰,有著嚴格的構成要件和歸責原則,其行為與后果要一一對應,強調罪責相稱。相較而言,政治責任則開放得多。政治責任實質上體現著一種政治信任。政治責任主體主要是那些選任官員,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政務官,他們的去留升遷由選民投票決定,當他們失去選民信任或信任度受到質疑時,就必須自動去職,否則,可以經由彈劾而強制去職。而且,這種政治信任帶有連帶性,即政治責任的主體不僅要對自己的行為負政治責任,還可能因為其下屬的機構和人員的行為承擔政治責任。現代的民主政治更加強調“有權必有責”,凡是掌握或行使著公共權力的官員特別是領導官員都必須承擔相應的政治責任,而不再僅僅限于選任制的政務官。與法律責任不同,官員承擔政治責任的原因非常寬泛,多種多樣。“水門事件”是因為竊聽行為違反了美國法律,導致了尼克松總統下臺,他的一些助手和官員,共有25人涉嫌其中而受到司法部門的起訴。經濟上的違規,也是受罰的行為之一。如德國前央行行長韋爾特克因住了德累斯頓銀行免費提供的豪華酒店而受到強大的輿論壓力,只好“解甲歸田”。因疏忽或失職,導致重大公共安全事件而辭職下臺的也不少見。如2001年3月,葡萄牙一座年久失修的橋梁在連日的暴雨中突然倒塌,導致70人死亡,公眾指責政府失職,葡萄牙公共事務部長只好引咎辭職。也有因工作能力或業績不佳而導致下臺的。如因美國經濟不景氣致使加州政府陷入了上個世紀2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財政危機,部分教師甚至都拿不到工資,引發公眾的強烈不滿,導致了被認為在民主黨內最有前途的前加州州長戴維斯被罷免。此外,個人的生活問題也有可能成為官員下臺的原因。如美國眾議院前議長金里奇就因為婚外情而被迫辭去議長職位。
政治責任與法律責任雖然表現形式不盡相同,但都是追究官員責任的方式和手段,二者的關系是既交叉又相互獨立。官員因違法犯罪被問責而承擔法律責任意味著失去行使政治權力的資格,必須因此承擔政治責任而失去職位。但承擔政治責任并不一定必然承擔法律責任,如香港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因為車稅引發了信任危機,只得引咎辭職,但并沒有要求他承擔法律責任。另一方面,不必承擔法律責任并不意味著可以不承擔政治責任,政治責任意味著更高的道義要求。政治責任與法律責任相互獨立,是強調二者不可相互替代。因為政治責任與法律責任嚴厲程度不一樣,用政治責任代替法律責任,實質上減輕了官員承擔責任的程度,是對法治原則的破壞;用法律責任替代政治責任,會使政治責任主體付出過高的代價,承擔過重的責任。
如果官員被問責時既要承擔政治責任又要承擔法律責任時,政治責任的實現往往具有優先性,即首先追究其政治責任。這主要基于這樣的考慮:盡管不是所有公共權力的行使者都是政治責任主體,但政治責任的主體肯定是公共權力的行使者,相對于一般公民而言,他們更有可能更有機會逃避法律責任。如果不優先追究其政治責任,政治責任主體仍然掌握著公共權力,其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特別是刑事責任就可能因為權力的影響而得不到有效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