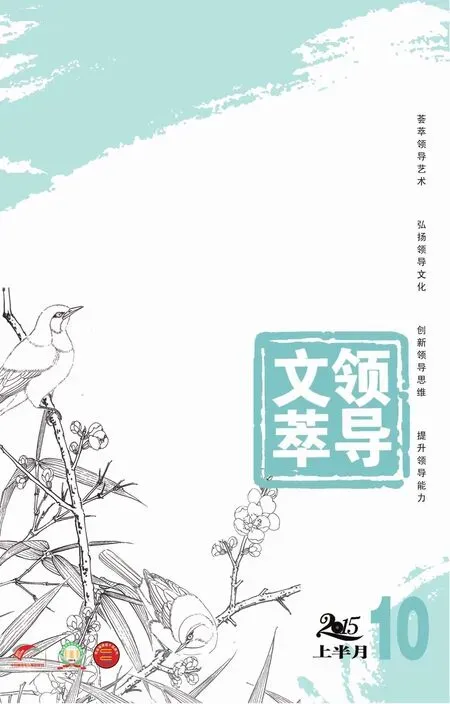普通人感念胡耀邦
徐慶全
多少人感謝胡耀邦
從1976年至1978年,胡耀邦抓住一個最要害的問題,拉開中國社會大轉(zhuǎn)折的序幕,這就是極具針對性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
這場大討論的意義有多深遠,已有定論。不過,普通百姓遠離政治,很難說能解其堂奧。要說有多少普通人感謝胡耀邦這個話題,還要從普通人的感受來說。
平反冤假錯案,是胡耀邦直接導演的一場撥亂反正的大戲。胡耀邦以“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的大無畏氣概,披荊斬棘,勇往直前。在這一大戲中,唱主角的蒙冤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得到平反,作為配角的普通人,其“第二次解放”的感受更深。
下面這組數(shù)字,很能說明問題:
1957年,全國有55萬右派,1958年“反右補課”、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全國又有二十多萬人“戴帽”,兩者相加,一共有七八十萬人。按照當年嚴格的政治審查標準,一個人“右派”或“右傾”,一家人就被劃入另類。以當年五口之家的約數(shù),這七八十萬人,實際上牽涉到三四百萬人。胡耀邦讓這些人從此“翻身得解放”,他能不在這三四百萬人心中“不朽”嗎?
包產(chǎn)到戶,也是中國改革開放歷史上的一場大戲,胡耀邦也是這場大戲的導演。包產(chǎn)到戶,現(xiàn)在,我們說是億萬農(nóng)民的偉大創(chuàng)舉,直接動因就是為了吃飽肚子。在“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叫囂言猶在耳,“一大二公”仍然為主流思想觀念的情況下,要順應農(nóng)民這一偉大創(chuàng)舉,并非那樣容易。
胡耀邦是如何做的?他主持中央工作后,明確提出自己的看法,“什么是農(nóng)業(yè),單打一抓糧食,不顧農(nóng)民家計是不對的。應當堅持的做法是,絕不放棄糧食生產(chǎn),積極發(fā)展多種經(jīng)營,農(nóng)林牧副漁,哪一項都不可忽略,那么多勞力,閑置起來是難以估量的損失”。
在總書記任上的胡耀邦,連續(xù)主持推出關于農(nóng)村問題的“五個一號文件”,激發(fā)億萬農(nóng)民長期被壓抑的積極性。1984年10月1日,天安門廣場慶祝建國35周年盛大游行中,農(nóng)民游行隊伍高抬“中央一號文件好”七個金色大字的巨幅標語牌,走過檢閱臺,廣場頓時歡呼起來。人們齊聲高喊:“中央一號文件好!”此后,在廣大農(nóng)村干部群眾心中,“一號文件”成為象征解放和發(fā)展農(nóng)村生產(chǎn)力的專用名詞,胡耀邦這個名字,也被幾億農(nóng)民掛在嘴邊上。
嶄新的領導人形象
1980年,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實際上,開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1981年,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共中央主席。對于普通人來說,只是偶爾在電視上看到他的鏡頭,對于他的工作作風,無從知曉。1982年,黨的十二大召開,作為總書記的胡耀邦,在大會上作報告,億萬國人才算真正了解到他的作風。在大約兩個半小時的報告中,胡耀邦最引人注目的表現(xiàn)是,他幾次站起來,輔之以大幅度的手勢,甚至夾雜有“這個……這個”的口頭語。
總書記的這種講話風格,盡管在一些人,尤其是上層中間,引起一些非議,對于普通人來說,覺得十分新鮮。當年,與我一起看電視的一位長輩說:“這個胡耀邦啊,沒有循規(guī)蹈矩。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干實事啊。”
胡耀邦逝世后,《科技日報》在紀念文章中有這樣一句話,讓我印象至深:“寧可聽漏洞百出的真話,也不愿聽滴水不漏的假話。”說出了老百姓的心聲。
2004年,在胡耀邦誕辰日,我和曾任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與胡耀邦有工作關系的杜導正同志,到胡耀邦家里表達思念之情。
那天,來人很多,當著胡耀邦夫人李昭及親屬的面,談到所謂胡耀邦講話隨便的問題。杜導正說了這樣一番話:“有人說耀邦講話隨便,而且,有些講話為情緒所致,有失分寸。我不這么看。過去幾十年來,我們習慣了晚年毛澤東式的領袖作風,說出話來,句句是真理。但是,我們應該不會忘記,領袖也是人,可以英明,但不會絕對英明,英明到先知先覺,英明到老天爺或上帝的程度,恐怕非人民之福。我覺得,一個領袖人物,十句話說對七八句就很了不起了。剩下的,給自己給大家留下回旋余地,即便自己錯了,還可以斟酌、改正。講話隨便一些,不要總給人拿腔拿調(diào)、高深莫測的感覺。晚年的我寧愿同坦誠相待、平易近人的領導人物親近。”
胡耀邦何以能樹立起這個嶄新領導人的形象?緣于他不管是位高位低,都把自己當做一個普通人。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胡耀邦當選為黨中央主席之后,發(fā)表了一篇講話,其中有一段話,講到自己,他說:“我個人職務的提升,并不意味著能力水平就一下子提高多少,我知道,今天的胡耀邦還是昨天的胡耀邦。”他對自己這么認識,可見政治上的冷靜和清醒。
在場有幾位老同志,高興地說:“就憑這個話,看來這個人我們選對了。”
的確,在我所能讀到黨內(nèi)高層對胡耀邦的回憶中,大多數(shù)人提到胡耀邦作風民主這一條。比如,田紀云這樣說道:“凡是他主持的會議,大家敢說不同意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即使跟他爭得面紅耳赤。我很清楚地記得,1985年6月,勞動人事部副部長嚴忠勤,在書記處匯報工資改革方案時,與耀邦意見不一致,跟耀邦爭論起來,很激烈。事后,耀邦同志對我說:‘嚴忠勤這人不錯,敢于直言。他還多次對我說:‘別看我當了總書記,我還是我,我還是原來的胡耀邦,我的水平還是原來的水平。”
《左傳》提出品評歷史人物的“三不朽”說,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這是史家的評判標準,普通人總結(jié)不到這樣的高度,只是有這樣一個樸素的標準:一個領導人,你惠及了大多數(shù)人,你不假、讓人親近,在人們心中,你就“不朽”,就真正地“活在人民心中”。
這也是如我等普通人,在胡耀邦逝世20年后,還念念不忘他的原因。
(摘自《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