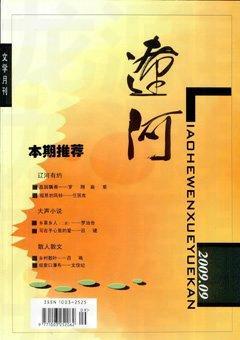搖晃的風(fēng)鈴
任國良
那個年輕男人從理發(fā)店前走過去,穿著黑色夾克衫,里邊穿著灰色帶暗格的襯衣,臉上棱角分明,面色紅潤。不到五分鐘,他又折了回來,站在那里看那個牌子。牌子是用鐵焊的,白漆做底,紅色的字:王師傅理發(fā)店。時間久了,紅色變得發(fā)白,漆有些脫落,不仔細(xì)看根本看不出字來。在林立的色彩鮮艷的各種招牌里,顯得很不合群。這是一條在高樓之間的小街,街兩邊有幾十家美容美發(fā)店、小旅店、小吃部。每家店鋪前都有一個拉客的小姑娘。王師傅理發(fā)店前面只有一塊牌子。年輕男人甩開幾個小姑娘的拉扯,猶豫著走了進來。
王師傅正在給一位上了年紀(jì)的老頭兒理發(fā)。王師傅個子不高,頭發(fā)梳得很整齊,穿著也是很樸素。王師傅注意年輕人好久了。他看出來這個小伙子不是來找小姐的,就有幾分好感。他破例地說了一句話:“先坐一會兒。”年輕人點點頭,坐在沙發(fā)上,點著一支煙。屋不大,前后兩進,多是理發(fā)用具,三面墻都有鏡子。在窗戶那里掛了一串紫色的風(fēng)鈴。開門、關(guān)門、王師傅用電吹風(fēng),風(fēng)鈴都會搖晃并發(fā)出悅耳的聲音。王師傅的電動推子不慌不忙地在老者的頭上左一下右一下地推著。有時可能只剪去幾根頭發(fā),推子在一個地方走好幾次,但絕不一下子剪得過深。鬢角、脖根都仔細(xì)地做出個形狀來。老者已經(jīng)瞇上了眼睛,發(fā)出均勻的呼吸。但王師傅卻沒有停下,那推子的作用此時更像是一種音樂或是一種撫摸。屋里沒有其它聲音。午后的陽光從高樓的縫隙中射過來。整個屋子明一塊,暗一塊。一個人睡著,一個人忙著,一個人手中的煙灰已有一寸長。
“咯咯——”一陣笑聲從后邊房間傳來。那是女人的聲音,小巧、細(xì)碎,有幾分嬌氣。老者猛然醒來,坐直了身子。王師傅說:“刮刮臉吧。”老者笑了:“小王,你的手藝是越來越好了。我都做夢了。”王師傅笑了一下:“不好意思,給您驚醒了。”刮臉,洗頭,再仔細(xì)檢查一下。半個小時過去了。老者站在鏡子前邊,滿意地說:“你小子一動手,我就年輕了二十歲,走了啊。”
年輕人坐在椅子上。王師傅開始動手理發(fā)。誰也沒吱聲。但是推子仿佛是最好的語言,剛開始時,兩個人的陌生感體現(xiàn)在相互配合上,有些不協(xié)調(diào)。三分鐘后,兩個人仿佛已經(jīng)是多年的好朋友。推子成了兩個人的紐帶。年輕人僵硬的身子變得柔軟,配合著做著輕微的姿態(tài)的調(diào)整。王師傅順手了,推子仿佛是在空中飛的自由的機器,沒有一點兒障礙。年輕人也閉上了眼睛,仿佛從肩上卸下了重重的擔(dān)子,長長地舒了一口氣。王師傅沒有說話。他已經(jīng)養(yǎng)成了這樣一個習(xí)慣。別人說什么,他委婉地附和,卻又清晰地表達著他的觀點。別人不說,要么是個寡言的人,要么心情不好,那他也不愿意給客人增加壓力。理發(fā)是一個手藝活,但在王師傅的感覺里,理發(fā)就是一門藝術(shù)。
洗頭的時候,王師傅的膝蓋不小心碰到了年輕人的腰,一個硬梆梆的東西讓王師傅一驚,那是一只手槍。年輕人也感覺到了,嘴角咧了一下,說:“我是警察,我叫于文強。”王師傅知道這個人。在小城里,于文強不亞于市長的知名度。他大學(xué)畢業(yè),功夫好,只身破了幾件大案,三十出頭,成了副局長。王師傅對職務(wù)不感興趣。他只對頭發(fā)感興趣。洗完了,又重剪,按摩。收費五元。于文強覺得在這里理發(fā)真是一種享受。但是他又覺得不公平,師傅手藝這么好,顧客卻并不多。
于文強剛走,又來了一位客人。王師傅熄滅剛點燃的一支煙,又開始了忙碌。
風(fēng)鈴是玻璃做的。王師傅偶然在朋友家看到,就喜歡上這種裝飾品。他自嘲地想,老了,老了,還有這樣的念頭,好笑。但經(jīng)不住風(fēng)鈴的誘惑。他到禮品店買了這個紫色的風(fēng)鈴。在盒子里,風(fēng)鈴是沒有血肉的,但是懸掛起來,一有風(fēng),風(fēng)鈴就活了。它的悅耳的碰撞聲仿佛人的腳步。但是風(fēng)鈴又是多么的脆弱,只一點點輕微的波動,它就會被奏響。它的情緒又是如此地不易平息,往往一陣風(fēng)過后,所有的事物都停了,只有它還在顫動、搖晃。王師傅有時覺得風(fēng)鈴就是一種裝飾品,一種玩具,有時又覺得風(fēng)鈴就是自己。
這一間店是王師傅的固定營業(yè)場所。但是王師傅還有自己的另外一個舞臺。
上午,電話響了。一接,是老顧客趙糧食。其實趙糧食具體叫什么,王師傅并不知道。只知道在糧食部門工作。趙糧食在電話里說:“王師傅啊,我要辦點兒事兒,你來給我理最后一次發(fā)吧。”王師傅明白了幾分:“你這些日子住院了嗎?”趙糧食明顯笑了:“咳,咳,你小子不夠意思,我都八十七了,沒病。什么都好說。我叫兒子去接你。”王師傅也覺得不好意思。但這也是規(guī)矩,如果有傳染病,他會帶口罩,戴手套。對一些老顧客,他都會選擇一個恰當(dāng)?shù)臅r機來說一下自己做事的規(guī)矩。現(xiàn)在趙糧食說自己,王師傅也覺得應(yīng)該。馬上收拾好家什,一把老式推子,一個剪刀,一個刮臉用的刀。一輛的士停在門前。王師傅進了里間說:“別惹禍,我去干活,一會兒回來。”出門上鎖,上車。趙糧食的家是一幢老樓,仍可看出當(dāng)年也是上數(shù)的。王師傅坐下。趙糧食的兒子進屋,和一個老太太扶著趙糧食出來。趙糧食坐在椅子上,看著王師傅說:“我要走了,火車票都買好了。小王,你可得好好給我剪,剪好了,我得領(lǐng)你一塊兒走。”王師傅笑了:“好哇,不行你先走一步,我這就到。”年輕人和老太太都轉(zhuǎn)過臉去,王師傅看見他們的淚水。趙糧食坐不住了,他的頭費力地挺著,但嘴上卻一點兒不老實:“小王啊,你給我理發(fā)三四十年了,你說,你光賣我的頭發(fā)能不能頂一頭肥豬的錢?”王師傅說:“能頂三四頭牛的錢。”趙糧食:“看樣子,我這樣的廢物也有用。兒子,你記著,再理發(fā)你就到王師傅那,他看到你就想到我,想到我他就難受。我見馬克思了,不能讓這小子好受。他掙了我一輩子錢,我得報復(fù)他。”王師傅說:“是啊,人家小姑娘小媳婦扯你拉你,你都不去。出門學(xué)習(xí)三個月,非得要回來上我那兒去理發(fā)。”趙糧食嘆口氣:“人吶,懷舊。今天給你二百,行吧?”王師傅說:“有點兒多了。”趙糧食說:“不多,我走了,你得趕禮,活著沒請到你,我走了的大爛菜你總得吃。”王師傅說:“好,好,我一定來。”那兩人已經(jīng)泣不成聲。
臨走,趙糧食握著王師傅的手,久久不放。
出了門,王師傅把用過的推子、剪刀、刀用白布裹了,一齊扔到垃圾箱里。花兩元錢泡了個澡。想想,又到市場上買了二斤大蝦。女人就愛吃這個。王師傅高興就一定會買。
于文強第二次來,氣色雖好,但是眉宇間有了一絲憂郁。他坐在沙發(fā)上吸煙,一支接一支。王師傅也沒言語,仍細(xì)細(xì)地為顧客理發(fā)。像他這種店,大部分顧客都是四十歲以上的回頭客。他做事就是這樣,干就干得最好。半個多小時后,客人滿意地走了。于文強坐到椅子上,掐滅了煙。王師傅邊給他圍巾子邊說:“煙少吸點兒,人受不了。”于文強動了動脖子,苦笑一下:“沒當(dāng)領(lǐng)導(dǎo)時我不吸煙,當(dāng)上領(lǐng)導(dǎo)了,不吸不行。也算緩解一下吧。”王師傅打開電源,推子響了起來,于文強突然說:“王師傅,這次理的時候,給我留一點棱角,短一點兒。”王師傅笑了:“好。”于文強問:“店里生意怎么樣?”王師傅說:“老百姓活得簡單,一家人吃得飽就行了。不像你們,也不容易。”于文強慢慢閉上了眼睛:“有時想想,還是老百姓好,面朝黃土背朝天,高興了就干,不高興就撂挑子。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王師傅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原則,現(xiàn)在看來,我最適合理發(fā)。”于文強閉著的眼睛動了一下:“我看王師傅可不簡單。”王師傅說:“你太高抬我了。我五十多歲了,站著干活也三十多年了,我干的這個活兒最枯燥,可我越來越覺得離不開這撥老朋友,這撥老朋友也離不開我。人吶,日久生情。”于文強輕聲說:“現(xiàn)在許多事,只有利益。”王師傅端詳著鏡子里的頭型,說:“年輕時我一表人才,能說會道,不知天高地厚,人家給我介紹對象,橫挑鼻子豎挑眼,后來有了現(xiàn)在的媳婦,又不好好珍惜,報應(yīng)啊。”
刮臉的時候,于文強說:“王師傅,這刀片在肉上走,感覺真舒服。”王師傅手上用力,嘴沒閑著:“刮臉的刀最鋒利,要不拿不下胡子。上歲數(shù)的人都愿意刮臉,人的皮膚很難接觸到刀,刀對人的皮膚的刺激,對神經(jīng)的刺激是最強的。”于文強仰起了脖子,王師傅捏住了他的上唇,刀剃胡子,剃鼻孔處的絨毛,又用剪子剪去鼻毛,之后又在臉上抹了一遍香粉。
于文強臨走,碰了下風(fēng)鈴。風(fēng)鈴叮叮當(dāng)當(dāng)?shù)仨懥似饋怼?/p>
于文強羨慕地說:“你的心境真好。”王師傅說:“像我這個歲數(shù),什么都無所謂了。”于文強回頭說:“王師傅,有什么事兒需要幫忙,你盡管吱聲。”王師傅笑了:“好。”
小街在火車站和客運站的對面,流動人口很多。所以各種牌子站在店鋪前,仿佛擺了一桌子的好菜,只要你肯花錢,總能找到對口的賣家。那種繁華讓人聯(lián)想到影視里的老街。輪回,時光的輪回,人事的輪回,總有許多類似的事情在歷史的某一天發(fā)生。
上午九點多鐘,來了一個四十多歲的農(nóng)民。農(nóng)民在進店看到王師傅之后,眼睛就直了。王師傅在小街上干了幾十年了,什么事兒都經(jīng)過,但是像這么看人的事兒,還是第一次發(fā)生。屋子里就剩下王師傅和那個農(nóng)民了。農(nóng)民坐上椅子,很小心地說:“我姓江,叫江有財。”王師傅有些好笑,你叫什么關(guān)我什么事兒。見到王師傅沒吱聲,江有財又說:“我想問你點兒事兒,問錯了你別見怪。”王師傅把白色的大巾子在那人領(lǐng)后疊好,塞進脖領(lǐng),有些不耐煩:“有什么事,你就說吧。”江有財?shù)芍R子里的王師傅,慢慢地說:“你繼父姓王,你親生父親姓于,是古城于相溝的人。”王師傅的臉一下子變了顏色,原來有些笑意的臉一下子長了。王師傅說:“別說了,你說的對。”江有財說:“你也別怪你爸。”王師傅的臉紅了:“我十歲,我,我媽,我一個弟弟,一個妹妹,全部跪在他面前,他都不能改變主意。要不是我繼父收留我們母子四口人,我們早死了。”江有財說:“你父親看中的那個姑娘是長得俊。”王師傅苦笑:“長得俊就得把老婆孩子撇了?他有沒有一點人性?”江有財盯著鏡子里的王師傅:“你和你同父異母的妹妹長得太像了,過去的事兒就過去了。你有多少年沒回于相溝了?”王師傅說:“我從離開就沒想回去。”江有財說:“你親爹歲數(shù)大了,經(jīng)常叨咕你們娘們孩兒。人吶,可能會做錯事兒,但做錯了,改了,也就行了。血管里的血都是老于家的。你看你這面相,和你親爹是一個模子里卡出來的。”王師傅眼里一熱,想罵人,說出來卻是:“我娘走了好幾年了,從離開家,她沒回去一趟。我那親爹身體怎么樣?”江有財故意問:“你想知道?”王師傅撣了一下巾子上的頭發(fā)說:“當(dāng)故事聽吧。”江有財長嘆一口氣:“也死了,就前些日子死的。他媽的,你說,我怎么不早幾個月來你這剪頭?”王師傅的手明顯一頓,又開始理發(fā)。
臨走,江有財在門前轉(zhuǎn)了好幾圈,四外看得都非常仔細(xì)。王師傅看出來,他在記道兒。
晚上,王師傅破例喝了點酒。女人看他喝酒,就格外小心,像一只貓,一點聲音都沒有。喝得有點多,他晃晃蕩蕩從屋里出來,買了些冥幣,找了個十字路口,跪在那里燒,一張一張卷,一張一張燒,嘴里卻沒閑著。嘟嘟囔囔的,一會兒爹,一會兒娘。
于文強有近一個月沒來理發(fā)了。像這種回頭客,什么時候該來,王師傅心里有數(shù),前后差個三天五天的,正常。若超過時間太久,王師傅就有了幾種判斷,在這個人還在這個城市的前提下,一個是嫌他年老不時尚,不來這里了;再一個就是出事了。像于文強這種身份,這個年紀(jì),不到他這里很正常,所以也沒往心里去。
王師傅這兒是個信息中心,所以市里的那點兒事兒,也有耳聞。其中一個新聞就是,于文強被雙規(guī)了,行賄受賄。所以于文強推開門,王師傅有些愣。看出來了,這一個多月,于文強沒理發(fā),沒刮臉,所以頭發(fā)很長,胡子也長起來了。王師傅急忙對在屋子里嘮嗑的幾個老友下了逐客令。于文強坐在椅子上。王師傅瞅了眼鏡子里的人,感覺到一種距離。于文強閉著眼睛,慢慢地說:“聽到不少傳聞吧?”王師傅冷冷地說:“我只負(fù)責(zé)理發(fā),別的事兒不管,也不聽。”于文強說:“真好,我什么時候能過上你這種生活?”王師傅笑了:“也不是每個百姓都活得那么輕松。”于文強睜開眼睛望著鏡子里的人說:“大叔,市面上的謠言,是有人要害我。請你相信我。”王師傅說:“我誰都相信。再說,我怎么看你,能有什么用呢?”于文強說:“誰都不相信我,我是清白的。你一定會知道結(jié)果的。”王師傅沒再搭言,只細(xì)心地理發(fā)去了。
于文強上午來理的發(fā),下午傍黑又來了。他坐到理發(fā)的椅子上。王師傅這個人有個特點,他總是能從剛理完的頭發(fā)上看出來不妥之處,哪怕是他花費兩個小時理出的頭發(fā),也能看出毛病來。所以于文強一坐下,王師傅就又忙上了。于文強躺在那里,長舒一口氣,輕快地說:“總算有結(jié)果了。我被撤消了領(lǐng)導(dǎo)職務(wù),現(xiàn)在是一名普通的警察了。王師傅,從今天開始,我就管你這片,有什么事兒 ,你盡管吱聲。”王師傅說:“我一個剪頭的,能有什么事?”于文強說:“我在離婚協(xié)議上簽字了。”王師傅心中一凜,接口說:“好聚好散,兩口子互相寬容一點。”于文強嘟囔著:“她為和我離婚,上紀(jì)檢委告我為老人做壽大操大辦,收禮,屬實。解除領(lǐng)導(dǎo)職務(wù),我一下想明白了,就簽了字。誰可憐我呀?我用誰可憐?”說著眼皮漸漸地不動了。
于文強醒來,已是掌燈時分。
王師傅理發(fā)店的斜對過是個公共廁所。原先污水橫流,現(xiàn)在改成收費廁所了,味道好了不少。王師傅從廁所出來,看到了江有財。江有財身邊有個中年女人。只是背影,江有財把女人領(lǐng)到理發(fā)店前邊就扭頭走了。中年女人進屋,一看沒人,往外走,和王師傅就碰對面了。
兩個人都愣住了。
兩個人的個頭、體型、面貌太像了,王師傅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側(cè)身進屋,說:“我不給女人美發(fā)。”中年女人似乎沒想到王師傅這么說,略顯滄桑的臉上漲起一片紅暈。她拎著個新編的筐,筐的上面用新毛巾蓋著。王師傅見過許多這樣的鄉(xiāng)下女人,拎著雞蛋鴨蛋、野菜野果走街串巷。有時他就想,一筐蛋賣個三十五十的,去掉車費吃飯的錢,能剩幾個錢?在家干什么不掙個三十五十的。他有些不屑。一次,一個賣野菜的女人中午到店里要水喝,王師傅給倒了杯熱水,女人從筐里拿出個饅頭啃起來。王師傅問:“你賣了錢了,去飯店吃一頓得了唄?”女人笑著說:“大哥,我一頓飯花三元五元,夠俺孩子在學(xué)校吃兩天,這一趟才賣四五十塊錢,去掉車費剩三十,我可下不起飯店。”王師傅這才有點明白,原來有些人過日子,到了今天還是以元、角、分來算計的。
中年女人把那筐放下,說:“家里也沒什么好東西,攢了一百個雞蛋,給你和嫂子吃。”王師傅火又來了:“你拿走,我不認(rèn)識你。”中年女人眼淚就下來了:“大哥,老人都不在了,是我媽的不對,我向你道歉。可我媽也背了一輩子的屎盆子。進土就進土了,我也不求你什么事,就是來看看。”女人說完扭頭走了。王師傅追出去,一直看著那個身影消失。他進屋,把那筐雞蛋放在沙發(fā)上,掀起毛巾,看著,看著,眼淚就下來了。
于文強來理發(fā),竟穿著警服。王師傅很意外。于文強坐到椅子上,摘下警帽,笑呵呵地說:“以前出門哪敢穿警服?現(xiàn)在好了,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小片警。”王師傅端量了一下鏡子里的并不長的頭發(fā),說:“咱們換個頭型?”于文強說:“身份變了,但人沒變,還要那個頭型,我就這個作風(fēng)。”王師傅隨聲說:“換個角度看生活,你說多有味道?咱們吧,有朋友、有親人、有咱們牽掛的人、有牽掛咱們的人。有情有義的平凡生活。”于文強說:“領(lǐng)導(dǎo)難啊,他哪能有這種心態(tài)?工作要成績,事業(yè)要高升。上哪找清福?看咱多好?”王師傅說:“什么時候當(dāng)新郎,我免費給你理發(fā)。”于文強笑了:“王叔,你怎么這么寒磣我。我離婚才幾個月,哪來的對象?”王師傅肯定地說:“現(xiàn)在五月份吧?我先放個屁擱這兒放著,不出一年你就能再婚。”于文強懷疑地說:“你上哪看去?”王師傅說:“你等著吧,別忘了請我吃喜糖。”于文強說:“行,你要說準(zhǔn)了,我認(rèn)你當(dāng)老干爹。”王師傅嘆口氣:“我哪有那個福分。”
窗戶開著,一陣微風(fēng),風(fēng)鈴晃動起來,那聲音像什么呢?有瓷器碰撞的味道,有鐵器與玻璃相擊的感覺,有水珠從高處落入靜潭的回味,甚至有一點短促的回聲。此起彼伏的,好像聲音被串成一串,忙不迭地被扔在地上。
“年輕的朋友們,我們來相會——”一陣細(xì)小緩慢的歌聲從里屋傳出來。聲音像少女一 樣嬌羞,似乎害怕驚動了什么,但又抑制不住激情。甜潤、輕快、活潑。
于文強有些奇怪地瞅著鏡子里的王師傅。王師傅似乎有些意外,所以把推子從頭發(fā)上拿起來,怔在那里,只片刻,他就感覺到鏡子里疑惑的眼神。他的臉一下子紅了,五十多歲的人,從事室內(nèi)的職業(yè),顯得很白,所以臉紅得異常明顯。王師傅頗不好意思地說:“我老婆,不好意思,打擾你休息了。”于文強笑著說:“師母的嗓子真好。”王師傅進了里屋,輕聲說了幾句什么。歌聲停下來。
于文強又閉上眼睛。
里屋傳來電視的聲音,很小,小到幾乎聽不到說什么。在于文強的感覺里,只有坐在離電視不足一尺的地方聽,或許能聽到。這是里屋最正常的聲音。于文強在這兒理發(fā)半年多了,每次來,里屋都是這種聲音。而這種聲音又告訴于文強,里屋有一個女人,從來不露面的女人。
于文強進屋的時候,王師傅看出了異常:于文強沒穿警服。于文強坐到椅子上,一躺,長舒一口氣,眼睛又閉上了。王師傅說:“你怎么長了這么多白頭發(fā)?”于文強苦笑道:“快全白了。”王師傅瞅了瞅鏡子里的那張憔悴的臉,于文強的眉頭始終是緊鎖的,仿佛是有意皺眉頭。王師傅知道,那是緊張造成的。
于文強睡著了。王師傅先是輕手輕腳,后來干脆住手了。他走出店門,站在小街上曬太陽。
鄰居是個女老板,約王師傅好多次。女老板說:“大哥,我這兒有干凈姑娘,你不解解渴?”王師傅笑了,搖頭。女老板說:“你買賣那么好,攢那么多錢干什么?兩腿一蹬,你什么都沒有。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王師傅說:“白費呀,我沒那個能力呀。”女老板不明所以,忙說:“有藥呀。”王師傅扭身就走。
現(xiàn)在,看著小巷里那些花枝招展的女孩子,王師傅習(xí)慣性地轉(zhuǎn)過身。
他看見于文強在小店里睡得很香。下午的陽光斜斜地照在他的臉上,那是一張多么有朝氣的臉啊。
于文強醒來,很不好意思。臨走,于文強面無表情地說:“我又高升了,我是這片兒警務(wù)局的局長。”王師傅說:“好好干吧。”于文強整理了一下衣服,走了出去。
王師傅看著那背影,有些陌生,又有些熟悉。
一天傍晚,要關(guān)門了。一個女人走進來。女人穿得很好,保養(yǎng)得也好,一看就是那種貴婦。王師傅邊掃地邊說:“對不起,我只給男士理發(fā)。你走錯地方了。”女人站在那里沒動。女人自言自語地說:“一點兒都沒變。你不認(rèn)識我了?”王師傅說:“不認(rèn)識。”女人嘆口氣:“王一摸,我是小蝴蝶。”王師傅說:“對不起,我不認(rèn)識你,我不是王一摸。”小蝴蝶笑了:“王一摸,二十多年前,叫響小城的王一摸,你死了我都認(rèn)得你的骨頭渣子。”王師傅毫無表情地說:“王一摸死了,二十多年前就死了。”小蝴蝶有些激動:“人可能死了,但是那一段歲月誰也不會忘記。嫂子現(xiàn)在還好嗎?”王師傅說:“王一摸死了,她就過上平穩(wěn)的生活了。”小蝴蝶環(huán)顧了一下小店,緩緩地說:“王一摸是專門給女士美發(fā)的。可惜他現(xiàn)在卻只給男人理發(fā)。”王師傅嘆口氣說:“一切都是報應(yīng)。”小蝴蝶盯著王師傅:“王一摸的手藝多好,小城有多少女人都希望能讓他給美發(fā),那是時尚、漂亮、個性的代名詞。不就是摸一下嗎。當(dāng)著大伙的面從后面抱著摸一下乳房,放松神經(jīng)又提高雙方的興奮性,多科學(xué)。如果是暗地里,那是不道德的,公開場合,那就是一種挑戰(zhàn),向世俗和道德挑戰(zhàn)。有什么不好?”王師傅坐下,點燃一支煙:“是啊,最后還是王一摸承擔(dān)一切。”小蝴蝶說:“這也不能怪王一摸,誰叫他媳婦疑神疑鬼。”王師傅吐了一口煙:“王一摸沒福分。寬容和諒解是有限度的。”小蝴蝶說:“誰都有過青春年少。可能我也有責(zé)任。剛和男朋友分手,就想發(fā)泄一下。我真的沒有什么惡意。”王師傅說:“王一摸也明白。可是他媳婦怎么想?自己的男人手里握著別的女人的乳房,在五六個人的笑聲里激情長吻,她會怎么想?”小蝴蝶低下了頭:“嫂子出事之后,我就離開了這個城市。我也無法原諒自己。我想對嫂子說聲對不起。”王師傅說:“王一摸死了,他媳婦也開始了新生活。平靜的日子多好。”
屋里傳來女人的哭聲。仿佛受了很大的委屈。而且聲音越來越大。卻又明顯地抑制。小蝴蝶懇求說:“讓我見見嫂子吧。”王師傅站起來:“如果你可憐王一摸的媳婦,就請你走吧。她受不了陌生女人的聲音,對她來說這是一種刺激。”小蝴蝶流下眼淚:“王一摸還是值得去愛的。他能和一個幾乎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的女人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他是一個好男人。”說完,小蝴蝶緩緩地走出了屋子。
王師傅沖到窗前,一個背影在夜色里模糊起來。
被撞到的風(fēng)鈴,叮叮當(dāng)當(dāng)?shù)仨懫饋怼?/p>
王師傅關(guān)上門,扭身進了里屋。
北方小城冬天有雪。
雪天活兒少。幾個老友坐在小店里神侃。一對男女捂得只露眼睛進了屋。男的脫下帽子,是于文強。于文強說:“理發(fā)。這是我的老干爹王師傅,這是我媳婦小雨。”屋里的人穿戴好都走了。小雨說:“王師傅,我家文強天天叨咕你。”王師傅笑了:“姑娘,你眼力不錯呀。”于文強坐下:“王師傅,我有點事兒。我想辭職,還想去干片兒警。”王師傅剛要開口,小雨從沙發(fā)上站起來:“這事兒你怎么沒跟我說?”于文強笑了:“現(xiàn)在說還晚嗎?”小雨有些火:“于文強,你聽好了,我可是二十幾歲的大姑娘,比你小十歲,你還是二婚,要不是看在你是分局局長的份兒上,我還不干呢。你今天辭職,咱倆今天就分手。”
于文強看了眼鏡子里的王師傅,王師傅也正在瞅他,有那么三秒鐘。然后,于文強閉上了眼睛,慢慢地說:“我這不是逗你玩嗎?”
一陣風(fēng)吹來,窗戶都跟著晃。風(fēng)鈴被震了一下,叮叮當(dāng)當(dāng)?shù)仨懫饋怼?/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