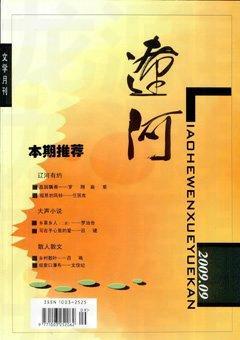鄉村散葉
召 喚
跑 暴 雨
好像是最后一個麥秸垛剛收頂,殘渣麥殼們也剛漚進水田,可腿腳上的泥巴還沒來得及洗凈,一抬頭,天上就丟起了雨點子,起先是有一陣,無一陣,田這邊有,田那邊無。入暑天的雨,隔牛背,也隔田埂。風一叫,雨就稠了大了,趕緊將擔麥殼的空籮筐頂在頭上,跑。雨,也跟著跑起來。等人到屋檐下,脫了衣服,擰一把透著汗腥的雨水,雨卻住了。
這是江漢平原的暴雨,但村人從來不叫暴雨,也不叫文縐縐的太陽雨,都叫“跑暴雨”。逗秋十八暴,暴暴都跑到。意思是說立秋前后的暴雨頻繁,就像小娃的屁股,一會屎,一會尿的,說來就來。
跑暴雨一下,這會兒,最要緊的是“搶暴”。夏天的稻場,除了碾場就是曬場,沒有一刻閑著的。麥子一天不進倉,心里就一天不踏實,但進倉前得曬干水份,以便保鮮。今天又是個好太陽,把麥子們攤曬在稻場上,中午再用木锨或竹耙翻個個,咬一粒麥子,咯嘣脆響,正好進倉哩,偏不湊巧,這當口老天冷不丁下起了暴雨。“搶暴啊——”男女老少風風火火齊上陣,腳忙手亂地就地將麥子堆起來,再用草苫子絲絲如扣地苫成錐圓形。自家的剛搶完,又不請自到地跑去幫鄰居“搶暴”,平日有什么口角隔閡的,一場跑暴雨就淋了個精光。等麥子一進倉,稻場下成河也不怕,不過,這時最要緊的是冒雨用繩子打圍欄,以防人走畜拱。跑暴雨后的稻場會無端地泛起一層泡泥的,一腳踩下去就會帶起一大坨泥。盡管圍欄打得再牢固,夜里仍有脫韁的牛呵豬的穿欄而過,將它們專用的八卦印章深深地蓋在稻場上。稻場是打谷(麥)場,但更是村人出出進進的臉面,糟蹋不得。
早晨開門,村街上就有了罵聲:“狗日的畜生!”不知是罵人呢還是畜生,待跑到自家豬屋或牛棚一瞄,空的,就禁了聲氣,說不準是自家的畜生所為,但有一點是肯定的,自家的畜生昨夜里一定也糟蹋了張三或李四的稻場。哪家的畜生都有脫鼻子的時候。總不能老跟不會說話的畜生慪氣吧。對,趕快趁雨過天晴擔來糯性十足的泥土,在千瘡百孔的稻場上打補丁。補丁是打好了,得整理平整才妥帖,就像熨斗熨平打皺的衣服一樣,可稻場沒熨斗,不慌,就用現成的石磙代替。稻場和“熨斗”間得鋪一塊“隔布”,那“隔布”一定得是隔年的稻草,因沉淀一年的稻草沒了新稻草的張揚、霸氣,柔韌而不硬硌,綿軟而不脆弱,鋪在雨后的稻場上,吸水卻不提地氣;那剛剛打下的新麥草飄飄然像個花花公子,一點也不“巴肉”。先將隔年的稻草們一溜溜鋪滿稻場,記住,碾稻場的稻草一定得鋪均勻,就像人蓋被子似的,頭是頭腳是腳地蓋嚴實,若藏頭露腳、凸凸凹凹的,石磙就會在上面打“嗝”,碾出的稻場就會成坑坑洼洼的麻子臉。
“呔——”牛鞭一揮,憨憨的石磙便聽話地一磙壓一磙地滾動起來。一向沉默寡言的石磙一旦派上用場就不安分了,總要“咯吱——咯吱——”地唱一路。自然,這是最好不過的伴奏,趕磙的老農嗓子就被挑逗癢了,你聽,《趕磙歌》就從石磙下不小心滾溜了出來:
跟著牛兒慢慢走呀,
跟著牛兒慢慢行,
舉起鞭子我舍不得打呀,
一步一步也不停。
慢慢走來慢慢轉啦,
石磙滾得多活泛,
稻場上就是要石磙轉啦,
一年到頭不愁飯……
卸下牛軛頭和石磙,老牛拉下一泡熱屎后,就靜靜地臥在老柳樹蔭下反芻。稻場還得在稻草被子下露宿一夜。翌晨,女人們用揚叉叉走稻草,讓嬌滴滴的露水太陽一淬,稻場上就成了一塊布滿草印的死泥,就像夏天睡草席的赤膊男人后背上印滿了席痕,平平展展卻又結結實實,不傷一點皮肉。這樣結實的稻場就是再下刀子也不怕哩!
不知從哪天起,稻場上開始有娃娃們比賽著釣一種叫不出名兒的地米蟲。娃們揪一根回頭青或掐一節蘭草,伸進米眼大的地洞里,釣,不一會,米粒大的地米蟲就會乖乖地被釣上來。玩膩了,娃們就會換一種方式,掏出小雞雞,對著稻場邊石磙兩端的石耳比尿柱射程的遠近和準頭。就在這當口,老天爺又開始“跑”起跑暴雨來。娃們就一邊撒尿,一邊望著白晃晃的太陽唱:
出太陽,下白雨,
一下下得沒的雨;
出太陽,下白雨,
一下下得沒的雨……
嗬,雨還真格在娃們清鼻涕的童謠里“跑”沒了。
這個夏天,不知“跑”了多少回跑暴雨,沒人記得了,就像遺忘稻場邊的那盤石磙一樣。
早稻說登場就要登場了,再去毒日下套那晾了多日的石磙時,發現石耳里竟搖曳著一叢麥芽芽,風一扇,滿鼻子竟是童子尿味哩!
這就是鄉村,鄉村的一場跑暴雨竟會淋出這么多有趣的故事來。
南 洋 風
我真不明白,這不知在江漢平原蟄伏了多久的風,一旦張牙舞爪地復出,總是改不了她的暴躁脾氣,火辣辣地爆炒著天,爆炒著地,催熟著大地上的農事和節令。這風,不像春風那樣纏綿多情,能梳織綿綿春雨,剪出行行燕陣;也不像秋風那樣刻薄無情,所到之處盡是黃葉凋謝、老氣橫秋的殘景;更不像冬風那樣冷酷跋扈,凜冽得生靈和萬物都龜縮著不敢露面。
一向土里巴嘰的農民卻很洋氣地送給她一個稱謂——南洋風。
我不知南洋風的祖籍究竟在哪里,也不知她是來自何處的移民,反正打她定居我的老家江漢平原后,總是在伏天里出沒,且都是晝出夜伏,極有規律。南洋風像一位助產師,只要在大地上走一遭,懷孕的萬事萬物便會立馬破了羊水,急著要分娩。你看,早稻熟了,煙葉黃了,棗兒紅了……所有的農事都腳跟腳手跟手地來了。
春姑曉得,自家的那二畝早稻遲插了幾天,七成熟,還得等幾天開鐮,但南洋風還在一個勁地刮,需灌深水降溫,才能保證收割時無癟殼。忙了水田忙旱田,棉花剛打過頂,再追施一次花肥,剩下的就只管田里成花海、落白云了。公爹的那一畝煙葉在南洋風里曬烤、晃動,像一匹匹翻動著的陽光,烘烤著平庸的日子。男人不明不白地“跑”了幾年,像一陣南洋風刮走得無影無蹤。關于男人的“跑”有許多版本,有說男人帶著窯場的那個比他小20歲的出納私奔了;有說男人卷走20萬的公款遠走高飛獨自享受去了。總之,男人幾年沒回家是事實,春姑一直守著這有名無分也無望的活寡也是事實。起先,春姑一直在心里后悔,大不該讓男人去承包村上的窯場。男人真是有不得錢,一有錢就花花腸子想七想八的。現在,春姑一切都釋然了,那一直糾結在她心里的悔恨、沮喪、巴望又失望……已離她遠去。她麻木了,麻木得像一株被南洋風撕扯的苦艾……
幾陣子南洋風,節令就到了割早稻、插晚稻的當口。稻田已曬得能走人了,那些半青半黃的谷子也“風”成了金黃色。江漢平原的土地就是肥,你隨手插只牛角,總能長成一頭牛犢,這樣的土質,常常是稻谷黃了稻秸還是青的,莊稼人就會擇一個南洋風口“放懶鋪”。“放懶鋪”是江漢平原一帶收割稻子的專用術語。露水一干,腳勤手快的姑姑嫂嫂們常會打伙串工,每人一壟,比賽著將割下的稻子們一溜溜均勻地鋪放在田里,睡懶覺。她們常常是一氣割完一壟才舍得伸腰,好像女人的腰是糯米做的,柔韌性極強,不曉得疼。男人呢,就不一樣了,要么割幾鋪就伸直身子,用鐮刀把捶幾下腰,要么就躺在田埂上抽煙。女人見了,就罵,看你懶得,快收!男人說,我才懶得收,讓它多曬幾個風火太陽再收。通常,割下的稻子要在南洋風里鋪曬幾個太陽。可是人懶風不懶,南洋風總是把陽光夸張地鍍在稻子上,直至吸干稻秸和谷子的水份,減輕了重量,男人們才肯“收懶鋪”。女人“放懶鋪”,男人“收懶鋪”,似乎成了他們各自的專利。由于曬后的稻子沒了水分縮小了堆頭,一雙七轉半的“草腰子”要捆好幾分田,人說“草腰子七轉半,挑死大力漢”,可這時像兩座山似的稻子擔在男人的肩上,卻輕飄得像兩個大棉包。這時,男人們總會得意地說,嘿,懶漢有懶福,幸虧這稻子“放懶鋪”哩。
春姑開始“收懶鋪”。田里有60大幾的公爹,和一雙放暑假的兒女幫忙“打抱”。一家老小硬是一口一口地將稻子們“銜”回了家。
收完這季稻子,春姑怕不得守了。
再守幾年,就不好嫁人了。
嗯,嫁人?說得怪輕巧,拖兒帶女的你要?
哎哎——這命苦得!
稻子剛進倉,可棉鈴蟲又肆虐起來。春姑背起噴霧器,又淹沒在了齊人深的棉田里。太陽好毒。南洋風好大。人們不敢有一絲懈怠,扯起勁地與天斗,與地斗,風風火火地到蟲口里奪“花”。大片大片的棉田都是打藥的農民,可在打藥的農民中只有春姑一個女人。日頭越毒,殺蟲的效果越好。春姑舍不得歇,打了一桶藥又一桶藥,她要搶在日頭蔫頭時打完這5畝田。南洋風一個勁地刮,藥水成霧狀直往棉葉上噴,不小心藥沫星子會搶機鉆進口里。肚子餓得咕咕叫,春姑也不肯把時間耽誤在路上,就隨手在棉田里摘了個隔生的苦瓜,拿到田溝里洗洗,一咬,脆嘣響,邊嚼,邊打藥。苦瓜不苦,苦瓜好甜哩!嚼一口,感到那南洋風、那飛濺的藥沫星子和苦巴巴的日子也是甜絲絲的。
春姑是準備回家時一頭栽進棉田的。
春姑就埋在棉田邊。要不是白幡在南洋風里飄呀飄的,誰也不會知道平展展的棉田里會有一個礙腳打眼的墳塋。
往后,人們依舊下田勞作,只是多了一些口舌:
你聞,這南洋風還有藥性味哩!
人哪!就該這樣死么?!
鄉 夜
雞們一上籠,再加上三二聲狗叫,夜就糯粉粉地漫下來,日子便在莊稼人的犁尖上和鍬刃下磨鈍了一截。活路也“嗝”在了夜里。犁地的農人,喘著粗氣一屁股蹾在田埂上,絕望地瞅著逼近又漫溢開去的夜色,先是揪心哀嘆自己的手腳慢了幾分,然后又埋怨這日影走得太倉促,像鷹子老鴰叼走一樣,說走就走了。哎哎,就差一犁呢,這塊栽秧田就犁整完了。這“嗝”在心里的農活當天不做完,夜里注定是會發餿的。好在農活是手里摸大的娃,閉了眼也能一把摸準鼻眼和脾性。于是就撲騰騰地趕起“嗝”下的活路來。夜呢,又被疼痛地犁開了一條口子。
赤腳走在田埂上,返青的茅草秧子像久違的姊妹,一個勁地支楞著腳丫子,心就有了著落處。田埂彎彎拐拐的,就像是老牛哪天掙斷的一根牛繩,很是隨意地阡陌在闊碩的鄉野,卻不經意牽住了人和牛的魂魄。沒有吆喝,沒有聲響,牛在前,人在后,只有走動著的兩條腿和四條腿,默契地把滿世界的黑,放在腳下的泥硯里,磨呵蹭的,夜色便濃糯成了一幅天然的水墨畫。這時的夜,就隨了田埂向夢的深處拐去。是的,跟早晨出工時顛了個個,那時,主人在前,牽了牛,悠著嗓子哼著花鼓調,向麥地或是稻田走去。播種的大事,一向都是主人做主哩!可是收工的路上,老牛卻牽了主人,走。這似乎成了多年的習慣或規矩。夜著實黑得像一口倒扣的大鐵鍋,可是不管有多黑,天生長了夜眼睛的老牛,總會準確無誤地把主人牽回家……就這么靜靜地走呵走,冷不丁,幾星牛糞鮮鮮腥腥地濺來,主人的臉上就生了一些天花。總是在村路和田埂碰頭的路口,總是在離家要遠不近的地方,那泡憋了很久很久的牛糞,就會極合適宜地打一個圓圓暖暖的句號。一天的勞作就是這樣結束的么?
牛欄剛墊了新草,老牛重重地臥下去,將一天的勞累揉在夜色里細細地反芻。晚飯時,男人就著一碟醬菜或一碗豌豆,滋滋有味地咪著老白干,再咪一口老白干時,夜色就咕咚咕咚一氣兒灌進了肚里。醉意中,猛地感到腿肚子發癢,手一摸,放燈下一亮,是一條腫脹溜圓的螞蝗。噫嗬!老子喝酒,你喝血哩。兩指輕輕一捏,血,便打了串兒地濺在土壁子上。娃兒調皮,用了竹簽“穿心過”,螞蝗就翻了個個,擱燈下一燒,夜,便噼噼啪啪有了一種辛辣焦糊的味道。睡意好像是隨了一陣穿堂風襲來的。一個哈欠,四肢就散了架。可夜色卻愈發地筋道起來。打了幾個結的燈繩就拴在床頭,仰手一扯,嘎——嚓,光亮就躲進了床底下。男人懶散地把自己躺成了一攤泥,哼哼著將一天的勞累和心嬌撒給女人。你看,這五大三粗的男人也有撒嬌的時候。女人有些不情愿,卻仍是將疼愛隨了笨拙的指法,絲絲扣扣地揉進男人的粗屁大鼾里。夢,就是自打第一聲鼾開始的。盡是些雜七雜八跟農事有關的夢。譬如,白天剛灌水施了拔節肥的那兩畝秧苗,忘了收田口子,肥水流跑了怎么得了?就扛了鍬,顛兒顛兒地向田野跑去。又譬如,收了這季莊稼,是種芝麻好呢,還是種黃豆劃算?正盤算著呢,爹挑著一擔農家肥氣喘吁吁地來了。爹都去世好些年頭了,可看上去還是老樣子,只是咳嗽得比以前更厲害了些。就上去要替爹捶背,可爹兇猛地一把打掉他的手,指著腳下的土地說,好好侍候侍候土地爺吧——這地都被化肥折騰成搓衣板啦!人虧地一時,地誤人一世啊!什么都可沒力氣,可把地沒力氣了,只得喝西北風!爹散完那擔農家肥,咳嗽一聲,就飄走了。翻個身,夢又變了花樣。怎么村長又來了呢。村長是來找他作證的。那天,明明是村長家的黑水牛吃了二五家的秧苗,可村長卻倒打一耙,反咬說是二五的黃牛吃的。好些人都看見了的,村長卻偏要拉他這個老實疙瘩作證。沒想他胸脯子拍得山響,說,這世道,馬無夜草不肥,田不耙不平,良知在心,公理在天,作證就作證!就說了真話,生平堂堂正正地做了一回人……要醒不醒的當兒,夢又將他鬼使神差地拽到了田里頭,哎呀!鬧轟轟的,黑壓壓的好多人呢。原來,是外出打工的村人紛紛返鄉,纏著村長要田呢。村長說,以前都把田當臭狗屎撂給村里,現在卻一窩蜂地要收回,真是吃了牛肉發馬瘋!有人聽了不服,說以前種田,這稅那費的,負擔重得挑不起,現如今種糧不繳一分稅,國家政策這樣好,誰不想多種幾畝田啊……
夢正靈靈醒醒摸了夜路兀自向前走時,可誰家的公雞打了一嗓子鳴,接著就是狗叫。狗似乎是叫第三聲的當兒,老牛也湊起了熱鬧,伸長脖子,朝夢的深處拐著彎兒長哞了一聲,就一聲,夜又往沉靜處走了幾個步子。正鼾是鼾屁是屁的男人一個激靈,夢就睜開了眼。猛地坐起,望著脹破了一屋子的月光,疑是睡過了頭,說哎呀!天都亮了,該下地啦。女人迷糊中蹬了他一腳,操你的心,才三更哩!男人又睡起了回籠覺,讓滿肚子的心事,四仰八叉地躺在夜的溫床上,滋滋潤潤地發芽、抽葉……
月亮確乎是出來了。有月亮的夜晚,鄉村的夜色就平添了幾許朦朧的姿色。你看,那田埂、草垛、樹木、莊稼……以及睡夢中的男男女女,都精靈兒似地變得生動而嫵媚起來。夢呢,像個回娘家的孕婦,只顧埋了頭,羞答答地邁著碎步兒,朝著最溫馨可親的地方一路走去……
月亮,是什么時候掛在天上抑或夢里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