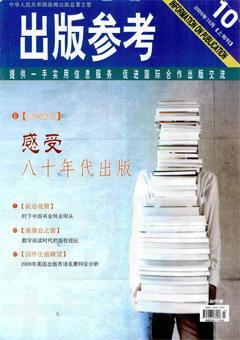感受八十年代出版
宋木文
所謂八十年代,當然是指二十世紀那個特定的十年。
講這十年的出版,不能不講作為起點的發生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場反思“文革”的撥亂反正。我有幸成為出版領域這場斗爭的積極參與者,批判“兩個估計”、緩解書荒,落實黨的干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調整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出版方針,都極大地解放了出版生產力,給主持八十年代出版工作的所有成員產生必須加快發展的強大動力和必須面對的巨大壓力。
主線是改革與發展
當時的形勢是,十年“文革”造成的精神與物質產品的極度緊缺,使剛剛解除禁錮的人們對書報刊的需求迅猛地增長著,要求出版必須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而客觀上又面臨著巨大困難。
這困難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其一是說生產精神產品的出版需要物質的保證,而國家當時對出版可能提供的物質條件又極其有限;當時出版賴以生存的印刷和紙張,前者技術落后、生產能力嚴重不足,后者屬短缺物資,供不應求,而解決這兩大矛盾,不僅受到資金短缺和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也受到經濟體制改革起步時存在的既有中央高度集中又有部門和地方分割帶來的困難,因而每前進一步都使人感到步履艱難。這是從中央領導到業內普通成員,都能感受到的。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和國務委員張勁夫主持的解決出版用紙的高層會議上,我看到因為某省拒調造紙用的木材就以減少對該省鋼材的供應來應對。胡喬木頗為感嘆地說:“用了不少行政命令的辦法,但還沒有解決問題”,“像現在這樣,年年花力量去解決紙張,不是辦法”,但為了對得起人民,還是抓了幾次。他還召我去杭州匯報1986年全國紙張安排的情況,對有關部門“只保課本用紙,不保其他圖書用紙”,會影響“知識分子的安定”,“也影響整個國家形象”,而深感憂慮。
其二是說,在出版工作方針的指導上,面臨著打破思想禁錮后出現的各種社會力量、社會思潮不同要求的挑戰,出什么書、出多少,一類書、一本書的出版,都會形成眾說紛紜的社會熱點,要求思想統一又難以統一,受上下左右夾擊的出版管理者,有時對這類問題的把握比解決物質條件的短缺還困難。至少我個人有這種體會,實話實說,因為物質條件的短缺可以上推下卸,而出版方針的把握則要自我承擔。例如,自1984年12月-1985年8月一窩蜂地競相出版新舊武俠小說,在半年多一點時間就出版164種、4406部,受到來自中央領導和學術界的嚴厲批評,迫使出版局向上送專題報告,檢查領導責任,向下發通報,控制出版品種和印數。探究競相出版新舊武俠小說熱,自有其滿足社會文化需求和追求經濟效益的合理因素,但也不能不考慮當時的社會承受能力,特別是當國家的紙張和印刷能力嚴重不足時,絕不能因集中大量印刷武俠小說而沖擊教科書和重點報刊的出版。
指導八十年代出版工作的綱領性文件,是中共中央、國務院1983年關于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這個“決定”是由胡耀邦提出,胡喬木指導,鄧力群主持起草的。“決定”規定了新時期出版工作的指導思想和工作方針;同時也對出版事業發展的重要緊迫問題提出了解決辦法。
八十年代出版工作的主線是改革與發展,且貫穿于全局和全過程。
發行體制改革先行
八十年代的出版改革是發行體制改革先行,始于1982年。
五十年代初,出版實行專業分工,出版社集中搞編輯出版,圖書發行由新華書店獨家經營,這種體制有其歷史的必要性,但造成流通渠道少,購銷形式和所有制形式單一,出版社不得辦批發,要辦集個體書店也受到限制。為搞活發行,解決買書難,國家出版局于1982年3月提出“一主三多一少”,即以新華書店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多條流通渠道,多種購銷形式,少流轉環節的改革方案。總結幾年來發行改革,主要是放得不夠,需要進一步放開。1988年中宣部與新聞出版署又把發行體制改革向前推進一步,實行“三放一聯”,重在放開,即:“放權承包,搞活國營書店;放開批發渠道,搞活圖書市場;放開購銷形式和發行折扣,搞活購銷機制,推行橫向經濟聯合,發展各種出版發行企業群體和企業集團。”
在推行“一主三多一少”、“三放一聯”實踐中,我感受到,發行體制改革與出版社的改革密不可分,但多年來在指導思想和方案設計上,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發行單位的改革上。在1988年討論出版社改革文件時,我提出必須把發行體制改革與出版社改革連結起來,而不是分割開來,要求“出版社既是圖書的出版者,又是圖書的經營者”,明確出版社總發行的地位,而不是“對新華書店發行補充”的那種“自辦發行”。后來又在認識上有所深化,提出“出版是基礎,發行是關鍵”,“應該把發行問題提到戰略地位上來”,“這個環節的問題不解決,整個出版工作就是‘一盤死棋”。
出版社改革在探索中前進
我看到,人們,包括一些出版研究者,把建國以后到“文革”前,甚至到這幾年轉企改制前,出版社都說成事業單位,有人甚至稱作“完全的事業單位”。其實,建國后,出版社一直被確定為企業單位,六十年代文化部也曾向國務院報告想把直屬出版社改為事業單位而未獲批準,只是上海按文化部報告精神經市委批準將所屬上海人民、上海文藝等出版社改為事業單位,出版社只設編輯部,同時將出版印刷業務剝離出來由經擴充的出版印刷公司統一經營。我在考察和回顧這起歷史公案時,曾含有意味地說過:“提出者未按原意落實,跟著辦的卻成功了。歷史就是如此。”
將出版社由“企業”變“事業”,是1983年的事。那一年有一次全國性的工資大調整。“文革”及以前近二十年沒調工資了。“調整”消息一出,人們歡欣鼓舞。但此次調資的范圍僅限于事業單位,而那時讓大家翹首企盼的“職稱評定”也限于事業單位。我時任出版局副局長,又分管這方面的事,必須想辦法讓出版社職工“坐上這趟車”。報告送上去,出版社由“企業”變“事業”,調工資評職稱乃至后來頒發政府特殊津貼都有出版了。但是,1984年開始提出的“事業單位,企業管理”,已經超出調工資時“事業單位”的含義,成為確定出版社屬性、指導出版工作一個帶方針性的提法了。現在經“轉企改制”的企業更不同于從前高度計劃經濟下的“企業”,而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企業”。
出版社改革是1984年在哈爾濱召開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上加以推動的。會議針對國家對出版社管得過死的狀況,提出擴大出版社的自主權,全社實行社長負責制,編輯部實行以提高圖書質量為中心的多種形式的責任制,用經濟手段促進精神產品的生產,以增強出版社自我發展的活力和能力。
出版社的改革是在探索中前進的。1988年5月由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署聯合
發出《關于當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見》,指出:“在發展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條件下,出版社必須由生產型向生產經營型轉變,使出版社既是圖書的出版者,又是圖書的經營者。為適應這種轉變,就需要積極而又穩妥地對出版社原來的體制,包括領導體制、經營體制、管理體制、人事體制、分配體制等進行改革,以提高出版社的應變能力、競爭能力和自我發展能力。”這是在當時主客觀條件下,對出版社改革可能提出的主要的和全面的要求。
八十年代的出版社改革,根據出版社從事精神生產的事業與企業雙重屬性,確定:“多數有條件的出版社要作為事業單位,實行企業化管理,通過逐漸改進和完善經營管理,不斷增強自我發展的能力和主動為社會服務的活力,對于另一部分不具備實行企業化管理的出版社,可以實行事業管理,但也要注意改善經營,逐步由生產型向生產經營型轉變,積極創造條件,爭取其中一部分能轉為企業化管理。”實踐證明,對出版社這樣確定屬性和實行不同經營管理,是符合當時情況的,是有利于推進改革和促進發展的。對比現在的轉企改制,或者可以說,這是在國家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并多次改變提法最后確定實行市場經濟的情況下,出版社由“事業”向“企業”發展轉化的一種過渡形態。我個人就是這樣,隨著認識的深化,1992年局長會議上提出出版是一種文化產業,建立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出版體制,有條件的出版社可以轉制為企業,隨后又提出“大部分出版社應該轉制為企業”,并論述其必要性和重要意義。當前的出版改革,如斌杰同志所說,有時間表、有路線圖、有任務書,正按轉企、改制、重組、上市,向縱深發展。
應當指出,八十年代的出版社改革有一定的探索性質,又是初步的,但改革也取得了基礎性的顯著成果,這主要體現在一批堅持改革,方向正確,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統一,面向市場而不是游離于市場的出版單位正在崛起,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以一批改革帶頭人為中堅的出版隊伍正在成長壯大,從這個意義上說,八十年代的初步改革也為后來進行全面深入改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適時進行書價改革
適時調整書價,對書價制度進行改革,是發展出版事業的重要保證。
1984年以后,我國的圖書價格有過三次改革,在領導班子,我分管書價工作,是積極參與者。
改革前,出版社執行的是1973年“文革”中制訂的定價標準,比1956年低標準定價還低。到了80年代,許多商品價格開始放開,出版的上游產品,如紙張、油墨、裝幀材料、印刷設備的價格不斷上揚,而出版社又要面向市場,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之路,原來出版一般圖書所享有的紙張補貼也逐漸被取消。國家不予補貼,出版社又無力自我消化,改革一般圖書的價格制度,勢在必行。
1984年主要進行兩方面改革:一是經國務院決定書價管理由原來中央集中統一管理改為由中央與地方分級管理,以地方管理為主;二是由我提議有關部門同意,將門類和學科分類予以簡化,由原來的正文38類、12個檔次,簡化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兩類;取消原有的12個檔次,只分上限與下限,做到既有相對統一的定價標準,又使出版社有一定的靈活性。這次改革改變了長期形成的出版物價格全國“一刀切”的管理模式。
第二次改革是在1987-1988年,有實質性的突破,實行按成本定價和控制利潤率的定價原則,定價權下放給出版社。當時受價格制度影響最大、出版虧損最多、出版最難而讀者特別是教學和科研人員又最為需要因而呼聲最高的就是印量少的學術著作。我同機關職能部門的同志一道去中國科學出版社作調查研究,并共同擬出3000冊以下的學術著作參照成本定價的辦法,經國家物價局批準實施。學術著作定價放開,對出版物價格改革的全局有重要影響。稍后,又將中小學和大專課本之外的一般圖書的定價放開,但為貫徹保本微利原則,實行宏觀控制,規定每社年利潤率不得超過總定價的5%-10%。
1993年啟動的第三次書價改革,主要是更明確地把書刊價格分為三類進行管理:中小學課本和大中專教材的價格仍按現行管理體制和管理權限實行國家,由地方和中央分別管理;對黨和國家的重要文獻,包括法律、法規、著作、文選,按照微利的原則由出版單位制定具體定價標準,定價權在出版社,國家主管機關進行必要的指導和調控;圖書的大多數品種的價格由出版單位根據紙張成本、印刷工價和發行冊數自行制訂定價標準。這樣,除教科書外,一般圖書的定價,基本上完全放開,由市場進行調節了。
我國書價體制改革是同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發展同步的,是逐步進行的,而且重大改革措施(如第一次書價改革)是報請黨中央和國務院主要領導同志批準的。在三次書價改革中,我們主要堅持了三條:一是保本微利、力求低廉;二是根據生產成本和市場需求由出版社自主決定價格;三是國家對書價實行分類指導和宏觀調控。
繁榮出版的十年
撥亂反正之后,國家出版部門歷屆領導班子都以多出好書為己任。就是1978年緩解書荒、恢復出版之舉,也是以重印一批中外名著得到普遍好評的。出書追求高質量,已成為我們的優良傳統,更是八十年代出版的主調。
我在1990年3月貫徹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壓縮整頓出版單位的全國新聞出版局長會議的工作報告中強調:“出版工作的成果,出版事業的繁榮,最終是靠多出好書來體現的。多出好書,這應當是我們各級出版管理部門,各個出版社的中心任務和調動本單位人員為之奮斗的行動口號。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十年,出版工作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是以出版了一大批高質量的重點圖書為標志的,今后的十年,我們應當有信心,也有條件在出版高質量重點圖書方面趕上并超過前十年,否則我們就將辜負人民的要求,有愧于后人。”隨后,這一年4月,署黨組制訂繁榮發展出版的十項措施上報中央;我又去上海調研,提出:多出好書促進繁榮是出版工作的永恒主題。
-
的確,如工作報告所講,八十年代是以出版了一大批高質量好書為標志的。例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一版)《中國美術全集》《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辭源》《辭海》《現代漢語詞典》《魯迅全集》(16卷本)《當代中國叢書》《走向世界叢書》《漢譯世界名著叢書》《不列顛百科全書》等都是這個時期出版或基本完成的。十年間以這樣一批高質量、上規模、標志性圖書問世,這是在中國出版史上并不多見的。
我在工作報告中寫入前引的這段話,是以八十年代的經驗啟示進入九十年代的工作,以不辜負人民的要求,不有愧于后人,怎敢不加倍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