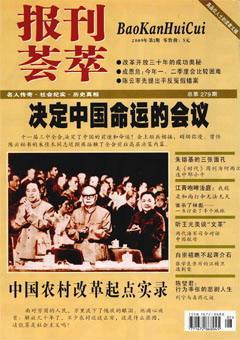誰殺了林彪
孫一先
擅長把報道和謠言拼湊在一起的美國記者炮制“精彩”故事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終于過去了,我們的國家歷盡劫波。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她逐步走上了改革開放的坦途。當年驚心動魄、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日漸遠去,有些被人們淡忘了。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
1982年,我奉派到紐約,在中國常駐聯合國軍事參謀團任職。1983年,一位華僑朋友向我推薦一本在美國出版的新書,是英文寫的,書名為《The Conspiracy andDeath of LinBiao》,作者Yao mingle。這是一本侈談“九一三”事件的書。1983年6月,由臺灣時事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譯成中文印刷發售,書名直譯為《林彪的陰謀與死亡》。8月,香港遠東評論出版社也翻譯出版,將書名更改為《林彪之死——流產政變幕后秘辛》。作者的名字,臺灣版譯為姚明理,香港版則譯為姚明樂,并指出按中文諧音似“要鳴了”的意思。從該書臺灣中譯本的用詞、用語、句法、語法來推敲,都是很流暢的中國話。書中涉及的一些有名有姓的重要人物,特別是在國內也鮮為人知的中共中央領導人的活動場所和一些軍事機密單位的地點,除作者有意掩蓋(例如說玉塔山實有所指,因某種原因而更改名稱)的以外,都是驚人的準確。我懷疑這本書是先用中文寫成,然后譯成英文出版的,而在其背后可能有一伙專門搜集中國大陸情況的人群或者一個專門機構。
該書的“緒論”,是由美國頗有名氣的“內幕記者”史丹利·卡諾寫的。這位記者曾替一家美國報紙在臺灣擔任特派員十多年,擅長把報道和謠言拼湊到一起,然后與官方消息來源相印證。1971年11月27日,他在《華盛頓郵報》頭版,以《林彪據信已死》的大字標題,第一個在美國披露了“九一三”事件的消息。卡諾在“緒論”中,雖然沒有直接肯定《林彪的陰謀與死亡》一書所編造的謊言,但他故意閃爍其辭地說:“這本書的故事確實和最近幾年有關林彪事件的謠言和報道相當吻合。”
起初,我對這本書并未在意,認為美國和港臺的出版商,慣于搞一些聳人聽聞的東西,來誣蔑中國共產黨。然而,由于這本書是用英文和中文兩種文字出版,在海外無論華人或者老外都可以閱讀,其影響由北美到歐洲逐漸擴大。
林彪外逃機毀人亡,一直到80年代中期,我國政府對其出逃細節和其座機墜毀原因,沒有對外公布過材料,海外的中國人,特別是一二十萬留學生,在尋求林彪死因時,自然把注意力轉向這本書。結果,使得這本書制造的謊言不脛而走,幾乎污染了半個地球。
這個趙研極自稱“在軍內地位很高”偷偷地去“發掘”另一個林彪
這本書的梗概如下:
首先作者冒稱是“看到中共中央有關林彪死亡文件的高干之一”。不僅如此,他還“看了參與林彪陰謀的人所做的證詞”,看得越多他越懷疑:為什么林彪毫未抵抗就接受失敗?為什么連動都沒動就放棄了武裝政變計劃?為了向讀者灌輸并加深這種疑問,作者捏造了一個名叫趙研極的人。1971年9月到1973年,這個人擔任“中央辦公廳特別調查小組”組長,任務是制造林彪事件的掩飾性文件。此人病死前曾留下一份回憶錄,被本書作者“發現”,作為全書第一章發表,并在其他章節中時而引用。
這個趙研極自稱“在軍中的地位很高”,但“已有很久沒有參與重要軍務”;他“從來沒有率兵打過仗”,1955年毛澤東授予他軍銜時說:“你在戰場外有卓越的貢獻。”1971年9月14日,汪東興把他從大連八七療養院接到北京,派給他的“任務是調查、研究并報告某些與黨中央所做有關林彪的中共中央聲明相抵觸的資料”。他在調查中發現,“以林彪的性格和經歷,竟會像只縮頭烏龜般躲在北戴河,任由他的愛人和兒子與毛澤東做生死斗爭,這似乎是不相稱也不可能的事”。由此他懷疑“除非有另一個林彪”,他于是就偷偷地去“發掘”這另一個林彪。
該書作者利用“趙研極的回憶錄”,把事情搞得撲朔迷離之后就根據他“所看到的‘中共中央一類檔案”,來編造林彪另有更大陰謀、最后死于毛澤東之暗害的神話。
連環套。是歷來武俠小說和驚險小說慣用的表現手法。該書作者也求助于這種方法。“創作”了陰謀中的陰謀這種離奇故事。書中寫道:
林立果當上空司作戰部副部長之后,就刻意發展“上海小組”等秘密組織。有一天,他對周宇馳說,要準備暗殺并推翻毛澤東,要周起草武裝政變計劃,并強調這是他爸爸的意思。事隔不久,林彪叫昊法憲去,向吳交了底:“現在主席是決心要我在他之前死,他也要你們全部陪我到八寶山去”。因此必須“使用特別手段”,“迅速行動,控制情勢”,“毛澤東的旗子不必摘下。但他的權辦要除掉”。之后,吳法競獲知林彪;已經同黃永勝做過類似的談話,很快也要同李作鵬、邱會作談。
林彪自己構想的“特別手段”,是與林立果的陰謀并行的另一套“宮廷政嚏計劃”,葉群和黃、吳、李、邱“一致贊許計劃精妙”。計劃的核心是制造中蘇沖突,同時借機殺掉毛澤東。實施辦法一個是對蘇聯發動突然襲擊,另一個是事先同蘇聯秘密接觸,請蘇聯合作制造戰爭;戰爭爆發,就請毛澤東躲到“玉塔山的工事”自保,然后用毒氣彈把毛殺死,尸體燒成灰燼;達到目的以后,就同蘇聯“從戰爭轉為休戰,敵對轉為結盟”。計劃既定,林彪一伙就讓總情報部的蘇軍情報處物色了一個兩面間諜吳宗漢,讓吳向蘇聯轉達他們的意圖。但是蘇方不相信,認為純屬開玩笑。
林立果起初并不知道他爸爸自己構想了另外一套計劃。他殫精竭慮地組織了“小艦隊”和“大艦隊”,以實現武裝政變的“571工程”。林立果“怕自己的名字沒有足夠的分量”,就向他的黨羽說政變“是我爸爸直接下的命令”。就在林立果緊鑼密鼓地在上海附近,指揮他的“小艦隊”準備打毛澤東乘坐的火車時,9月7日林彪把他緊急召去北戴河,表示不同意“用導彈炸火車這樣魯莽的辦法”,要他“趕快告訴上海的人立即停止”,并且向他講解了“玉塔山行動方案”。
9月11日,林彪在北戴河召集有林立果、周宇馳、劉沛豐等人參加的秘密會議,說明他的“玉塔山行動方案”:估計毛澤東將在9月底前結束旅行返回北京,初定于9月25日爆發中蘇武裝沖突,五天內戰線的長度和參戰的人數,將高五至十倍,緊急情況下,勸毛躲進“玉塔山”的指揮中心,林彪等人則在鄰近的“O號工事”里指揮作戰,此時調幾個心腹野戰師包圍“玉塔山”的8341部隊,然后讓“小艦隊”的攻擊小組,從地下通道進入“玉塔山工事”里,把毛澤東和其他領袖殺死。事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發布中央軍委的聲明,指出一個叛亂
集團以毛澤東和林彪為攻擊目標,現在已有藪地擊潰了這些反革命分手,宣布全國實施軍管,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推選林彪為最高領袖。
林彪和林立果的暗殺計劃。被周恩來從幾條途徑獲悉,周馬上通報給毛澤東和汪東興,建議即刻結束南方巡視之行。而且在抵達北京之前,要做出如何時付林彪行動的確切的決定。在毛澤東抵達天津的時候,周恩來通知毛,林彪意外地從北戴河回到了北京。
接下去。該書作者編造了一個“精彩”的場面。構成了全書的高潮:
9月12日下午,林彪在獲知毛澤東已出乎意料地提前回到北京之后,就同葉群帶了禮物“去拜訪他以示尊敬”。汪東興告訴他們主席已經入睡,主席定于今晚在“玉塔山”設宴,請林夫婦吃晚飯,主席已計劃要在那里住到國慶節。林彪雖然覺得可能有危險,但認為可借機觀察毛澤東的舉動,以便決定是否提前實施“玉塔山行動方案”。林彪赴宴前,到“O號工事”會見“四大金剛”和“小艦隊”的核心成員,商量是否馬上發動對蘇突擊。到會的人都主張不能再遲疑。就在擬定了作戰命令等待他最后簽署時,他突然改變了主意。認為不應該多疑而亂了方寸,決定“再等一陣子,等一切都準備好再行動,在本月的17或18日行動”。
9月12日晚8時10分。林彪、葉群帶了海鮮和人參等禮物,抵達毛澤東在“玉塔山”的別墅。席間,毛澤東專門打開一瓶明朝的老陳酒招待林彪夫婦。毛先談到南方巡視的經過,以及旅途的愉快,后又談到關于長壽的研究,并和林彪相互夾菜,氣氛親切而熱烈。宴席也有江青、周恩來、康生、汪東興參加。晚宴結束,這幾個人提前告辭,主席又挽留林彪、葉群談了20分鐘。10時54分,林、葉正式告辭,毛澤東和汪東興目送他們上車。
晚11時整,毛的別墅內外都聽得見接連兩次巨大的爆炸聲。原來是,林彪的座車以時速15公里駛過別墅外曲折的小路,在拐彎處離路障七至八米處滑停下來。這時,埋伏在附近的8341部隊的爆破小組,看到發射火箭的信號發出來了,隨即扣動扳機,瞬間一聲震耳欲聾的爆炸聲,一枚40厘米火箭彈不偏不倚打到汽車后部,接著第二枚火箭彈射向汽車的中部,汽車有好幾部分在火焰里飛向空中。前座的兩個人被炸得粉碎,后座的婦女,腰以上被炸成一堆破布與骨頭,坐在她身邊的男人炸得只剩下半邊臉,但身體尚有部分完好無損。
后來,那個趙研極檢視檔案中的照片,從死者右眼、眉毛,以及那半開眼睛布滿皺紋的四周,辨認出確實是林彪無誤。該書作者煞有介事地寫道:
這些照片與中央辦公廳公布給高干看的照片大不相同,后者是駐蒙古的中國大使館在飛機失事現場拍攝的。不用說,林彪躺在飛機殘骸里的照片,和葉群、林立果的照片一樣,都是經過改造的。
那么對于墜毀在蒙古境內的中國噴氣飛機怎樣解釋呢?該書作者繼續編造:
……林立果(當時已到西郊機場)突然之間變得不知所措,……周宇馳叫潘景寅率領機員登機,并打電話給機場說,空軍司令吳法完下令這架三叉戟準備起飛,然后叫劉沛豐陪林立果上飛機,……機上有七名機員,其中一名通訊員是中年婦女,其他都是男性:兩名駕駛員、一名領航員、一名總機械工程師,以及兩名機械員。……周宇馳在地面看到陸軍開進機場,正接近停機坪,就用無線電通知林立果立即起飛。林立果問周自己怎么辦,周說他可以乘直升機逃走,將在約定的地點會舍。
周恩來找黃永勝談話。說林彪已供認了他的秘密活動,將聽候命令,接受審查。黃永勝感到已無回避余地,林彪屈服了,他只能跟著做。周令黃給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打電話,說他已認罪。這幾個人看到已別無選擇,也都俯首認罪。周要吳法完到空軍指揮所去,向各軍區空軍和指揮中心發布命令,禁止全國各機場起降任何飛機,并問他是否可以迫使逃走的那架噴氣式飛機下來。吳指示北京空軍司令李際泰,派四架殲7飛機,從楊村機場起飛,去內蒙古追那架三叉戟噴氣機。當那架飛機朝中蒙邊境飛去時,周問吳怎么辦,吳主張將它擊落,周同意,吳就讓李際泰下令靠近邊界地區的三個導彈營發射地空導彈。那架飛機進入蒙古領空后,就從雷達屏幕上消失了。據空軍的攻擊效果分析報告認為,第一批導彈已將這架飛機擊中使其受傷,但駕駛技術高明的潘景寅,立即降低高度躲避雷迭追蹤。
三叉戟256號飛機墜毀后,在烏蘭巴托的中國大使館派人到失事地點展開調查。大使館用電報傳回北京外交部呈周總理的秘密報告上,標有“81029號絕密文件”字樣,里面說墜機的乘客年齡在二十至五十歲之間。大使館努力安排把尸體運回中國,但后來接到一項命令一事實上是毛澤東直接下達的——要尸體就地埋在墜機地點附近。
蘇聯和蒙古均派技術人員對已埋葬的尸體進行檢驗,至少有一些蘇聯的驗尸人員不相信林彪是那次墜機而死的乘客之一。
文章到此完而未完,作者在該書最后一章,引用“趙研極的回憶錄”,說1973年汪東興透露了干掉林彪的安排,是毛澤東一手策劃的,在返回北京的火車上,就已確定了實施計劃,而且“毛澤東堅持在林彪所選擇的政變地點,來打他和林彪的最后一仗”。
從這本書的以上主要內容,可以看出它的險惡用心所在。它鉆了我國保密制度嚴格,關于林彪外逃細節及其座機墜毀詳情一直沒有發表官方詳細材料的空子,大肆造謠生事,混淆視昕,并且一版再版,擴大發行范圍。它的污染范圍之大,影響之深,使當代許多演義性小說望塵莫及。無論是北美、歐洲、東南亞國家的華人,還是從這些國家回國的留學生,或者常駐國外和臨時出國的公務人員,都傳聞林彪并非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附近,而是在北京被毛澤東搞掉的。這些國家的老外就更不用說了,他們更容易相信這本書的內容。原蒙古外交部專員、曾參加中蒙雙方視察林彪墜機現場的古爾斯德,一直堅信墜毀的飛機上沒有林彪。當我向自己接觸到的海外歸來的年輕人講明事實真相的時候,他們也往往以《林彪的陰謀與死亡》一書的論點,同我爭辯。
我深感有必要也有責任,向公眾說明導致林彪機毀人亡的事實真相,以澄清視聽。于是,在我任職期滿回國以后,1986年冬天,在一個出版社的朋友勸說下,以筆名“伊白”寫了一篇文章《林彪折戟沉沙目擊記》,發表于《萬象》雜志1987年1月號上。這份雜志雖然很快被搶購一空,一些小報爭相摘登,好些讀者給我寫信,但它的影響畢竟有限。
我撰文揭示歷史真相弄清十個問題
《林彪折戟沉沙目擊記》一文發表后,引起了中央黨校黨史專家于南教授的注意。他于1987年4月22日給我來信,說1979年4月至1981年2月,他參加過“兩案”
的審理工作,看到駐蒙古使館報回的關于林彪墜機事件的文電和照片。說他這些年一直在研究林彪問題。在一些地方講過“九一三事件”;由于當年看駐蒙古使館文電和照片時不準抄錄,僅憑記憶有限,因而我的這篇文章為他解決了很多問題,在最近給黨校培訓班和研究生班講課中,運用了這篇文章的材料。他在信中指出了我文章中記憶不準的幾個情節。
我此前并不認識于南教授,他是在參加審理“兩案”時,看到我1971年9月24日,寫給周總理關于林彪座機殘翼那個大洞的分析報告,從而知道了我的真實姓名,后來又從我50年代一位老鄰居那里,打聽到我的下落。在這以后,我同于南教授建立了聯系。并在1987年6月和1988年5月,應他之邀到中央黨校給黨史師資培訓班和研究生班講過兩次課。
于南教授在同我的交往中,給我看了《黨史信息》上刊登的胡耀邦總書記1986年11月16日的一段講話拼交換對《林彪的陰謀與死亡》一書的看法,共同感到不能聽任國外惡意造謠這樣廣泛流傳,我國官方應該發表文章,揭示林彪外逃墜機的真相,澄清國內外視聽。
胡耀邦的這段話,大意是:“中央對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做出了決議(按: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但只能是原則地說說,有不少重大的歷史事件不要說年輕的中央委員不知道,就是有些年老政治局委員也不大清楚。這些重大歷史事件不在我們中央委員中講清楚,將來老同志不在世的時候,就說不清楚了。因此,中央委員對1949年以來的主要歷史事件應該知道。”接著,胡耀邦列舉了10個題目,要求有關部門研究編寫:
1,張聞天、王稼祥“二十八個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2,“三反”、“五反”是怎么回事;
3,抗美援朝是怎么一回事;
4,高崗、饒漱石的錯誤在哪里:
5,廬山會議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開起來的,為什么把彭德懷同志給“揪”出來了;
6,“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搞起來的;
7,林彪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8,江青、張春橋在歷史上究竟是不是叛徒:
9,“四人幫”是怎樣被抓起來的;
10,華國鋒同志不正確的地方在哪里。為什么把他換下去。
胡總書記講話以后,社會上興起一股寫“文革”、寫“九一三”事件的熱潮。我給許文益大使打電話,建議外交部組織編寫有關材料。許大使給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主任裴堅章寫了一封信,建議由他找同去林彪座機墜毀現場視察的沈慶沂、王中元和我,組成編寫組,研究寫出視察墜機現場和外交交涉的經過這段歷史真相。1987年5月,編寫組成立。調閱了外交部的有關文電,并去中央檔案館查閱了檔案,訪問了李耀文、韓念龍、符浩等同志。經過半年的研究和寫作,最后完成了兩篇文章,一篇是許大使的《歷史賦予我的一項特殊任務——“九一三”事件的對外交涉》,另一篇是我們三人合寫的《視察林彪叛逃飛機墜毀現場紀實》。另外,外交史編輯室還請符浩寫了一篇《“九一三”事件補白》。這三篇文章刊登在內部發行的《外交史資料》1987年第6期上。后來,1988年1月15日,公開出版的《黨的文獻》雜志(總第一期)予以刊登。1990年5月,又收入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國外交風云——中國外交官回憶錄》一書中。
許大使的文章,除在《世界知識》等國內報刊上刊登外,1988年5月,還譯成英文,在向海外發行的《北京周報》第21、22期上發表,引起了國際上廣泛的注意。在巴黎出版的《歐洲時報》及其他海外中文報紙全文或摘要登載。有的外國報紙發表短評或質疑,他們不明白中國官方為什么在這個時候披露林彪出逃飛機墜毀的真相。
1988年1月31日和2月1日,新加坡的《聯合晚報》,連載了我在1987年1月發表于《萬象》雜志上的《林彪折戟沉沙目擊記》,他們換了個標題:《荒原上的疑云》,而作者用了我的真名,不是發表該文時的“伊白”。
1988年春天,我應《解放軍報》兩位副總編的要求,‘寫成《罪與罰——林彪墜機現場視察紀實》一文。從4月25日至5月30日,連載于該報第三版上,在軍內引起熱烈反應。由于這份報紙是在軍內發行,因而社會上看到的人不多。
以上“親歷者”所寫的這些文章,有力地駁斥了《林彪的陰謀與死亡》一書編造的謊言。
西方世界的新聞媒體,對新中國一直存在著固執的偏見。加以臺灣和香港地區的某些報刊興風作浪,他們散布大量懷疑論調,不相信我國作者揭露的歷史真相。
林彪究竟是怎么死的,死在北京還是蒙古的草原上?對于最后澄清這個歷史真相做出貢獻的是澳大利亞的一位年輕記者彼德
在北京出版的《作家文摘》第80期(1994年7月8日)摘登了李安定寫的《林彪之死真相查訪記》,詳細報道了彼德·漢納姆的整個采訪活動。該文稱從1993年5月開始,彼德·漢納姆用了半年的時間,鍥而不舍地奔走于蒙古、俄羅斯、美國及臺灣、香港,往返數萬公里,寫出了第一手調查材料,發表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志上。此事立即引起國際上的廣泛關注,許多國家的報刊對他的文章予以轉載和評述。西方的媒體認為,彼德·漢納姆所進行的采訪,“其意義在于,中國官方關于林彪之死的解釋,第一次由一個西方記者通過客觀的獨立調查給予證實”。
漢納姆起初是自己出錢,進行這次采訪旅行的。首先他來到改變了社會制度走向自由化的蒙古,自己雇車到達林彪座機墜毀現場。原來保護現場的鐵絲網已被拆除,附近居民哄搶了飛機殘骸,一些較大的部件,由貝爾赫礦區派人運走,賣給了中國商人。漢納姆在現場只揀到十二塊飛機殘片。現場附近的居民向他講述了所見飛機墜地燃燒及尸體情況,許多人不知道林彪是誰,更無法證實林彪在這架飛機上。
漢納姆回到烏蘭巴托,找到一個過去在蒙古外交部擔任英語翻譯的人。此人講,中國飛機墜毀不久,公安部找他去翻譯一張英文紙片,他看了有點惶惑,原來是避孕藥的說明書。公安部的人笑了,說這個說明書是放在失事女尸的手袋里。漢納姆據此分析,葉群時年五十一歲,已過了使用避孕藥的年齡,由此判斷這個女尸不是葉群,那么林彪是不是在飛機、逃亡就很難說了。
正在“山重水復疑無路”的時候,漢納姆找到了當年參與蘇聯專家檢驗遇難者尸體工作的蒙古病理專家莫尤(按:此人是中國大使及其隨員視察墜機現場時,蒙方隨行的衛生組法醫)。這個人向他描述了一些鮮為人知的情節:
1971年9月13日,中國噴氣飛機墜毀的當天,蘇聯人就趕到現場。這批蘇聯人是由軍人和航空專家組成的調查組,他們負責了解飛
機墜毀的原因,但他們對九具尸體不屑一顧,而對這架英國制造的三叉飛機更感興趣,把三臺羅爾斯羅伊斯公司制造的斯佩式發動機中尚完好的一臺拆運回蘇聯。
蘇聯當局根據其駐華使館的情報,認為應該對這架飛機上乘坐的究竟是什么人弄弄清楚,于是在飛機墜毀五周年之后(按:后來俄羅斯報紙又稱為9且下旬),派克格勃的調查組來到墜機現場。他們把墓地的棺材全都挖了出來,逐個檢驗因天寒地凍而未完全腐爛的尸體,在蒙古專家的幫助下,首先肯定了尸體的所有傷痕都是因飛機墜毀造成的,排除了乘客是在墜機前死亡的可能性。
克格勃調查組雖然帶來了“九一三”以后中國再沒有公開露面的領導人資料,但燒焦的尸體已面目全非,比照資料難以判定。于是,他們割下了那個女人和那個歲數最大的男人頭顱,放在大鍋里架起柴火煮,目的是將毛發、皮肉剝離干凈。這種殘酷的做法,外行人看來實在是異常恐怖。最后,蘇聯人把兩個煮干凈的頭顱裝箱帶回蘇聯。
漢納姆聽了蒙古專家的講述以后,認為揭開謎底必須到莫斯科去。但是,到那里找誰呢?他在烏蘭巴托苦苦追索中,得到一張當時蘇聯調查組人員和蒙古官員聚餐的照片,有人向他指出其中一位是來自莫斯科第三醫院的托米林一調查組的主要病理學家。
漢納姆用自己的稿費買了機票,想到莫斯科來個順藤摸瓜,弄清真相。但在一個國際大都市中,憑一張照片、一個名字來尋找一個人,實如大海撈針。當他得知莫斯科第三醫院已經撤銷的時候,真像是當頭挨了一棒。但他并沒有死心,拿出照片幾乎找遍了莫斯科的大小病理實驗室,終于有人認出了托米林,給了他一個電話號碼。
托米林友好地接待了漢納姆,但他拒絕回答有關問題,強調他同克格勃有協議,不得泄露調查結果,盡管克格勃不存在了,仍然要經過克格勃的后繼機構的批準,他才能把秘密公開。
漢納姆費了很大的周折,弄清了取代克格勃的新機構,遞去了采訪申請。當時正值盛夏,俄國官員許多都到郊外度假去了,漢納姆一趟趟跑,也找不到要找的人。簽證眼看到期,錢也花得差不多了。幸好。《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志知道了他的采訪計劃,愿意給予部分資助。于是,他利用等待莫斯科官方批準的時間,到美國去從另一個角度進行調查。
在美國,漢納姆訪問了外交界、情報界、新聞界許多人士,收獲甚微。一個華人餐館的老板介紹并安排他同在紐約的張寧見了面。張寧原是一個歌舞團演員、老紅軍的后代,“文革”期間經過“選美”來到毛家灣,成為林立果的“未婚妻”。“九一三”之前,她隨林家到了北戴河96號樓。張寧向漢納姆訴說了自己的遭遇,講了葉群、林立果和林彪出逃的情況,她肯定林彪乘上“三叉戟256號”飛機飛走。
漢納姆重返莫斯科,驚喜地獲悉托米林得到批準向他講明當年的事實真相。
1993年10月,托米林在他的辦公室會見了漢納姆,在座的還有當年飛機墜毀事件調查組的負責人、原克格勃的將軍扎格沃茲丁。他們的對話如下:
“林彪和他的夫人葉群在這架飛機上,他們是因為這架飛機墜毀而喪生。”扎格沃茲丁斷然地說。
“你們如何證實這個結論呢?”漢納姆問。
托米林拿出一包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和資料,其中有一張從正面和左右側面三個角度拍攝的頭骨照片。托米林指著照片說:“這正是林彪的頭骨。”并解釋說林彪的頭部在戰爭中受過傷,其位置正好與頭骨的傷痕相吻合,而且蘇聯保有林彪1938-1941年在莫斯科治病的詳細病歷,有關林彪牙科記錄也與頭骨的實際情況絲毫不差。
扎格沃茲丁補充說:“我們另一個鑒定方法,是用頭骨對照了林彪生前的照片。克格勃的資料里有一張俯拍的免冠照片,清楚顯示了林彪頭部的傷痕。我們還把頭骨照片和林彪過去的一些照片疊放,看到兩者的輪廓完全重合。”
托米林還說,人們的耳廓如同指紋,一個人一個樣,沒有重復的,因而是鑒定身份的重要依據。當年從現場割下了那具女尸的一只耳朵,與葉群的有關資料對照,得出了相應的結論。
為了使鑒定頭骨和耳廓的的結論萬無一失,克格勃的這個調查組,根據林彪病歷中患過肺結核的記載,重返蒙古檢驗尸體。托米林記得那天正好是11月7日十月革命節,北風怒號,天寒地凍,他們挖出了林彪尸體,在其右肺確實發現鈣化的硬塊,與病歷中的X光片一致。
調查組的工作,使蘇聯最高領導非常滿意,他們得到了嘉獎和晉升。扎格沃茲丁擢升為將軍,托米林則獲得領導國防部所有病理實驗室的特權。
扎格沃茲丁對漢納姆說:“二十二年來,全世界只有四個人知道這個事件的結果——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當時的克格勃主席)、托米林和我。今天,我們把這個調查結果透露給你。”
漢納姆當然心滿意足,他半年來艱苦的奔波采訪,終于找到了一個歷史懸案的謎底。最后他問了一下這架飛機上有沒有黑匣子,扎格沃茲丁說黑匣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鑒定時沒有發現錄音里有飛機和地面的通話。
漢納姆的采訪報道,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披露之后,許多國家的報刊予以登載。其影響相當廣泛,使得《林彪的陰謀與死亡》一書所散布“林彪是在北京被毛澤東搞掉的,沒有在那架墜毀的飛機上”的謠言及其造謠者。消弭得無聲無息。漢納姆的采訪報道問世不久,新華社《參考消息》1994年5月21日,登載了俄羅斯軍隊的《紅星報》報道的《林彪事件鑒定始末》。據稱他們于1994月5月派記者采訪了托米林。托米林的真實身份是退役少將軍醫,當年已是著名的犯罪偵察學家、經驗豐富的法醫和高級專家,剛被任命為國防部法醫學實驗所所長。與他同去蒙古進行調查的,有克格勃的偵察員扎格沃茲丁及其助手病理學家沃爾斯基。
托米林回憶說:
“9月的一個早晨,克格勃的一位領導打電話問我能否立刻出一趟國,我說當然可以。”“幾天之后。我們乘飛機抵達烏蘭巴托……在蒙古士兵的保護下驅車找到了飛機墜毀現場,一群野狼已在那里筑了窩,士兵們對天鳴槍驅走了狼群。我和沃爾斯基則開始掘尸檢驗。尸體共有九具,全部燒得面目全非并已高度腐爛,我在兩具尸體的口中發現了做工相當精細的金齒橋和金牙套,于是決定將這兩具尸體的頭骨帶回烏蘭巴托。我只是憑直覺才這么做的,當時根本沒有什么猜想。”
托米林回到蘇聯駐蒙古大使館,翻閱幾本雜志時看到了林彪的照片,他心里一動,脫口而出:“真像啊!”回到莫斯科以后,他便收集大量的林彪的照片,在一張脫帽照片中,發現了林彪的右太陽穴稍上處有一道明顯的疤痕,而從蒙古帶回的頭骨上也有這么一條傷痕。當他找來林彪過去在蘇聯治病時的病歷,一張x光片上清楚顯示了其肺部結核鈣化的硬結。于是他決定再次飛往蒙古,陪同他的是人體形
態學研究所所長佩爾米亞科夫。
“當時已是11月,天氣寒冷,我們每過5分鐘就得把手伸進溫水中暖一暖。結核病灶很快便找到了。臨走時,我又收集了那兩具尸體的幾塊骨骼和所有牙齒。回國后,我對那幾塊骨骼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死者的身高和年齡同林彪及其妻子葉群的身高和年齡完全相符。”
托米林怕萬一有失,決定用拉特涅夫斯基氏液(由酒精、醋酸和漂白物質組成的混合物,可以大體恢復半腐敗器官的形狀和大小,甚至恢復肌肉彈性),來檢驗在飛機失事現場割下的林彪和葉群的耳朵。實驗結果再次證實了前面的結論。最后,在向安德羅波夫匯報鑒定結果之前,托米林找到了能根據人的頭骨構造恢復其面貌的專家,復制出林彪的頭像,結果同照片分毫不差。
彼德·漢納姆的報道和俄軍《紅星報》的采訪,從蒙古方面也得到了印證,并有進一步補充。1998年2月18日,《參考消息》刊登日本《朝日新聞》記者對“九一三”時任蒙古外交部副部長的云登的采訪報道。云登肯定地說:
9月14日,蒙方本來要派專機運送中國駐蒙古使館人員去溫都爾汗視察現場,突然接到蘇方通知,蘇軍直升機已從赤塔飛到中國飛機墜毀現場進行調查,并拆走飛機上的一座引擎,因而運送中國人員的專機不得不推遲至15日下午起飛。云登還證實,死難者尸體掩埋四五周(按:此時間與漢納姆所講一致)后,蘇聯掌握了情報,認為“似乎是林彪乘坐的飛機”。10月中旬,蘇聯國防部法醫部門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兩名將軍到現場,從墓中挖出了據信是林彪及其夫人的遺體,割下頭顱帶走了。11月,這兩位將軍再次來到現場,詳細檢查了被割掉頭部的男性遺體,并帶走了上半身。當時有蒙古的兩名法醫在場,但在事后蒙古政府被拋在一邊,尸骨也沒有歸回原葬墓地。云登透露,中國飛機墜毀現場發現了大量軍用物品;包括:中國空軍密碼,含師級名稱在內的飛行指示書,寫有部隊名稱的燃料購買證,出入部隊的身份證明書,軍用手槍(中國造六支、蘇聯造一支)及一支自動步槍,軍裝和軍隊相關書籍,等等。蒙方認為中國軍用飛機侵犯領空,進行間諜飛行或破壞工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機上遺物情況沒有告訴中國方面。中國方面雖要求歸還機上遺物,但當蒙方要求提交全體機上人員名單時,中方撤回了自己的主張。
后來,云登又接受了日本《星期日周刊》記者的獨家專訪,對上述說法做了若干補充,其中較重要的是:“我方人員在機內發現有軍用航空地圖,地圖上從河北省北戴河穿過失事現場,一直畫線畫到貝加爾湖附近的伊爾庫次克,目的地是當時與中國為不共戴天之敵的蘇聯”;“此外,機上裝備有蘇聯制造的高度儀”,“當時在操縱室里有兩個高度儀,一個是該機從巴基斯坦購人時便已安置好的普通高度儀,另外一個是專門用于低空飛行的特別高度儀,屬于當時蘇聯最尖端的儀器,并未供應給任何國家,即便是同盟國的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