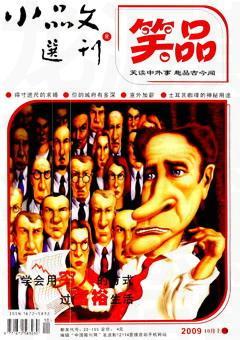最深情的語言等二則
范愛萍
老友在外地開一家汽配商店,邀我前去幫忙打理。一個月后,我完成任務急忙回家。剛下火車,我的手機便“嘟嘟”地響個不停,是老伴問我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我說:“在回家的路上。”末了,我順口說了句:“想你了。”
回到家,老伴接過我手里的提兜,我到衛生間洗了手,然后坐到沙發上。她一下摟住我,對我說:“剛才在電話里說什么了,再重復一遍。”我真的記不清楚自己剛才講些什么了,只好應付說:“不就是說了句馬上回家嗎?”老伴說:“不對。”我搜腸刮肚,結果還是想不起來。老伴看我抓耳撓腮的樣子,捂著嘴笑著說:“就那句‘想你了,再說一遍。”我恍然大悟。但是,讓我面對著老伴再說出這句話,還真的有些難為情。我對她說:“吃飯吧,剛才不是說過了嗎?”她說:“不行。”我說:“都老夫老妻了,那都是年輕人的浪漫,咱就別玩啦。”可是,老伴真的鐵了心,我不說就不讓吃飯。我壓著嗓音含含糊糊地說了一聲,她搖搖頭,說沒聽清。我提高了嗓音,但說得還是有些不清楚,她生氣地扭過頭。我只好鄭重其事地大聲說:“老伴。我想你了!”沒想到,老伴聽到我這帶著感情、發自肺腑的聲音,眼淚竟流了下來。
外出一個月。挺想家,也想老伴。但沒想到,一句普普通通的“想你了”,在滿頭白發的老伴聽來,竟然是天底下最甜美、最深情的語言。
黎志摘自《牛城晚報》
臨刑前的情愫
柴靜
她當上警官那年,年紀還小,笑臉緋紅,肩上搭著兩條照亮的大辮子。
他偷盜,搶劫,后來,是她那里的囚犯。
她形容他的樣子:“眼睛特別亮,留著胡子,笑起來,嘴角這樣歪一下。”
每次提審,他們都遇上。
再以后,換別的警察,他一聲不吭。
等她來,他嬉皮笑臉地說:“我要吃個燒餅。”她氣鼓鼓地甩一下辮子,還是去買了。
他們也談審訊筆錄之外的東西。她慢慢才知道,他是紅軍的遺孤。,再后來,他們用眼睛交談。
她的眼神說:“你沒有希望。”他的眼神說:“可是我喜歡你。”
她勸他改好。但是一次、兩次,他們見面的地方,總是提審室。
最后一次見面,是在法庭。
她在他身后站著。
“錢愛勇,違反刑法第232條,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他突然回身,看見她。她的眼淚“嘩”地一下滿臉都是。身邊同事捅捅她,她什么也感覺不到。
他也哭了,手被縛著,只能甩著頭把眼淚從臉上甩下去。
她的眼神說:“我說了讓你改,我恨你!”他的眼神說:“可是我喜歡你。”
他被推上車帶走了。她失控地追著車跑,追到看不見車為止。站住的時候,她下意識地看腕上的表,直到現在她還記得表上的時間:11時30分。
然后,她站在原地,35分,40分,45分……12時整。
槍聲響起。
這是今天,朋友們在飯桌上,她講出來的故事。
她現在是一個大城市的公安局局長,一個27歲女兒的母親。
隔了30年,她也許是這個世界上惟一記得他的人。她說:“人可以犯很多罪,但是愛,沒有罪。”
摘自《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