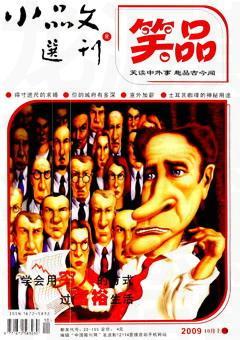擺譜
李開周
我發現過去那幫文化人挺能擺譜的。
比如說蘇軾,他在江邊一樓上睡覺,大床貼著窗戶,什么時候想看外面風景,伸手把窗簾拉開就行了。要是懶得用手,他用腳也成——人躺在床上,大腿高高翹起,腳丫子蹬住窗戶縫兒,一使勁,咦,窗戶開了。就這么簡單。
可是這么簡單的事兒蘇軾自己不做,非讓長隨去做。長隨住在樓下,蘇軾要向他下達開窗戶的命令,得扯著嗓子喊,喊這一嗓子的熱量消耗再加上長隨爬樓所做的功,開百八十個窗戶也夠用了。所以從工效的角度看,蘇軾純屬吃飽了撐的。
蘇軾不這樣看,他覺得這才風雅,才符合他文化人的身份。用他自己的話說,“東坡于榻上慨然長噫,欠身起立,使童子啟戶,憑欄而望之。”他老人家挺尸在床上“慨然長噫”,長隨卻要屁顛屁顛跑去“啟戶”,這場面像極了秘書給局長拎包,小弟給老大點煙,又體面又瀟灑,官派和貴氣兼而有之。
在北宋,地方官赴任前都要雇幾個仆人,路上挑行李,到任后做保姆,時稱“長隨”。一個長隨一年的吃住和工資加起來,最多二十貫銅錢就能打發了,而北宋官員俸祿極其豐厚,像蘇軾這樣的干部,工資加職田加衣賜加公使錢,每年能掙到幾千貫,雇一百個長隨也沒問題。
到了明朝,市井小販收入極低,一年能掙三四兩銀子就不錯了,可是只要那小販愿意儉省,五年下來就能買一丫鬟。大概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明朝有丫鬟的家庭極多,在明話本里,武大郎那般窮困潦倒,竟然也有一個一叫迎兒的丫鬟。
長隨和丫鬟都有存在的必要,因為總得有人忙于工作,總得有人忙于照顧這些忙于工作的人,大家因分工不同而互惠互利,這是好事兒。然而很多時候,被忙于照顧的那些人并不忙,他們之所以雇一保姆,只為能像蘇軾那樣擺譜。更荒誕的是,有些雇了保姆的人也并不富,他們之所以能雇上保姆,只是因為被雇的保姆比他們還不富。
據說有些日本女人到了中國,就不想再回去了,原因是中國生活太方便,一個人只要稍微能掙點兒錢,就能雇一群保姆,把自己照顧得跟一奴隸主似的。而這種好事兒在日本就很難碰到,因為日本沒有那么多赤貧群體,做奴隸主的成本太高。
納水摘自《城市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