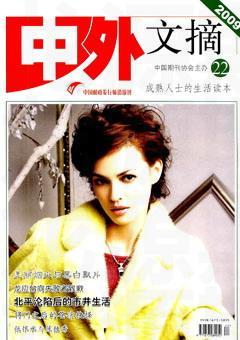公務用車60年演變等二則
李 婧
“所謂公務車,是指國家財政出資購買的,用于政府事務的車輛。建國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政府公務用車也在不斷改革。具體來說,可分為四個階段。”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院李文釗博士在接受《環球人物》雜志記者采訪時,對政府用車的歷史演變做了詳細解說。
第一階段:物質匱乏,百廢待興(1949—1978年)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建立了公務車使用制度。汽車作為一種生產資料配給政府官員,嚴禁私人購買。
在建國初期,國家領導人坐的車輛,許多是解放戰爭時期保留下來的。1949年,毛澤東進入北平前出席閱兵時,乘坐的就是繳獲過來的敞篷吉普。
隨著一汽等中國本土汽車廠的建立,中國開始制造自己的汽車。此時,公務車的來源是蘇歐采購與國產汽車相結合。進口公務車的使用僅限于省部級以上的干部,其他級別的機關配車基本以吉普等車型為主。
當時的高檔進口公務車莫過于裝備8缸發動機的前蘇聯吉姆牌轎車。這種車最初是供國家領導人使用的,后來配備給副省級以上干部。類似車型還有波蘭產華沙204轎車,前蘇聯伏爾加M21轎車、勝利M20轎車等。公務車中,國產的轎車包括紅旗牌轎車、上海牌轎車、北京212吉普等。
第二階段:初步發展和混亂期(1978—1994年)
改革開放初期,作為重要生產資料的汽車依然實行計劃生產,統一調度,統一分配,并沒有馬上進入大眾消費領域。由于對各級政府部門擁有車輛的管制放松,再加上合資廠商生產遠遠不能滿足需求,因此,大量的轎車進口在所難免。這個時期是公務車采購的第一次大規模發展時期。但是,由于缺乏統一的管理,財政資金浪費較為嚴重。
數據顯示,1984年全國進口的轎車、面包車高達20萬輛,耗資近20億美元,超過了前30年的總和。“八五”期間,全國公車耗資720億元,年遞增27%,大大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
這一階段,最早風行的是日本車,比如豐田皇冠、尼桑藍鳥、公爵王等等。隨后是桑塔納和奧迪。1985年,中國引進了德國品牌桑塔納,到1993年取消汽車控購前,國產桑塔納全部由原國家計委和全國各省區計委統購統分。
1988年,奧迪授權中國生產奧迪100,第一年生產了近500輛,它迅速為公務用車所青睞。
第三階段;定規建制期(1994—2002年)
1994年,《關于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定》出臺,對于不同層級干部的座車配備第一次有了排量和價格的限制。
1999年,我國更明確規定了不同層級干部的車輛配備標準:省部級干部配備排氣量3.0(含3.0升)以下、價格45萬元以內的轎車;副省部級干部使用排氣量3.0升(含3.0升)以下、價格35萬元以內的轎車,黨政機關的其他公務用車一般配備排氣量2.0升(含2.0升)以下、價格25萬元以內的轎車。同時,第一次提出政府采購的概念,不過,這時候的政府采購還基本屬于零散式的采購,各個單位需要什么,就報批什么。
第四階段:程序完善,依法采購(2002年至今)
2002年6月29日出臺的《政府采購法》從法律上對公務車采購做出了更明確的規定,使得政府采購第一次有法可循,政府采購向集中采購轉變,這讓采購更規范、更透明、更經濟。
《政府采購法》中規定,集中采購要通過集中采購機構來進行,因而獲得政府采購的前提是進入集中采購機構公布的采購目錄。
2006年10月,財政部聯合環保總局發布一項“綠色清單”,就公車采購部分,該清單規定只有“東風標致、東風雪鐵龍、本田思域、奧迪A6奧迪A4、寶來、捷達、開迪(Caddy)、現代等九大品牌的車型獲得中國環保標志產品認證。
然而,遺憾的是,這份清單中沒有一家本土企業的產品入圍。或許意識到了這點,2009年的第4份“綠色清單”,逐漸加大了企業品牌的數量。
不過,自主品牌仍面臨尷尬:入圍只是獲得采購資格,并不必然表示政府機關一定要進行實際采購。從某種意義上講,自主品牌似乎只是獲得了一種名分。
摘自《環球人物參考》
當哈佛教授遇到世界名牌市場總監
洪晃
有一次,一個女主人在一個大型晚會上精心安排一對“男才女貌”坐在一起,想讓他們邂逅一下。男的給女的讓了座,然后問道:“你是做什么的?”
女人非常自豪地亮出世界名牌市場總監的頭銜。
男人說:“嗷,你是賣包的。”
“那你是干什么的?”女人反問。
“我是哈佛商學院教授。”男人非常自豪地自我介紹道。
“嗷,”女的說,“不就是個教書的嘛。”
這一晚上,男人再也沒跟女人說話,女人再也沒看男人一眼,女主人也悄悄跟我們發誓,再也不亂點鴛鴦譜,吃力不討好。
過了一個星期,女主人接到教授很沮喪的電話,他匯報道,冤家路窄,他居然和“世界名牌”同一個航班去上海,名牌經理當然是渾身名牌進了公務艙,而名牌大學教授卻灰溜溜地坐到后面的經濟艙。教授說,他太受刺激了,將來他養了女兒,一定不讓她念書,讓她賣包去。
從那以后我一直在考慮兩個問題,一是讀書是否有用,二是我到底算不算一個讀書人。我在大學里面是個不好不賴的學生,所有成績都是“良+”左右,劉索拉說她在音樂學院讀書的時候和我一樣,所以有個“良上君子”的美名。
工作以后非常忙,沒時間抱著書本瞎看,但是又特別怕別人看出來我不讀書,所以就養成了看書評的好習慣。比如《世界是平的》這本書出爐后,好多朋友是一頁頁、一個字一個字地看了,而我就看了一眼書評。在一個派對上,有人聊起這本書,我很隨意地說,世界要是平了,那共產主義就到來了。旁邊的人都覺得我的話很深奧,除了看過《世界是平的》還研究連《共產黨宣言》。我給大家留下了良好的讀書人的印象。而事實上,這是書評上看來的觀點,我就是巧妙發揮了一下。
我老覺得盲目讀書沒啥用,看完書倒背如流是知識消化不良的表現,就跟吃了一頓大餐以后抱著馬桶嘔吐一樣,那營養沒吸收進去。那一天到晚嘴邊掛著名人名言的大概都是有消化問題的人。
至于“賣包的”和教書匠的故事,最近聽說他們又邂逅一回,還是在飛機上,都在頭等艙。教書匠拿到終身職位,因此也開始穿戴國際名牌了,而“賣包的”去上了個EMBA,回來也升為品牌經理了,兩個人在飛機上聊得非常投機。
摘自《愛情婚姻家庭》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