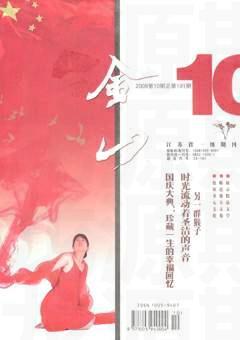愛者如斯
許 晨
近年來,中國傳統文化以一種驚人的速度呈復蘇之狀,越來越多的同胞開始理性對待純粹西方化的熱潮,重新關注起中國傳統佳節如端午、重陽。當然,效果最為明顯的當屬七夕中國“情人節”了。
七夕剛過,余熱尤在,大商場的鮮花巧克力還沒全部來得及下架,大小情侶多半還沉浸在幸福之中。七夕節的文化回歸,不僅是戀人幸福,商家也跟著狠狠地“幸福”了一把。
或許想問,傳統節日的特色體現在哪?能否想象,當年篇章里交待的“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的境界竟是位才子捧著一盒“德芙”在等佳人。是不是先民所謂的“死生契闊,與子成悅”可以被理解成“該死的溫柔”,是不是含蓄的“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可以改用Rab來唱。如果可以,這樣的回歸傳統我們期待作甚?也不過就是每年翻版一次二月十四罷了。
所謂東西心理本自同,至情的主題,都是人類的一種大愛的體現。西方在情人節比我們要冷靜得多,他們不是沉醉于花前月下,不是兩人世界的海誓山盟,而是向自己所有的親朋道上一聲“節日快樂”,沐浴于《圣經》的他們知道,愛,不是自私的。中國的七夕呢?古時便有“乞巧”一說,是向著蒼天默默祈禱句古老的耳語:“愿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這就是宗教家所謂的:“博愛。”
到底有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愛得不講目的,不問理由,不分親疏,不設范圍,不管形態,也不只是歇斯底里在某一天。哪怕是對自己的仇人。
托爾斯泰曾經在闡述西方哲學精神時所說:“如果愛有原因,那就不再是愛;如果愛有結果那也不是愛。愛是超乎因果的東西。”或許現在的年輕人認為他們對愛的理解已經獲得純西方的觀點,但是,卻沒有發現,即使是西方神學、哲學的源頭,也沒有同意這樣的觀點。也許在如今年輕人的眼中愛已經淪落為愛情的代名詞,這的確也是愛,可終究不圓融。
說到底精神結構無形無質,因為沒有社會的群體構建而顯得極易流散。而精神的構建又不應該淪為社會功利事業的附庸。只有在一座獨立的精神圣殿中,愛才能保證自己至善至美,生生不息的地位。所有人都有無庸置疑的愛的天賦,在社會上無論什么時候也都會有大愛的胸襟,有真愛的奉獻。如果沒有群體的精神構建,這一切都會是雜草中的孤芳,泥淖中的殘荷,不成氣候,盡管有人不停的感動。可是當無數的后輩陶醉在海誓山盟,兩情相悅中時,他們依然會唱到:“你是我生命的完完全全”,依然會很自信地認為自己已經追求到了真愛。
因為還有真愛,我們還能夠跋涉,在渾噩中也還有喜樂,因此,我們還只是人類。倘若身寄星云,愛及八荒,即使我們微若螻蟻,卻也圓融安詳,因為真愛的境界恰恰就是善和美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