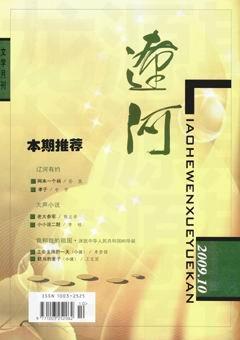舊屋或者塵埃(散文)
李天斌
一幢,二幢,三幢,四幢……它們像路旁的行道樹,更像光影里的塵埃,快速呈現又快速消失。幻滅——那些記憶的輪廓,當記憶呈現的時候,就已被記憶所吞噬。我無法確定誰是真正的參照物——我在這個秋天的黃昏孑孑獨行,我緩慢,我迅速,我在舊物的隧道里淚流滿面——逝去的時光,死去的親人……還有舊屋,對了,就是那些舊屋,正不斷進入我的眼簾……
雜草叢生。通向房屋的院子,早已在一片荒蕪里逃遁。大門緊閉,一把爬滿鐵銹的大鎖,孤獨地掛在門上——門內或者門外的通道,一如心的死寂!那些熱鬧的,生活的或者日子的,那些蹤影——一種被遺棄的孤獨,如我一樣,在秋天黃昏的風里兀自蒼茫。我匆匆走過——我是靜止的,我永遠在這個點上,而房屋在后退,直至隱去……這就是我最先看見的舊屋。
先前,我舅公就住在里面。而實際上,就在此前,我也一直認為他還住在里面——這讓我很是吃驚,我的確是很長時間沒有回村了。我竟然不知道他早已去世。一塊院子的雜草叢生,一個人的離去,對時間而言,輕微如塵埃。而我的不經意——一個自認為短暫的瞬間,竟然就上演了許多人事的枯朽!像時間的道具或者潛臺詞,讓我,不得不匆匆走過——我的目光不能在那里停留,在有關時間的概念上,我像落荒而逃的那縷秋風,扎進去,在黃昏的蒼茫里銷聲匿跡。
我再次想起了那把鎖。我不知道,當舅公已然離去之后,這把鎖意味著什么?歸來之后的開啟?……這明顯不可能。它終將隨著舊屋的倒塌湮沒為廢墟。它的鐵質的肉身,也無法逃脫時間的洗劫和掠奪。就像舅公,一個曾經熱烈地活著的生命,轉瞬間卻已化作蔓草輕煙,及至無跡可覓……而我終于發覺,我對那把鎖的回顧,其實就是對舅公的惦記和耿耿于懷。
我知道我繞不過去——舊屋或者塵埃,那些消失的生命,他們曾經的存在,一直牽扯著我。那些真實的抑或手制的幻象,像一條無法趟過的河,讓我不得不一次次念叨著一些重復和熟悉的詞語……
舅公其實并不是我奶奶的親弟弟。甚至不是奶奶近房的堂弟。他們雖然同族,但不知已經隔了幾世幾代。不過這并不影響他們之間的親情——血脈在這里已經是一種恍惚和遙遠的紐帶,同姓同輩分亦僅是一種理由和符號……實際的情形是,舅公和奶奶,情同手足,這讓奶奶安慰了一生,直至死后。在《失憶的憶》里,我曾經寫到過奶奶的家世。奶奶這一輩,只有三姊妹,沒有哥也沒有弟。像這樣的家庭,在重男輕女的年代,是被人瞧不起的。除了缺少勞力之外,斷代的香火——一縷血脈最終的消失,意味著此時的家庭已經名存實亡!而當我知道奶奶這些家世的時候,奶奶的那個家早已不復存在——她的父母早已亡過,兩個姐姐早也遠嫁他鄉并已兒孫滿堂,那個作為家的依憑的舊屋早已拆除——家的記憶淡如云煙,家的概念傷感如一張薄薄的紙——這是我從一張印有24孝圖的祖宗牌上窺見的秘密——不識字的奶奶總叫我幫她指認一個姓陳和一個姓蔣的名字,她說他們就是她的父母,因為她沒有哥或者弟,所以她必須要在每年的七月半供奉他們……舅公的出現,或多或少彌補了奶奶的一些缺憾。在那個年代,農村普遍有這樣的風俗,不論是紅白喜事,都需要有“外家客”前來撐點門面。“外家客”,除了是一種追求“圓滿”的風俗的需要之外,還暗含了顯示一個家庭背后“勢力”大小的意義。舅公并沒有讓奶奶失望。在奶奶給我父親、二叔、三叔以及小姑辦婚事的時候,他都約了很多的“外家客”,讓奶奶荒蕪的內心獲得了安慰。這種安慰直到她和爺爺先后去世之后仍在延續——當他們去世的時候,舅公仍然以“外家客”的身份,分別牽了兩只羊來祭奠……而我之所以要把這些詳盡的說出來,此時,除了對舅公的感激和內疚(我竟然沒有接到他的死訊)外,更有跟一幢舊屋的對峙——那些熱鬧的,凋零的,那些堅硬的,柔軟的,那些近的,遠的,沉重或者輕盈,此時,恍如前塵舊影……我亦像一個影子,自己手制的真實的幻象。
我站住——我固執地想要穿透一座房屋。而實際上,爺爺奶奶的舊屋早已拆除。僅剩一截墻壁的舊址,被我母親立起一棵棵瓜架,上面布滿了蘭瓜葉。而讓人覺得奇詭的,瓜架之下的雜草里竟然還綻開著零星的玫瑰,那些紅色的,白色的繽紛中透出荒涼。我并不滿意母親這樣的構思。舊屋的拆除,于母親而言,意味著一塊空地的誕生。我無意責怪母親。母親跟我不一樣,一座舊屋的消失,在母親眼里,并不處在生命的刻度之上——母親并不需要這樣的哲理,爺爺奶奶的離世,她對一塊空地的繼承并耕耘,如同日出日落和月圓月缺一樣天經地義。但此刻,當我站住,我不得不說,沿著母親構思的這些圖案,一座舊屋,一些舊事,開始復活——在黃昏的秋風里,讓我的骨骼隱隱作痛。
我不知道這是第幾次與它對峙——這是我近來比較喜歡的一個詞語。對峙,那種緊張但卻強勁的張力,或圓或方,或者并不規則,它的形式成了我面對時間的姿勢。去年,今年……我已經記不清我在這里站立的次數。但有一點不容置疑,那就是我每次回村,我都要在這里站立,靜默、甚至流淚——有人說我總是陰郁,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與生俱來的氣質,但我知道,當我在這里站立,我的陰郁,其實也是一種溫暖的凝視。
我總愛回憶起我的爺爺和奶奶。就在昨晚,我還在有關他們的夢境里回到從前——那些場景,仿佛蒙太奇,完美的組合,真切,仿佛如昨。
場景一:我放學回來,歸巢的鳥雀在門前的樹林里亂飛,翅膀劃過風,在夕陽的托舉里像一些鬼怪的影——這一定是我那時的想象,我進不了家門,父母不知還在哪塊地里勞作。而我總是害怕,在黃昏來臨的時候,我就開始害怕——那些不時燃起的磷火,那些關于鬼怪的傳說,往往以黃昏作為它們出現的起點。夜色已經開始彌漫,但父母還沒有回來——于是,我便只能跑到奶奶家去。奶奶正往灶坑里不斷添送柴禾,火紅的光焰把她的臉龐照得光亮無比。古銅色的皺紋——那些細碎的線條、歲月和風霜,在光亮的火焰里似花非花……而我分明看見的是奶奶躺在棺材里的最后的容顏——就要出殯了,做法事的先生說,這是你們跟亡者最后的告別。我伸出頭去,奶奶安靜地躺著,雙目緊閉,那些皺紋,像失血的花朵,枯萎,但卻出奇的安靜……
場景二:夜色彌漫……仿佛夢與夢的延續。很多時候,我都有這樣的感覺,我總在夜間不斷地醒來,不斷地做夢,盡管有中途的停頓,但前夢和后夢,似乎是一個完整故事的連接。這夜色也一樣,在逐漸彌漫的夜色里,我看見奶奶獨自在村口眺望——到鄉場賣旱煙的爺爺直到此時都沒有回來。山路崎嶇,是折斷了腿?還是被人搶了?——這死鬼,怎么不早點收攤?這死鬼啊,千萬不要出事……我看見奶奶在彌漫的夜色里來回走動,不斷祈禱,站立不安……我看見,在舊屋,在一堆柴火旁,奶奶幫助爺爺脫下被水打濕的鞋子,然后擺上熱氣騰騰的飯菜……
場景三……似乎還有場景三。但我已經記不起來。夜夢的雜亂,一如我心的雜亂——我不知道對爺爺奶奶的回憶,是不是總與一幢房屋有關。房屋——安身立命的處所,愛情和生命的出發地。從這里開始,爺爺奶奶孕育了父親、二叔、三叔以及小姑……還有我們這些孫子,將一幢房屋的精神不斷傳遞和延伸……而此刻,站在這廢墟之上,一幢舊屋的存在和消失,究竟給予了我怎樣的啟示?
我不知道。也無從知道。我開始走。我必須要穿過這秋天黃昏的風,回到父母現在居住的舊屋去。是夜,我躺在雕花的木床上,望著從窗里透進來的月光,我始終無法入睡。我不斷打量這幢房屋和這張雕花的木床。這是一幢曾經熱鬧的房屋,因為我們兄弟姊妹5個而顯得狹窄的房屋。但現在,卻因為我們兄弟姊妹的各散四方顯得寬敞并且空蕩,父母的雙腳,甚至無法走遍每一個房間……在夜色和蟋蟀聲的包圍里,竟然有人去樓空的荒涼……床,是屬于我和妻子的木床。我結婚的時候,父母按照風俗,給我打了這張床,一對戲水的鴛鴦和那雋永清秀的“喜”字,寄托著對我和妻子的祝福……但時至今日,我和妻子還沒在這上面睡過10次,甚至沒有在上面做過愛……它顯然也被遺棄了,宛如廢墟,舊屋或者塵埃,在本質上接近輕微——可有可無……
一代又一代的玫瑰
在時間深處相繼消失,我希望
逝去的事物中有一朵不被遺忘,
沒有標志或符號的一朵。
我緩慢。我快速。我無意中翻到博爾赫斯詩歌上卷257頁(《玫瑰與彌爾頓》),我看見月光從它身上滑過,我看見一個模糊的影——迅速向后推移,我是靜止的一個參照物,在原點朦朧如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