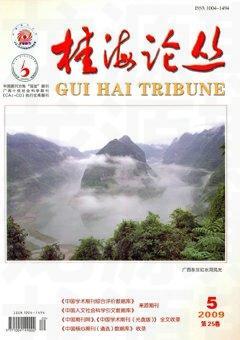建立法治型“泛珠”區域勞務合作機制的思考
韋 娌
摘要:區域勞務合作法律協調機制是法治型“泛珠”區域勞務合作機制的核心,因此,建立法治型“泛珠”區域勞務合作機制,對于鞏固合作成果,推動合作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這個法律體系既應具備國家制定的區域經濟合作的法律,又應具有地方立法協調法律機制、合作運行機制等。
關鍵詞:泛珠;區域勞務合作機制;行政協議;政策型;法治型
中圖分類號:D9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494(2009)05-0055-04
一、問題的提出
2004年7月14日,泛珠三角九省(區)勞動保障部門共同簽訂《泛珠三角九省區勞務合作協議》,并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勞工處及教育統籌局、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工暨就業局共同簽訂了《泛珠三角區域勞務合作聯席會議章程》,標志著泛珠三角區域勞務合作(以下簡稱“泛珠”區域勞務合作)全面啟動。作為全國最大的經濟合作區域,“泛珠”區域勞務合作涉及到全國近半數的跨省人員的就業問題。據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計,泛珠三角區域內的粵、湘、黔、川、閩、桂、云、贛、瓊等南方九省(區),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總數達6000多萬人,其中跨省流動就業超過3500萬人,接近全國跨省務工人數的一半,2006年創造的勞務收入超過2200億元。[1]勞務合作已經成為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合作旨在推動勞動就業政策和社會保險政策制度協調和銜接,搭建區域勞務合作交流平臺,加強跨省區就業服務體系建設,實行貧困地區勞務輸出幫扶制度,加強職業技能培訓和職業技能鑒定合作,加強區域勞動者權益保障制度建設,從而實現區域內勞動力市場的統一,促進勞動力資源充分開發利用和規范、有序、合理、高效配置的目標。
泛珠三角區域勞務合作自啟動以來,在合作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先后共同簽訂了《泛珠三角九省區勞務合作協議》、《泛珠三角區域勞務合作聯席會議章程》、《泛珠三角區域勞務合作計劃》、《泛珠三角區域九省區勞動力市場聯網合作議定書》、《泛珠三角區域維護跨省區務工人員合法權益聯動協議》等行政協議。通過建立實施協議的組織機構和機制、區域勞務合作聯席會議協商機制、維護跨省區務工人員合法權益合作機制,明確了共同合作的宗旨、原則、內容,約定了共同履行的職責、義務,建立了合作的基礎。經過四年的努力,使泛珠三角區域勞務合作趨于務實,流動就業的區域政策的協調性加強,就業環境逐步改善,勞務輸出組織化程度較合作前有明顯提高,從廣東省勞動部門獲悉,2009年農民工入粵整體有序,返崗率高,流失率低,低素質農民工數量有所減少。1至2月新增就業人數26.2萬人居全國前列。[2]此外,區域間人力資源配置優化初見成效,勞動者合法權益保障力度較大,帶動區域經濟互動發展效果十分明顯,充分展示出區域勞務合作的強大生機與活力。但是,泛珠區域勞務合作仍處于政策合作層面。以行政協議和行政磋商溝通機制為主要形式的政策型“泛珠”區域勞務合作機制具有靈活、易操作的優越性,但也存在主體協調能力有限、行政協議效力有限,以及行政磋商程序不規范的局限性。要使合作更具有長效性、制度性和有效性,特別是在當前金融危機形勢下如何推動合作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則更需要關注實現合作向法治型轉化的相關法律問題,使合作更具有穩定性、規范性和效力性。
二、政策型“泛珠”區域勞務合作機制的優勢與局限
當前,泛珠勞務合作仍面臨著城鄉平等就業、勞動衛生安全保障、休息休假、勞動和社會保障、子女教育、自治組織建設等諸多問題,但最為突出的還是缺乏法律協調機制的問題。目前“泛珠”區域勞務合作是以“泛珠”九省(區)及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合作推動,市場運作為特點的,其合作運行機制是采取以行政協議機制和行政磋商溝通機制為主要形式的政策型合作機制,這種合作機制有著其不可替代的優勢。就“泛珠”區域勞務合作機制而言,訂立行政協議的主體和實施主體都是合作省(區)各主管勞動和社會保障事務的行政主管部門,行政協議的訂立無需經過地方立法或政府批準,因此,具有靈活和易于操作的優越性。但也存在其自身難以逾越的局限性。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肖金成在回答《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提出的“為了協調區域內各方利益,是否有必要建立相對比較穩定的專門的協調機構?”問題時提出“要實現一體化,政府要利用一定的行政手段,但僅用行政手段是不夠的,”“區域經濟一體化不能依靠行政命令,強制執行。”一語道破了以行政手段為主要的政策型區域合作機制存在的局限性。
就行政協議機制而言,存在兩個方面的突出問題:
其一,是協議主體的局限性導致的對合作的實質性推進產生的影響。現階段,“泛珠”區域勞務合作協議的主體是“泛珠”九省(區)及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人力資源與勞動社會保障職能部門,無論是在哪種政治體制、法律制度或法域下,這種主體都不是立法體系中的主體,因此,此種協議便無法成為法律規范的基本形式,其實施和推進則只能以規范性文件,即政策的方式進行。這也就是目前合作各方出臺的規范性文件多,法律規范極少的原因。那么,當合作協議與合作各方的地方立法產生沖突,合作協議將如何得以實施和推進呢?在“泛珠”勞務合作中,既有社會制度不同的法域之間的法律沖突,也有同一社會制度的法域之間的沖突,且九省(區)之間,由于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地方立法權限存在差異,以及中央對地方的政策傾斜不同,造成地方立法存在很大的差異,因此,合作協議與地方立法的沖突難免會成為協議實施的瓶頸,容易使協議流于形式或因僭越立法權產生違法現象。
其二,是這種行政協議的效力問題,也使合作向深度、廣度發展受到限制。從行政協議的特點看,協議的主體是平等關系,任何一方都不具有行政權上的優越性,且協議也不具有可訴性,因此,協議對于各方是否具有效力,具有何種效力頗具爭議。學術界有的觀點認為這種協議不具有效力。因為,當有協議主體違約時,沒有任何法律機制保障協議的履行。因此,協議對違約者就失去約束的能力。但較為普遍的觀點認為,這種協議具有的是“軟性約束力”,“協議”作為一種合同形式,是簽約人的意思表示,對簽約各方具有約束力。所謂軟約束力,是指一旦出現違約,并沒有一種強制性的制約機制,而是基于各方相互信任而產生自我約束力,違約責任是基于成員間的內在依賴關系通過內部責任形式來解決。而現實的情況是,至今我國尚無法律對這種行政協議的約束效力問題,尤其是行政協議與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以及其他規范性文件的效力沖突問題作出相應的規定,從已簽訂的勞務行政協議看,協議條文本身也沒有涉及協議的效力問題。因此,行政協議效力的不確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協議作用的進一步發揮。
從磋商溝通機制看,由于締結和磋商程序不規范導致協議內容過于原則也影響了“協議”的質量。目前,合作各方磋商締結各種勞務行政協議最主要的平臺是由泛珠三角區域九個內地省(區)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勞工處及教育統籌局、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工暨就業局(簡稱“9+2”勞動保障部門)組成的泛珠三角區域勞務合作聯席會議。聯席會議原則上每年舉行一次,由各成員單位“共同主辦,輪流承辦”,在會議上一般包括有各合作主體作主旨發言、提出議題、締約等程序。但目前會議主要采用論壇形式,在較短的會期時間內要完成上述內容,造成協議各方很難有充分的時間進行實質性的磋商溝通和利益平衡,也很難有充分的時間對協議條款進行考究和細化,所以,協議的內容都比較原則。此外,一些起著重要的規范性作用的內容和條款普遍缺失,比如,責任條款、效力條款、爭端解決條款等都沒有涉及,也造成協議可操作性不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