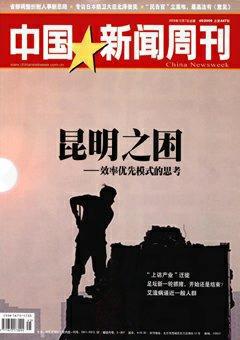地方政府決策方式謀變
韓 永


“地方政府還是原來的政府,民眾已經不是原來的民眾了”
2009年11月末的昆明,螺獅灣事件余音未了,“防盜籠”事件又在暗流涌動。
從2009年11月24日開始,昆明市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的負責人相繼接到一個指令:從即日起,這些單位的職工要自覺拆除自家的防盜籠,以為城市騰出更多的公共空間,也為其他市民做出表率。
指令的語氣,沿用了近兩年一貫的雷厲風行:不僅將拆除的期限嚴格限定在年底之前,而且規定“必須百分之百拆除”,“如不執行將嚴厲問責。”
11月2日,在一次“拆臨拆違現場推進會”上,中共昆明市委書記仇和下達了這樣的指令。他說,防盜籠擠占公共空間的現象十分突出,希望有關部門進行整治,“必要時可走立法途徑。”
坊間一時議論聲起。在昆明信息港彩龍論壇上,有網民質問這一決策的邏輯:在安全問題尚待解決的情況下,把防盜籠拆掉,豈不是給了小偷一個綠色通道?這一牽涉面甚廣的決策,為何再一次忽略了民意的表達?
事實上,在昆明的近兩年里,“大動作”頻出的同時,一直伴隨著這樣的質疑。一位社會學者指出,這種質疑一旦與受損的利益相結合,就會演化為與政府對抗的行為。“這不僅是仇和主政下昆明的困境,也是轉型期中國的困境。”
決策遇阻
從仇和2007年12月上任昆明市委書記以來,該市有據可查的民眾與政府對抗的行為,除了這次的螺獅灣事件外,還有3起。
這3起事件都與去年市政府對小區道路“私改公”有關。小區道路“私該公”,是昆明市政府為解決市區擁堵出臺的一項政策。其思路是通過將小區道路公有化,分擔城市主干道的承載壓力,從而緩解交通擁堵,是謂“交通微循環”。
仇和對這一舉措寄望甚大,不僅將目標細化,還屢屢上陣督查。2008年2月份,《昆明主城區內單位及小區道路轉為城市公用道路方案》出臺,建議將39條單位及小區道路轉為城市公用道路。
這一決策的背后,是昆明的交通現狀與仇和要將該市建設成面向東南亞的國際大都市目標之間的差距。仇和對交通在城市發展中的地位,曾有一個非常著名的論述:“沒有大交通就沒有大物流,沒有大物流就沒有大流通,沒有大流通就沒有大商務,沒有大商務就沒有大市場,沒有大市場就不可能帶動昆明的都市經濟發展。”
而昆明的交通面臨的現狀,仇和也曾經用一組數字作比。他曾說:“大家知道,100萬人口的城市需要10個出入口,200萬人口的城市需要20個出入口,300萬人口的城市需要30個出入口,500萬人口的城市需要50個出入口,而擁有600多萬人口的昆明,卻只有17個出入口。”
40多個出入口的差距,讓仇和對交通工程的進度尤為強調。他建議這些工程可以超時序、超程序、超常規,實行工作時間倒逼,以開工倒逼時序、倒逼程序、倒逼手續。云南省一位規劃官員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特別提到了對不按規劃建設的擔憂。
3起事件發生地之一的盤龍區北辰小區業主對這一倡議并不買賬。去年3月中旬,這一小區的業主在小區門口發現了一個公告,稱欲在該小區門口建立交橋以備昆曲高速落地,同時將小區內的部分道路“由私改公”。此后,他們就以法律和規劃的常識為武器,拒絕小區道路“私改公”。
該小區一位楊姓業主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他們主要有兩個“抓手”:一個是《物權法》,一個是規劃的合理性論證。《物權法》第73條規定:“建筑區劃內的道路,屬于業主共有。”而如果政府要征收,北京大學憲法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給出了三個前提條件:一、必須是公共利益的需要,即昆明市政府對“私改公”的初衷是否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考慮;二、要符合比例原則,即“私改公”是緩解城市道路堵塞的最佳方案,并且這一方案對相對人的利益損害最小;三、政府應根據憲法第13條、物權法地121條和42條,給予當事人合理的補償。
北辰小區的業主們認為,比照上述三條,政府的做法每一條都有可商榷之處,但尤以第二條證據充分。當年3月7日,《春城晚報》曾經披露市規劃局提出的《三環路與昆曲路聯系通道方案》,方案有4種,前三種實施的條件都好于北辰立交,但“實施尚需時日”,而北辰立交“空間位置不太理想,實施的空間也不理想,但實施相對容易”。《方案》舍其他三種條件更優的方案不予推薦,只作為遠期實施方案,卻選擇條件最為不宜的北辰立交方案,在業主們看來是急功近利之舉,“其以后重復建設的投資,誰來埋單?”
讓業主們尤為不能接受的是,這一牽涉小區內萬人以上利益的決策,事先沒有經過任何聽證。直到看到小區外面的一紙公告,他們才知道自己的道路“被公有化”了。
對于民主,仇和曾經有過這樣的表述。他說:“我搞科研出身,科研重結果,不重過程,所以有時表現出急躁的情緒。”“西方在我國現在這個發展階段時,在我國這種GDP時,哪里有人權呢?”
但是,“政府還是原來的政府,民眾已經不是以前的民眾了。”北辰小區業主決定堅持到底,決不就范。
民間力量的成長
北辰小區上文提到的楊先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與政府交涉的過程中,他發現小區的很多業主都非常熟悉《物權法》,有的對與規劃相關的法律也非常熟悉。他說,在整個過程中,有兩個人起到了核心作用:一位是云南財貿學院老師單瑜,另一位是退休的高級工程師熊鍔。“他們一個負責法律上的事,一個負責規劃上的事,這使得業主在與政府的交涉中時時處于領先。”
除此之外,小區內還有懂網絡的人建起了維權網站,有商人組織捐款,老人則挨家挨戶地發送傳單。還有人專門在網上動員,“唇亡齒寒”的鼓動,一時響徹各個論壇。
楊先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北辰小區屬于昆明的高檔小區,業主多是文化水平較高的人。在北辰小區之前同樣因小區道路與政府起爭執的創意英國小區和陽光花園,業主的構成也與北辰小區大同小異。
長期關注群體性事件的民間人士王國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樣的小區具備了兩個與政府博弈的要素:一個是業主的法制觀念很強,另一個是他們的物質基礎不錯。“前者讓他能言之成理,后者則讓他不易被收買。”
業主代表共與盤龍區政府建設局在2008年4月進行了兩輪談判。第一輪,由于業主事先通知了一些媒體,官員退避三舍,拒絕出面。第二輪,業主在談判中占有壓倒性優勢,逼著建設局有關負責人不得不做出“方案確實有缺陷”的表態。建設局一位負責人見狀不妙,武斷地終止了會談,聚集在周圍的業主情緒激動,于是在2008年4月22日發生了堵路事件。
至此,這一事件開始脫離理性的軌道,逐漸演變為群體性事件。激動的人群堵斷了北京路和北辰大道交匯口4個路口,致使昆明北市區交通癱瘓了近4個鐘頭。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錫鋅說,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多發生在理性的渠道用盡之時。
創意英國小區和陽光花園也都對“私改公”反應激烈,但最終沒有做出過激的舉動。創意英國小區的業主們多次集會,并選出臨時業主代表,與昆明市、五華區建設部門進行了幾次“對話”。最終,在媒體公布的昆明市第三期微循環改造的102條道路名單上,去掉了創意英國小區的名字。
陽光花園則發生了業主被打事件。2008年4月6日,在沒有任何通知的情況下,業主們突然發現施工方的設備開始運轉,于是上前阻止,雙方發生沖突。沖突中,三位業主受傷。
王國國說,北辰小區事件的前后兩段,分別展示的是兩種力量:前一段展示的是理性的力量,這個期間法律意識和專業知識發揮著主導作用。在理性的力量遭遇政府的不作為后,這一群體開始展示“革命性”的力量。“其中的邏輯是,既然你不跟我講理,我何必跟你講理!”
“私改公”最終沒有在北辰小區實行。與螺獅灣拆遷風波中的參與者一樣,他們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有6位參與者因此被盤龍區人民法院以擾亂社會秩序判定有罪。這顯然對他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記者此次聯系他們時,已經沒有人愿意再提此事。
開放性決策破局
這種由決策造成的“雙輸”的結局,正在執政者中間引發深思,有些地方已經開始著手改變原有的決策方式。
廣州市法制辦主任吳明場,曾在此前寄望于通過“為民決策”,即站在被執行者的角度來決策,以期達到良好的執行效果。但發現效果不彰,“老百姓根本不買賬。”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有時候你明明是為他好,比如舊城改造,改善了居住環境,美化了城市,可是為什么被拆遷的人不覺得是好事呢?這值得我們反思。”
成都城鄉一體化推行初期,也曾遇到類似的難題。邛崍市油榨鄉黨委書記王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很多村民一聽說土地要確權,就下意識地懷疑政府是不是要收回土地。
吳明場兩年前開始反思這件事,最終發現問題還在于沒有真正地吸納民意。“我們以為決策代表了民意,實際上可能并不是。”昆明市下屬某縣縣委書記付天承認,有時候官員的想法與民眾相差很大。“拋開官員的政績沖動不說,政府想的多是全局的事情,而老百姓更多只想著具體的事情,”付天說:“為了全局利益,有時候需要部分民眾做一些犧牲,但由于官民之間長期以來缺乏有效的溝通,老百姓并不理解官員的想法,有時還會下意識地懷疑官員的動機。”
吳明場說,這時候的決策,就不應該由官員越俎代庖,代民眾說話。“比如拆遷,誰都知道這會美化環境,但你無權讓我以犧牲自我作為代價。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有選擇權。”他說,政府現在面臨的一個任務,是要改變自己的決策程序,解決“由誰來決策的問題。”
吳明場說,解決了這個問題,另外兩個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一是矛盾在決策之前就能得到解決;二是人大的通過就會順利得多。“大多數老百姓都認了,人大也不好再說啥了。”
他說,從今年開始,廣州市政府開始制定一些程序性的規定,以便更好地吸納民意。
杭州市政府的嘗試要更早一些。從2007年開始,杭州市政府開始嘗試在政府常務會和市長辦公會上邀請一定比例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市民代表參加,對一些與民眾關系密切的法律性文件進行決策,已初見成效。
此外,北京、長沙也都有過類似的嘗試。
但吳明場同時表示,并非所有的議題都適合公眾決策,“比如垃圾站,放到哪里都不要,那怎么辦,肯定也不能公眾說了算。”
浙江大學政府績效考核研究中心主任胡稅根給出了一個建議。他說,那些涉及到公眾利益的項目,可以提交人大表決。
這一注重吸收民意的決策方式,在昆明仍尚待起步。付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所管轄的縣在決策過程中民眾的參與,現在只散見于一些法律法規在表決前的公示,還沒有擴展到決策過程。“聽證有時候也就是走走程序,”云南省政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廳級官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