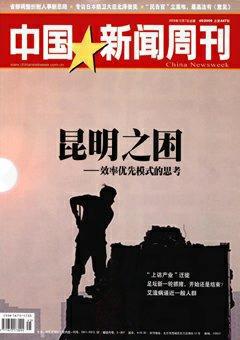村官眼中的拆遷博弈
陳曉舒

在村官眼里,城中村拆遷前要解決的問題,有開發商的合作分配,還有村民的利益分配。
2007年動遷的獵德村已經成為城中村的改造樣本,村內切出一塊地拍賣給開發商,獲得資金用于改造。
2009年10月20日,與天河區的獵德村隔江相望的海珠區琶洲村也將4塊地賣給了開發商。此前的6月1日,白云區同和村與富力地產也簽訂合作改造協議。
引入開發商的模式看似是多贏的方式,但是也有其隱憂。這個模式使得原本已經擁擠不堪的城中村,為了滿足開發商的利益,只能不斷提高容積率,才能將改造持續下去。(是指一個建設項目內,地上總建筑面積與總用地面積的比值。容積率直接涉及居住舒適度,容積率越低舒適度越高。一般認為,良好的居住小區,高層住宅容積率應不超過5,多層住宅應不超過2。)
“與其讓開發商來做,為何不能讓我們自已開發?”廣州市白云區三元里實業有限公司(原村委會改制)經理李國強說。
在村官眼里,城中村拆遷前要解決的問題,有開發商的合作分配,還有村民的利益分配。
再造“水泥森林”?
三元里經理李國強說:“長期以來,政府出于擔心開發商介入會進一步加大市中心居住密度等原因,而拒絕引入開發商改造城中村。”
2004年,廣州城中村改造堅持“不以房地產開發”為原則,以村集體和村民個人出資為主,政府將對公共設施、基礎設施配套建設給予適當的支持。
直到今年8月份,由富力地產、合景泰富地產與新鴻基地產合力打造的廣州珠江新城CBD項目在獵德村正式動工,自此真正揭開了廣州引入開發商進行城中村改造的序幕,也成為廣州其他城中村改造的可借鑒對象。
但獵德模式并不被李國強看好。“最大的原因就是經過改造后的獵德村,容積率會非常高。開發商介入最大的缺點是他們要得到回報,單就合理的回報來看,他們所能做的只有提高容積率。”李國強說。
李國強算了一筆賬:目前,廣州的城中村,容積率普遍在3-3.5之間,如果要保持地產商們的利潤空間,容積率恐怕至少得翻一倍。而白云區政府之前給三元里村改造后的容積率訂為6.7,“我們提出不要超過5。現在訂的是4.8。”在冼村的改造方案中,冼村改造地塊毛容積率最低約為7.1。方案中提到,如將冼村改造毛容積率確定為7.1,拍賣地塊容積率確定為8,則沒有任何空間對村民可能提出的補償標準提高要求做出調整。
而廣州市楊箕村改造村民要求住宅臨遷費用已達到30元/平方米每月,并仍有升高趨勢。楊箕經濟發展有限公司(楊箕村委會改制)董事長張建好稱,借鑒獵德村改造經驗,準備“賣地籌錢”,但是“核心問題還是容積率的問題”。
“如何在這11萬多平方米的土地上,切出一塊拍賣,剩下的還可以‘一補一,這個經濟平衡很難。”張建好坦言。
也就在2008年末,廣州市建委負責人提出,城中村改造切忌急功近利。經過改造后的城中村要讓村民真的“住進了城里”。不能為了多蓋房子,就盲目索取過高容積率,變成新一代的“水泥森林”。
村官:賣地還是賣樓?
“我們最害怕的還有爛尾樓。”除了經濟上難以平衡,張建好還對開發商上門合作的方式有些搖擺。她認為最好的辦法是政府主導征地開發,而不是開發商來買地。“還是政府一手包辦好”。
“與其讓我們賣地,不如讓我們賣樓。”廣州白云區三元里村經理李國強則表示。三元里所在的白云區相對獵德、冼村、楊箕所在的天河區、越秀區來說,土地價值較弱。“如果切出一塊土地進行拍賣,所得資金滿足不了拆遷補償要求。”
白云區目前參照的是上海模式。由政府主導,提供三個補償方案:1、原地復建,回遷后拆一還一;2、現金補償;3、區域平衡,在遠一些地方建小區,然后再補償差價。
李國強考慮的是如何讓土地利益最大化。他的設想是,將三元里需要改造的地塊按照商業形式改造,建商場,酒店和寫字樓。而村民們的住宅可以在本村的備用地范圍內,進行區域平衡的方式補償。
按照李國強的方式來做,廣州市政府得給城中村集體經濟組織開發權,讓他們自己進行商業化改造。這樣才能保證城中村改造的資金,也能使集體經濟的利益不受損失。“這不僅僅是怕今后出現改造爛尾樓的問題。”李國強認為。
李國強說,就算村公司自己不做,政府也可以開發賣樓。這樣的方式都可以讓他們住的舒服一些。他稱獵德村改造后房子太密,“那樣的房子有什么好住的”。
而廣州“城中村”每個改造項目拿到土地市場上都將是一個巨無霸項目。琶洲村改造面積達185萬平方米,總投資額達100億元?獵德村改造僅復建房建筑面積高達93萬平方米,項目面積近57萬平方米,只有少數有實力的開發商才能參與其中。
前廣州市規劃局局長潘安曾表示,政府在城中村改造過程中主要是組織、引導的作用。如今政府牽頭引入開發商還存在法律上的障礙,因為城中村改造的主體是村民,原則上應是村民說了算,政府主要是組織、引導作用。
村民:分紅不分紅?
2009年8月以來,在冼村和楊箕村的實業公司門口,村民們以靜坐的方式抵抗城中村的拆遷。“和他們解釋過很多次了,拆遷完公司還會在,分紅也不會取消。”張建好稱,村民們抵觸還是擔心分紅會隨著城中村的消失而消失。
這個局面也是城中村改制改造多年來遺留下的病根。
李國強稱,廣州的城中村從上世紀末開始改制改造,目的是為打破城鄉二元制結構,讓城中村真正融入到城市管理中。
經過改制的城中村,原村領導班子多數都轉成集體經濟組織的領導。書記變為董事長,村委主任變為經理。另外,街道辦則另外派人成立居委會,負責城中村的行政事務。
雖然一些規模大一些的行政村,如石牌、冼村等被分為幾個居委會,但是真正管理村內事務的還是有原村委會轉變的公司來負責。
既然早已身處城市的中心,但城中村依然是廣州市城市管理的邊緣地帶。“村外的馬路歸市政負責,到了村里,換一個燈泡都要村集體拿錢。”李國強說。城中村內的治安、衛生等事務也全部由這個集體公司負責。
這讓“村委會”感到力不從心。楊箕經濟發展有限公司張建好抱怨:“我們幾個村干部一人要管理這么多物業,拿的工資也是區政府規定的,還天天被村民懷疑我們貪了很多錢。”
這也成為村干部和村民間最大的矛盾。“他們成天不干活,在村里打牌賭錢,就等著分紅,分不夠還罵我們。”張建好稱。
現在剛開始的動員階段,已經讓張建好和楊箕村居委會的工作人員磨破嘴皮。“挨家挨戶地調查,找村民征求意見,看同不同意改造。如果同意,那么我們形成方案,進行招拍掛。”張建好說。
一年以來,楊箕村和冼村這兩個毗鄰廣州市CBD核心區域的城中村仍在商討方案。據兩村村干部稱,方案已討論不下五次。“亞運會前拆完,還要看能否找到一個合適的改造方案。”冼村實業公司副董事長盧佑醒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