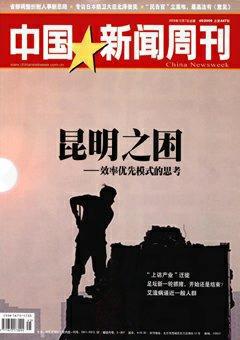經(jīng)濟(jì)形勢(shì)挑戰(zhàn)治國(guó)智慧
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已經(jīng)患上嚴(yán)重的投資依賴癥的情況下,如果大力調(diào)整結(jié)構(gòu),很可能導(dǎo)致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減速,如果放任這種結(jié)構(gòu),政策繼續(xù)集中于保增長(zhǎng),則結(jié)構(gòu)的惡化同樣會(huì)導(dǎo)致相當(dāng)嚴(yán)重的經(jīng)濟(jì)乃至社會(huì)政治后果。
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27日召開(kāi)會(huì)議,分析研究明年經(jīng)濟(jì)工作,為即將召開(kāi)的中央經(jīng)濟(jì)工作會(huì)議定了調(diào)子。按照慣例,中央經(jīng)濟(jì)工作會(huì)議都是在12月份召開(kāi)。當(dāng)前的經(jīng)濟(jì)形勢(shì)處于一個(gè)極為微妙的時(shí)機(jī),如何進(jìn)行抉擇,考驗(yàn)著決策者的治國(guó)智慧。
從2008年底開(kāi)始,面對(duì)經(jīng)濟(jì)衰退的趨勢(shì),“保增長(zhǎng)”成為中國(guó)政府的首要任務(wù)。政府也全面采取了各種財(cái)政、貨幣甚至政治措施。至少?gòu)暮暧^層面來(lái)看,效果還不錯(cuò),“保八”已經(jīng)不成問(wèn)題。
然而近來(lái),經(jīng)濟(jì)學(xué)界和市場(chǎng)剛剛形成的樂(lè)觀心理又蒙上陰影。綜合起來(lái),目前決策者面臨兩個(gè)兩難困境。
首先,從國(guó)內(nèi)看,各界對(duì)通貨膨脹的擔(dān)心越來(lái)強(qiáng)烈。實(shí)際上。按照另外一種經(jīng)濟(jì)學(xué)理論,大規(guī)模擴(kuò)張性貨幣政策本身就意味著通貨膨脹的開(kāi)始,并且,從年初開(kāi)始,這種通貨膨脹就已經(jīng)在股市、房市等資產(chǎn)性市場(chǎng)清晰地表現(xiàn)出來(lái),各地房屋價(jià)格的瘋狂上漲就是通貨膨脹的表現(xiàn)。隨后,價(jià)格上漲蔓延到水、電、氣等公用事業(yè)領(lǐng)域,也蔓延到食品、農(nóng)產(chǎn)品等領(lǐng)域。接下來(lái)會(huì)不會(huì)蔓延到其他領(lǐng)域?
從國(guó)外看,迪拜債務(wù)危機(jī)爆發(fā),引起全球?qū)τ诘诙谓鹑趧?dòng)蕩和經(jīng)濟(jì)衰退的擔(dān)心。盡管中國(guó)金融監(jiān)管層和相關(guān)機(jī)構(gòu)再三澄清,這場(chǎng)危機(jī)對(duì)其沒(méi)有直接影響,但無(wú)人能夠排除間接影響。事實(shí)上,這種間接影響可能很大,假如它確實(shí)引爆全球、哪怕只是美國(guó)的第二次金融動(dòng)蕩和經(jīng)濟(jì)衰退。因?yàn)椋衲暌詠?lái),中國(guó)的出口一直處于低迷狀態(tài),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主要靠投資拉動(dòng),如果出口再度萎縮,則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壓力就會(huì)陡然加大。
這兩個(gè)動(dòng)向,對(duì)決策層施加的是完全相反的壓力:后者要求政府繼續(xù)維持寬松的經(jīng)濟(jì)政策,但這就意味著,價(jià)格上漲將會(huì)蔓延到更多領(lǐng)域,從而導(dǎo)致大面積通貨膨脹。而如果為應(yīng)對(duì)通貨膨脹壓力,過(guò)早地收緊貨幣政策,則經(jīng)濟(jì)有可能第二次探底,全球可能出現(xiàn)的第二次衰退將使問(wèn)題更為嚴(yán)重。
第二個(gè)兩難困境指總量增長(zhǎng)與結(jié)構(gòu)惡化的同時(shí)存在。中國(guó)經(jīng)濟(jì)之所以陷入本次衰退,與外部的結(jié)構(gòu)失衡有關(guān)系,但主要還是內(nèi)部的結(jié)構(gòu)失衡所致。這就是人們廣泛談?wù)摰耐顿Y、出口與消費(fèi)的失衡,而導(dǎo)致這種失衡的根源則是在經(jīng)濟(jì)過(guò)程中,不同人群參與經(jīng)濟(jì)剩余分配的權(quán)利也就不平等。在這種制度環(huán)境下,經(jīng)濟(jì)的高速增長(zhǎng)反而急劇地?cái)U(kuò)大了收入差距:首先是各級(jí)政府的收入增長(zhǎng)大大超過(guò)民間;其次,民間財(cái)富急劇地向高收入群體傾斜,中低收入群體的相對(duì)消費(fèi)能力日趨低下。而這樣的收入結(jié)構(gòu)是無(wú)法支撐消費(fèi)型增長(zhǎng)的,經(jīng)濟(jì)只能依賴出口和面向出口與基礎(chǔ)設(shè)施的投資來(lái)維系搞增長(zhǎng)。
2008年底后,政府為應(yīng)對(duì)經(jīng)濟(jì)衰退出臺(tái)種種保增長(zhǎng)政策,反而讓這種失衡的結(jié)構(gòu)更為突出。從2008年11月份確定4萬(wàn)億救市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以來(lái),金融機(jī)構(gòu)開(kāi)始投放數(shù)量驚人的貨幣和信貸,其中大部分都流入地方政府和國(guó)有企業(yè)之手。由此而出現(xiàn)了大規(guī)模的國(guó)進(jìn)民退現(xiàn)象,由此也出現(xiàn)了投資增長(zhǎng)一枝獨(dú)秀的現(xiàn)象,投資相對(duì)于消費(fèi)的比例達(dá)到創(chuàng)紀(jì)錄水平。當(dāng)然,在此過(guò)程中,社會(huì)不同群體的收入分布不均狀況也就更加惡化了。
增長(zhǎng)目標(biāo)與結(jié)構(gòu)惡化之間也是一個(gè)兩難。在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已經(jīng)患上嚴(yán)重的投資依賴癥的情況下,如果大力調(diào)整結(jié)構(gòu),很可能導(dǎo)致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減速,尤其是在目前宏觀經(jīng)濟(jì)本身比較脆弱的時(shí)候。但如果放任這種結(jié)構(gòu),政策繼續(xù)集中于保增長(zhǎng),則結(jié)構(gòu)的惡化同樣會(huì)導(dǎo)致相當(dāng)嚴(yán)重的經(jīng)濟(jì)乃至社會(huì)政治后果。
面對(duì)這兩個(gè)兩難困境,決策者其實(shí)已經(jīng)有了基本應(yīng)對(duì)策略。在此之前,中共中央11月24日在中南海召開(kāi)黨外人士座談會(huì),就當(dāng)前經(jīng)濟(jì)形勢(shì)和明年經(jīng)濟(jì)工作聽(tīng)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guó)工商聯(lián)領(lǐng)導(dǎo)人和無(wú)黨派人士意見(jiàn)和建議。而11月27日的政治局會(huì)議宣布,要保持宏觀經(jīng)濟(jì)政策的連續(xù)性和穩(wěn)定性,繼續(xù)實(shí)施積極的財(cái)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不過(guò),會(huì)議也提出,要增強(qiáng)政策的靈活性和可持續(xù)性,要更加注重提高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質(zhì)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方式轉(zhuǎn)變和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更加注重推進(jìn)改革開(kāi)放和自主創(chuàng)新、增強(qiáng)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活力和動(dòng)力,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保持社會(huì)和諧穩(wěn)定。對(duì)于投資,會(huì)議確定的方針是保持投資合理增長(zhǎng),完善和落實(shí)鼓勵(lì)民間投資相關(guān)政策。
應(yīng)當(dāng)說(shuō),這套政策組合還是比較均衡的,但可以預(yù)料,在慣性作用下,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不大可能有實(shí)質(zhì)性動(dòng)作,各部門、各地方政府出臺(tái)的政策仍將會(huì)在保增長(zhǎng)上大做文章。這是禍?zhǔn)歉#瑹o(wú)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