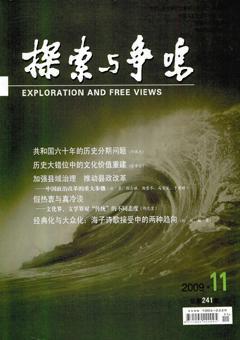中國古代缺乏以社會自治為前提的縣域治理
程念祺
中國古代,在國家實行官僚化統治之前,統治者各有其民。其時,人民是“自治”的;而“自治”的基本單位,是村社共同體。然而,履畝而稅實行之后,村社共同體組織生產和分配土地的職能喪失,“自治”的能力隨之削弱,并逐漸消亡。這就給國家的官僚化統治帶來許多問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縣域治理問題。2000多年之中,中國最小的行政區域都是縣;縣以下,諸如鄉里保甲之類,不過是應政府之命,為方便政府征發賦役和維持地方治安而建立的一種人口編制,而不是人民的自治組織。人民沒有自治組織,社會的許多事業必然荒廢。原來,在村社共同體內部,生活和勞動雖然以家庭為基本單位,但諸如份地定期分配、公田耕作、溝洫疏浚、公積勞動和貿易,以及社會互助等各項事業,皆由共同體所主持。可以認為,在這種村社共同體內部,仍保持某種“大同”的性質。這是適合當時農業社會生產力水平要求的。而當這種“大同”的性質喪失,村社就只剩下原來共同體的軀殼,不再具有上述自治的功能;“和協輯睦”和“敦庬純固”也沒有了。村社不能自治,則縣域治理就只能是一句空話。
以漢代為例。漢代縣以下設里、亭、鄉。里設里魁,“民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亭設亭長,“以禁盜賊”。鄉設嗇夫,“知民善惡,為役先后,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設三老,“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設游徼,“禁司奸盜”。由此可見,當時在地方上,人民被控制在一個“賦役—教化—治安”的系統內,是純粹的“治于人”者,而非“自治”者。在這種情況下,所謂“教化”,其實不過是聾子的耳朵——擺設。漢代地方上還有一種豪強,始終與國家爭奪對人民的控制權。對豪強的打擊,是漢代國家的一項既定國策。但是,舊的豪強被消滅了,新的豪強又產生了。豪強是地方勢力,卻與政治特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憑借著政治經濟特權,使大量人民依附于他們,如同牛馬。漢武帝時,董仲舒指桑罵槐,說漢朝像秦朝一樣,在國家和豪強壓榨之下,“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后來漢哀帝也承認,貴族、官吏和豪強“多畜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足”。至于篡政的王莽則指責漢朝:“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奸。”凡此,都足以表明,社會的基層如果不能自治,就不可能有所謂縣域治理,那么民政的敗壞是必然的。漢代也有一些地方官,在治理地方的過程中,親自對百姓“教以禮讓”,“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但是,人民既然無“自治”的環境,那么這種“教化”就沒有生活的基礎,因而決不會有實際的效果。
西漢地方為郡縣兩級。郡的權力很大,一郡轄數縣,或十幾個縣;郡的屬官和所屬各縣的縣令(長)及其屬官,皆由郡守任命。漢武帝時,一個叫嚴安的人上書說:“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意思是要削弱郡太守的權力。但是,漢武帝沒有采納嚴安的建議。后來,郡太守違法亂紀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漢武帝始設州刺史監察郡太守的行為。刺史之設,權力漸增,而不僅僅為監察;至東漢,州更演變為更高一級的地方行政機構,地方行政遂由二級統治轉變為三級統治。三國時夏侯玄認為,地方行政無論是二級還是三級統治,對于縣治都是不利的。他建議,不如“省郡守,但任刺史”,“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于此矣”。即地方行政只設縣一級,使中央的政令可以直達,而以刺史監察縣治。顯然,夏侯玄所考慮的,是加強縣一級行政的權力,以利中央對地方行政的控制;但仍沒有涉及怎樣通過發展地方自治,以促進地方事業的發展。
就總體傾向而言,秦漢以后,中國的地方行政,無非是疊床架屋;而宋元明清四代,更是將地方的行政權一分再分,目的無非是加強中央對地方行政的控制,并且不惜以犧牲地方的辦事能力為代價。在這種情況之下,國家之所謂民政,主要就是收稅。錢穆就批評宋朝“地方政事的性質,似乎只在為中央聚斂”;“既已盡取之于民,不使社會有藏富,又盡輸之于中央,不使地方有留財”。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時縣一級的所謂治理,唯一的目的就是完成朝廷的賦稅征收,而地方的事業則是一切廢置。
學者往往認為,中國自古是皇權不下縣,基層社會由鄉紳和宗族自治。皇權下不下縣,不可一概而論。對這樣的議論,近來已有學者予以批評。蓋人民之被編制在一個“賦役—教化—治安”的系統內,怎么可以說是皇權不下鄉呢?但是另一方面,當人民僅僅被編制于“賦役—教化—治安”的系統之內,實際上已被剝奪了自治權力,又如何自治呢?所謂鄉紳,或在鄉里有某些義舉,但總體而言,是一股兼并勢力,不是兼并土地和隱占人口,就是向小農轉嫁賦稅,又如何率民自治?宋朝的范仲淹想利用宗族的力量來實現人民的自治,首先想到的就是在宗族內部設立“義莊”,為宗族內部的救貧恤孤、教育和公積事業,建立一個實現的基礎。他制定了《義莊規矩》,希望各地宗族都能仿置。但是,他的義莊“置上田十頃于里中”,可見,也是以兼并為前提的。但根本的問題在于,宗族并非是社會自治的溫床。明初的方孝孺,也是希望在鄉里和宗族中實行社會自治。但方孝孺認為,“法弛教失”之下,雖“至親之愛皆化而為途人”。意思是說,人民生活的物質基礎、制度保障,以及與之相關的教化,都已不存在了,宗族的親親之義也就不可能保持下去。所以,他提出的自治方法,按蕭公權先生的概括,就是在鄉族之中,“運道德之力量以正風俗,藉互助之組織以救饑寒”。這種方法的特點,就是在一鄉一族之中建立自治組織,使人人參與,而不是靠一二精英之贊助。
按呂思勉先生所說,宋明時代的一些封疆大吏、地方長官和紳士,的確已認識到“治化的良否,不盡系于政治,而亦由于社會”。這樣的認識,使他們或用心于地方社會的自治方面。然而,在當時的那種政治體制下,國家設官治政的目的,即如黃宗羲所說:“君分吾以天下而后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后牧之,視天下人民為人君囊中私物。”而認為人民并無自治的能力,則是另一種更為深刻的偏見。毫無疑問,這樣的目的和偏見,使中國基層社會的自治,受到了最大限度的抑制。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歷史上的縣政,總顯得無所作為。黃仁宇先生認為,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一個巨大的平面,而官僚的統治垂直于這個平面之上,兩者之間缺乏一個中間結構,所以國家和社會之間很難溝通。實際上,他所說的社會之為平面,亦即社會沒有自治組織,故政治難以對社會產生作用。
中國歷史上,就中央對地方的控制而言,官制的設置是有很多成功經驗可以總結的;但就國家和社會的關系而言,因社會缺乏自治,則政治缺乏社會資源;而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因人民缺乏自治,則縣治難以發揮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