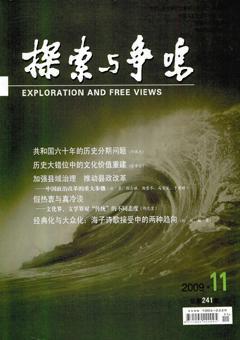縣域政權改革的邏輯
楊雪冬
已經(jīng)存在了2000多年的中國縣制是世界上最悠久、也是一直沿用至今的地方政府體制。這是中國政治制度相較其他國家政治制度的一個重要差別,也是支持中國政治統(tǒng)一的基礎性制度。無論是傳統(tǒng)社會中的“政不下縣”,還是近代強調(diào)地方自治的新縣制改革,抑或是當代縣域管理的黨政結構,縣這個政權層級都擁有完整的國家管理和控制功能,以及相應的組織安排、工具手段。相對于中央來說,縣是最完整的微觀國家;而相對于社會來說,縣又是離其最近的現(xiàn)實國家。
目前的縣級政權運行由黨政結構決定。雖然中國有著悠久的縣制傳統(tǒng),但是現(xiàn)行的縣域管理體制是由共產(chǎn)黨重新構建起來的。建立的基本方式是先建黨,再建政,然后由政黨動員和構建社會,形成對政權的合法支持。雖然在縣級建立了完整的國家權力機構,實現(xiàn)了明確的制度分工,但是無論從縱向關系,還是水平關系上,黨委都是推動這些組織機構運行的體制動力,政黨管理方式的變化直接決定了政權運行方式的變化。在高度垂直化管理的政黨體制下,縣級黨政結構單一化為黨的地方組織。
改革開放給縣級政權帶來的最大變化是縣級政權開始恢復微觀國家的地位。一方面,下放權力成了國家和黨領導體制改革的重要內(nèi)容,縣級政權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尤其是發(fā)展經(jīng)濟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在黨政分開原則指導下,縣級政權機構的分工更清楚,運行的獨立性也有所擴大。“五大班子”(黨委、人大、政府、政協(xié)、紀律監(jiān)察委員會)成了縣級政權的基本架構。盡管各級政權結構類似,但是縣級政權以書記為“一把手”的運行機制更具有個人化色彩。人大、政協(xié)由于沒有人員進入常委會,所承擔的法定職能失去了現(xiàn)實權力的支持,造成了縣級政權內(nèi)部結構失衡,運行高度黨委化,并強化了“一把手”的權力。而縣域內(nèi)公共輿論和公民社會的不發(fā)達,進一步彰顯出這種個人權力擴大的潛在危害。
因此,在縣域政治中,形成了一種悖論性的現(xiàn)象:一方面,縣級政權抱怨上級權力下放不足,干預過多;另一方面,縣級政權的領導者在縣域范圍內(nèi)又有著高度的自由裁量權,即便存在著不斷加強的垂直控制。縣級政權——這個微型國家擁有了畸形化的自主性。這種自主性在發(fā)展經(jīng)濟方面得到充分發(fā)揮,并適合了經(jīng)濟效率的要求。縣級黨委通過中心工作機制將所有的國家政權機構都動員起來,后者無論是職能運轉還是資源投入都圍繞經(jīng)濟發(fā)展這個中心。在社會對財富增加渴求的背景下,官方的經(jīng)濟增長邏輯普遍化為社會的要求,并從國家道德層面消除了一些社會群體對具體經(jīng)濟增長政策措施帶來的消極后果的抵抗。由于經(jīng)濟發(fā)展已經(jīng)成為了黨的意志、國家目標和社會共識,所以在經(jīng)濟發(fā)展問題上,縣級政權無論在體制內(nèi)還是社會中都獲得了足夠大的空間。
在市場經(jīng)濟完善的過程中,公共權力空間的擴大為權力的“私有化”提供了條件。一方面,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為所有物品和關系轉化為商品提供了可能和理由;另一方面,交易的邏輯也跨越了還沒有定型的公私邊界,從經(jīng)濟領域向社會政治領域蔓延。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具有畸形自主性的縣級政權面臨著急遽腐敗的侵蝕。與資本勾結和與黑惡社會勢力沆瀣成為兩種典型形式。一些縣級政權嚴重脫離了體制控制,喪失了對縣域社會安全和公正性維護的基本功能。無論在東部發(fā)達地區(qū),還是在中西部欠發(fā)達地區(qū),我們都能看到這種縣級政權公共性蛻化的現(xiàn)象。
以避免地方利益做強為基本目標的“異地任職”制度,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這種蛻化。一方面,官員到異地任職雖然會與地方勢力保持距離,但是也不容易對任職區(qū)域形成認同。縣域社會固然規(guī)模更大、關系更為復雜,但依然是“熟人社會”。地域認同對官員構成了情感約束和道德制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縣級黨政首長調(diào)動頻繁,“空降部隊”增多(多從上級直接調(diào)任,幾乎沒有本地干部提升的可能),更抵消著這種地域認同的形成,也放任了政治投機心理。“流官”替代了“父母官”。一些官員毫無顧忌地實現(xiàn)著公共權力的“私有化”。
本地干部的心理也有失衡的傾向。在經(jīng)濟上,大部分縣的干部收入明顯低于地級市、省會城市的同事;在政治提拔上,有限的縣處級職位也使許多人無法企及;在崗位上,又不斷受到干部年輕化和用人“個人化”的沖擊。本來依靠家鄉(xiāng)情感保持高度穩(wěn)定的縣域干部群體反而成了最不穩(wěn)定的群體,責任意識受到嚴重削弱。大批有著豐富經(jīng)驗的官員以提前退休的方式進入了經(jīng)濟領域,使縣域經(jīng)濟進一步官僚化,并推動了縣域政治生態(tài)的惡化。
當然,以干部體制為核心的垂直控制在方式上也在增多。縣級政權內(nèi)部也在形成某種非正式的“一把手”制約機制。一是黨政一把手矛盾的加深和顯性化,縣委書記的“拍板權”受到了縣長的掣肘。而縣長通常又是縣委書記位置的第一接替者,這為縣級決策更改頻繁埋下了隱患。二是縣委常委會成員數(shù)量增多,公安局長、實力派副縣長、縣委政府兩辦主任等在許多地方都進入了常委班子。人大、政協(xié)作為民意機關繼續(xù)被排除在縣級政治決策之外,而公安局長政治地位的提高,又破壞著黨委領導下的司法體制內(nèi)部關系的平衡,法院、檢察院的地位相應被削弱。因此,這種非正式制約機制,雖然存在著分散“一把手”權力的可能,但更可能造成縣級政治向“實力化”蛻變,體制內(nèi)部關系更加不平衡。更危險的是,這種“實力化”也容易簡化為“金錢化”,職位直接代表著經(jīng)濟實力。
縣級政權運行的績效日益與“一把手”的能力、素質、自我約束程度等個人因素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一些所謂的“政治強人”或“鐵腕書記”頻頻出現(xiàn)于各地的政治版圖上。客觀地說,這些官員的大部分行為對于縣域政治生態(tài)的改善并沒有帶來實質性的變化,因為他們執(zhí)政的方法多是高壓驅動型,帶有強烈的個人化色彩。雖然有效發(fā)揮了地方自主性,但也充分暴露了個人權力過大的弊端。形象工程、決策個人偏好往往是這些政治強人留下的遺產(chǎn)。
隨著各類資本投資的擴張,掌握較齊全的生產(chǎn)要素(最突出的是土地、自然資源)的縣在經(jīng)濟重要性上也在提高,縣域之間的經(jīng)濟競爭日益激烈,縣級政權希望獲得更大的經(jīng)濟發(fā)展自主權。這種要求也得到省級政府的積極回應,以打破現(xiàn)有城市化方式對農(nóng)村造成的資源汲取,形成資源的反向流動,恢復農(nóng)村與城市的平衡。這是“省管縣”財政體制改革的根本原因。
經(jīng)濟自主權的擴大必然會產(chǎn)生提高政治地位的要求。縣域治理惡化增加了這種要求的籌碼,因為縣域內(nèi)出現(xiàn)越來越多的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如果不能控制在特定范圍內(nèi),必然會對上級政權乃至整個體制產(chǎn)生沖擊。“一把手”的重要性再次體現(xiàn)出來。必須在制度上為這些管理著微型國家的“一把手”建立起有效的政治激勵。因此,我們看到了今年以來中央要求縣委書記任命權上收到省委,各省提高部分縣委書記的政治級別等舉措。這對于一直抱怨縣里工作條件艱苦、晉升渠道有限的縣委書記來說,無疑具有很強的激勵作用,也會緩和黨政一把手之間的摩擦。但是,從長遠來看,如果缺乏其他配套機制,這些措施很可能會進一步助長縣域政權自主性的扭曲,因為書記權力的強化會加劇縣級政權內(nèi)部結構的失衡。
總結過去30年縣域政權的運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經(jīng)濟放權和政治整合(或控制)一直是推動其變化的兩個主要動力。由于縣域政權內(nèi)部結構的失衡以及縣域社會發(fā)育不夠,使得這個微型國家的自主性呈現(xiàn)出畸形狀態(tài),即自主權的擴大集中體現(xiàn)為個人權力的弱約束化。面對日益增強的社會要求(數(shù)量上和渠道上),擁有這種畸形自主性的縣域政權顯然疲于應對,甚至會由于個人權力的過大引發(fā)體制內(nèi)部的抵制和社會的不服從。因此,單純地依靠政黨體制的政治整合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個人權力的弱約束問題。這就必須重新思考如何恢復縣域政權內(nèi)部結構的平衡和推動縣域社會的發(fā)展。前者需要回到現(xiàn)有的憲法框架下,恢復和強化縣域政權各組成部分法定的功能;后者則需要為縣域內(nèi)公民社會和公共輿論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條件。這是一個法治與民主同步進行的過程。這也是重新思考“郡縣治,天下安”這句話含義的現(xiàn)實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