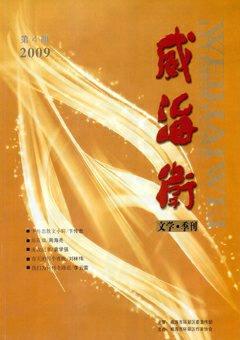李東山與“寶”字牌鐘表(外二篇)
近日,筆者步入一家古玩店,以低廉的價格購得十架解放前形態各異的座、掛鐘。打開鐘表盒,擦去鐘表內層層塵土。筆者發現這十架鐘表除了一架為日本“馬球”牌鐘表,其余九架全部帶有“寶”字。如此之多的“寶”字牌鐘表引發了筆者的興趣。經多方考究“寶”字牌鐘表竟意外地得知它誕生于煙臺,而且“寶“字牌鐘表創始人李東山是威海人。
李東山(1873-1946),本名李秀桐,字東山,威海城里人。李東山幼年家境貧寒,早年當過北洋海軍魚雷營工兵,戰后以肩挑小販謀生。后赴煙臺恒興德絲行當伙計。遂在堂兄的接濟下,自辦一小雜貨鋪主要經營五金、油漆、雜貨,包括進口的各類洋貨。鼎盛時期有職工50余人,資金總額達6萬元(銀元)以上。同時,在威海建房16間,買地百畝。
進口的洋貨中,從日本進口的馬球牌鐘表引起李東山的注意。他聘請鐘表修理師傅唐志成為技師,他多次赴日本觀摩學習,購置設備。1915年李東山在煙臺朝陽街開辦我國第一家民族鐘表工業——寶時造鐘廠(1931年更名為“德順興造鐘廠”),自任經理,鐘表外型是仿日本的,注冊商標是五角星內一個“寶”字。1928年起,“寶”字牌鐘表質量趕上日貨,而且價錢還低于日貨,很快擊退了日貨。開辟了膠東、北方及東北市場。1931年有職工500余人,年產座、掛鐘5萬余架。李東山也躋身于煙臺五大家之列。自1932年起,他先后派出十幾名技術人員分赴天津、沈陽、上海、青島等地協助創辦造鐘廠。建國后,這些技術人員皆為國家鐘表工業的中堅,他們奠定了國家手表工業的基礎。
“這些鐘表距今最近一架也有60余年的歷史了,是否還能像以前一樣?”朋友李君一直在好奇。筆者撥準時間、上足鐘弦,鐘表竟然還能發出清脆的響聲。鐘表背面至今還保留著當年貼在上面的廣告,“請用國貨‘寶字牌,本廠設於(于)山東煙臺朝陽街東巷……掛鐘準走八日時辰……山東煙臺德順興造鐘工廠謹啟”。“寶時造鐘廠”實為中國造鐘工業第一家。李東山實為中國鐘表工業第一人。
威海不同時代的“婚書”
威海舊時婚姻均為父母包辦,由媒人提親,甚至“指腹為婚”。一般“門當戶對”,屬相對頭,歲數合適,一般男大于女二、三歲。兩方父母同意后,則定親,送柬。“送柬”是舊時正式簽訂婚約的一種形式。建國后,男女青年逐漸做到婚姻自主,婚事新辦。市民結婚由民政科統一辦理領取結婚證。近年來,筆者在威海民間收藏了20余份威海境內建國前后的“婚書”,現選擇幾份比較有代表性的“婚書”與讀者朋友共同分享。
1、1939年的“娃娃親婚書”
舊時的婚書又稱“八字貼”等,一般用描金鸞鳳朱紙,依男左女右次序,分書男女姓名、生辰八字、籍貫、祖宗三代名號;一式兩份,擇吉日請媒人傳送,以為婚據。筆者收藏的這份婚書紙質粗糙,底為紅色,黑筆書寫,是1939年文登四區高村鎮村民的“娃娃親婚書”。訂婚人男只有8周歲,而訂婚人女只有3周歲。婚書外有封套,封套面有“龍鳳呈祥、平安如意、福祿鴛鴦、天仙送子”等吉語。前幾日,筆者多方聯系得知當年的訂婚人男方至今還健在,筆者在電話里與老人溝通,當說起70年前那段“娃娃親”故事時,老人卻“守口如瓶”,閉口不談。
2、1946年威海市民的一份“訂婚證書”
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的“訂婚證書”采用統一的格式。筆者曾經在威海民間見過威海衛管理公署印制制式的“訂婚證書”,上面印有“威海衛管理公署印制”字樣,“訂婚證書”背面貼有印花稅票等。這是一份1946年的“訂婚證書”。“訂婚證書”展開長35厘米,寬23厘米,“訂婚證書”上的訂婚男和女為威海人,另外上面還有書寫男女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的姓名,介紹人、主婚人的姓名都寫得清清楚楚。“訂婚證書”裝在特制的鐵筒內,鐵筒外有“百年好合、鴻雁傳書、孔雀開屏”等圖案以及印有“上海新亞書店印行”字樣。這是一份特別講究的“訂婚證書”,訂婚人的身份應當不同尋常。
3、1955年威海市人民政府頒發給威海市民的“結婚證書”
這張結婚證書形狀類似今天的獎狀,中間上方有“五角星、五星紅旗、麥穗”等圖案。“五角星”上方有“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和睦團結、愛國生產”文字。“結婚證書”簽發的時間為1955年1月18日,上面有結婚人的姓名、年齡、籍貫、編號、威海市人民政府和市長的印章等。新中國成立以后,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7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并于同年5月1日頒布實施,但新《婚姻法》頒布實施后,當時真正自主登記結婚的人卻很少。這張保存了50余年的“結婚證書”更加彌足珍貴。
老威海攝影社拍攝的一張照片
筆者收藏的這張老照片是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威海三位儒雅紳士的合影照,照片由當時威海衛大同福記攝影社拍攝。
說起收藏這張老照片還有一段小故事。筆者近幾年在威海民間搜集了兆芳照相館、美麗照相館、壽星照相館和亦我攝影社等一部分老威海照相館拍攝的照片。筆者前幾天在一藏友處獲悉威海一郊區村莊改造時一村民在自己老屋中發現帶有“威海衛大同福記攝影社”的照片。當筆者準備收藏這張照片時,卻得來已經被煙臺一藏者收藏的消息。接下來筆者一直千方百計尋找這張照片的下落。近日,筆者在威海的舊書攤上卻發現了這張照片并被筆者收藏。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老照片上有三位站立男士,右側為一老者,頭戴瓜皮帽,威海人又稱瓜皮帽為“西瓜皮帽”,這種帽子常為有身份的人所戴,一般百姓只有在節日期間戴用。老者身著長袍,長袍又稱大褂,有單棉之分。這是清末民初威海民間男子的主要裝束之一。長袍皆右開大襟,布盤紐扣,開叉及手,下垂中指末端。一般用棉布為料。老人面對攝影師的鏡頭略顯得緊張,表情很不自然。筆者猜測老人可能是第一次照相吧;中間站立者為年輕男子,頭戴禮帽,禮帽一般為鄉紳、商人及知識分子所戴。身著長衫外加穿馬褂,馬褂,長僅及于臍,這種穿著稱為“長袍馬褂”,在當時成為一種時尚;左側年輕男子應當為一知識分子,著裝與中間男子基本相似,只是手握禮帽,該男子可能剛剛走出理發店就來到了照相館,也許在向他人炫耀一下自己時髦的發型吧!這張黑白照片鑲在灑金紙片里面,照片的右下角有“威海衛中山路大同福記攝影社”紅色字樣。筆者查閱有關資料得知“威海衛中山路大同福記攝影社”由黃智軒經營,固定資產1千元(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