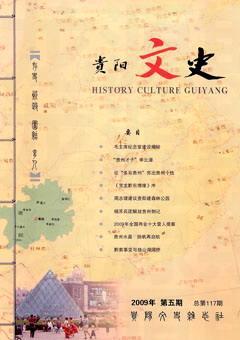非青非紅
葛兆光
下面的故事,是真實的經歷,不是編小說。
40多年前。我所在的貴州小縣城凱里周圍。遷來十幾個隸屬于第四機械部083系統的“中央廠礦”,它們好像雨天后林子里的蘑菇一樣,散布在四周的山旮角里。接著,在每周例行的“趕場”時,原本熙熙攘攘總是晃動著靛藍土布衣、苗家百褶裙的街市,突然也從四面八方涌進好多勞動布工裝。他們不太講價的采購,嶄新的一色穿著,和摻雜著地方方音的普通話。讓這個小鎮,變得有些異樣。發生了關于外來人和本地人故事背后,還有關于文明和落后的理解,以及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之間鄉土認同的差異等等。
一
我和我當年最好的朋友劉元、惠倫,既不是凱老街或州委子弟一類本地人,也不是上世紀60年代三線內遷時來的外地人。我們三家都來自北京,卻是在60年代初從各部下放來的。劉元、惠倫家是冶金部的,劉元的父親在州委黨校當教員,因為他有文化,算是讀書人。惠倫的父親在縣機關,那時他還年輕。記得是我們那里有名的籃球好手,放在現在。算是縣城里的邁克爾·喬丹,后來還當過縣籃球隊的教練,但當時他的正經工作,好像是縣政府的一個小科員。我家則來自外貿部父親雖然出身大學的外貿專業,又曾經在南京軍政大學當過教員,但自打一參加革命工作起,就因為好亂發言的脾氣。始終在被“戴帽”和下放的邊緣搖搖晃晃,雖然混過了好幾次風浪,但終于在1960年最困難的年頭。被驅離外貿部。趕到凱里這個貴州東南邊緣的山城。
和我家一起下放的,還有另外三家。一家的男主人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陳叔叔,他后來托人走關系。在“文革”前就回到北京外貿學院教書。另一家是學西班牙語的韓叔叔,他大概是單身,高高瘦瘦的,至今我不知道他的下落,后來我家全部離開凱里,他卻還在當地苦撐。最后還有一家,男主人赫赫有名,是當過蔡元培先生秘書的高平叔先生,從北京下放到凱里師范,最終連語文課也不讓他上,只能在巴掌大的資料室里管理圖書。他的太太姓張,傳說是莎士比亞專家,英文極好,個子高高的,常常模樣很奇怪的,用大扁擔挑著兩個小小籃子去買菜,籃子里左一棵白菜,右一個茄子,也許連五斤都不到,晃晃悠悠搖搖擺擺的,卻也成一副擔子,惹得當地剽悍的苗家漢子常常大笑。仿佛看西洋景兒。
上世紀70年代上半葉,“文革”高潮已經過去,這幾家也從被慘斗的“牛鬼蛇神”中逃脫出來,大體過上了正常的團聚生活。插隊農村的我們,雖然沒有找到好工作,但大多也都回城。三線內遷早已是10年前的事情了,那些外地人漸漸熟悉了這個民風強悍的山城,而本地人也看慣了這些自居自傲的外地人,在趕場的日子里都混在一起。可是,本地和外地的認同感始終是涇渭分明。現在回想起來,那些從上海、從北京、從四川內遷的人,其實很悲慘,他們的心里,一方面是“身在異鄉為異客”的悲哀,一方面卻是城市人對本地人的無端傲慢。他們身在苗鄉卻保持著外地人的口音、衣著、圈子,本地人對他們的敬畏,又增加了他們的自負。特別是,當時從下鄉的知識青年里招工,因為是中央級廠礦,又是保密的電子設備生產單位,所以要選根紅苗正的,只有本土優秀和純粹的年輕人,才有可能進入這些地方。這種優選法包括地區的差異和出身的差異,又加上了文明(技術)的差異,更激發了他們的倨傲和狂妄。凡是被招進去的本地人,雖然是本地出身,卻因為沾了中央級的光,也都仿佛高人一等,迅速地認同了“中央”而背棄了“地方”。穿著勞動布工裝挺著胸脯對我們也操起了北京話,連國罵都是“我操……”,省略了后面的賓語,也顯出了連罵人都比你文雅。
二
劉元、惠倫和我當時都二十一二歲,因為家庭有問題,進不了中央廠礦這個高門檻。一開始,我們都曾經想過這個路,可是,當招工的人從鼻子里噴出蔑視的氣,眼睛里露出嘲笑的光,我們就知道無望,再也不心存妄想。惠倫的父母情況好些,就落在一家叫作“紅光化工廠”的小廠,算是有技術的產業工人。我則因為父親母親的緣故,只能靠我在鄉下插隊時曾經做過磚瓦工的本錢,好不容易混進了縣磚瓦廠,仍然干著用手工打磚打瓦的活兒,只是每月有一份薪水,吃飯有一個食堂。劉元最慘,他父親“文革”初期被迫害自殺,全家落了個“自絕于人民”的反革命家屬帽子,所以,只能到一家國營飯店去做廚師。雖然飯店吃得飽,但在一般人心中,地位比起工人階級,特別是比起中央廠礦產業工人來,差了不止一截。不過奇怪的是。進不了中央廠礦的我們,也不大能夠融入本地人的群體。盡管我們在家說的北京話,可能比中央廠礦的人還地道,但是,因為在地方,所以夠不上中央那一級:盡管我們在外也操著地道的以鎮遠腔為基礎的“州委機關”話,可是因為出身不是本土,好像也不那么被當地人認同,有些像兩邊不認的夾心人。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罷,我們三人之間關系特別好,每當周日我從鄉下的磚瓦廠回到縣城,大多數時間都會和他倆聚在一起,何況我們恰恰都是當地最好的乒乓球手,所以在一起的時候,總是在找地方打球。
進不了中央廠礦做學徒工,多少有些受屈辱的感覺,所以總想找機會“復仇”,哪怕是象征性的贏回自尊。大概已經是1973年吧,我們這支沒有單位的雜牌球隊到處南征北戰,幾乎所向無敵,于是,也找中央廠礦的乒乓球隊下戰書。那時候,據說是生產過人造衛星部件的凱旋廠和208廠都很牛,一個南京人和一個上海人,年紀比我們大一些的,都曾經拿過地區的冠亞軍,也許他們覺得我們是土包子隊,但也許也知道我們厲害,為了保持榮譽,他們常常借口忙而不太應戰。只是架不住挑戰多了,起哄的人多了,也激起他們的好勝心,終于約定了在秋天的一個周末,派卡車把我們拉到208廠里決戰。現在想起來,那一場球的觀眾好多,氣氛也緊張。有點兒像武林以生死決勝負的意思,上場的人也不怎么互相寒暄,而觀眾呢?卻在四周一個勁兒地鼓噪。這場球也許是我一生記憶中最難忘的,近四個小時,惠倫贏了兩場輸了一場,劉元也贏了兩場輸了一場,而我,先是莫名其妙連輸了兩場,但是,最后卻像絕地反擊,在決定性的第九場,面對曾經號稱第一高手的那個南京人。居然演出了一場驚天大逆轉。
再搭敞蓬大卡車回到縣城,已經深夜,那時的縣城里沒有幾盞燈,到處是黑漆漆的。下車后我們都沒有回家,也沒有像現在的年輕人一樣,舉杯豪飲或者徹夜狂歡,只是在一柱昏黃的路燈下面坐著百感交集,直到三四點才默默分手。我至今不明白,為什么我們會這么在乎這次比賽,其實,我們都參加過上到省、下到縣的各種比賽,但是,哪一次也沒有像這一次這樣,讓我震撼
和難忘,經過九場幾乎四個小時,最后我們贏了,可是贏的時候想到的,卻是我們曾經被這個“中央廠礦”拒之門外。
盡管贏了轟動一時的比賽。惠倫還是在廠里每天上班開機器,我呢,那時已經轉到龍頭河畔的農藥廠,每天圍著灶臺用熬骨頭的動物油制造土肥皂。而劉元則還是在凱北飯店當他的白案廚師整天揉面。在那個既不抓革命也不促生產的年頭,人好像沒有任何其他念頭似的,在時間里面漫無目的地磨蹭。只是當提到打球,想起那場驚心動魄的比賽,才會精神一振。但很快又黯淡下來,畢竟中央廠礦的人還是挺著胸脯來趕場,本地人還是抱著團兒敵視著外地人,我們還是三不靠,只好自己打自己的球,沒有人知道我們曾經用這種贏球的方式來自欺欺人地喚回自尊。
在平平淡淡的時間流逝中,生活也有些變化。在飯店的劉元有了女朋友,不太來打球了。據說是一個在當地很出眾的女孩子,長得很漂亮,和劉元很般配。因為劉元也是一個相貌很出眾的男孩,中等個頭,皮膚很白,臉方方的,嘴上有淡淡的黃胡須,一直很有女生緣。恰好那時我去了縣宣傳隊幫忙寫劇本,惠倫好像也在秘密進入談戀愛的階段。這一來,大家就漸漸很少聚會了,只是在周日的時候,還偶爾見上一面。
記得是1974年夏天,每天晚上我都在山上宣傳隊的住處無聊地翻閑書。有一天晚上,有人突然來告訴我說。劉元住院了,是傳染性的肝炎,大概是因為飯店不衛生的緣故,又過了兩天,又有人來告訴我,劉元死了,死于喝酒。本來他有肝炎不應該喝酒的,但是這時他的漂亮女友因為嫌他家是反革命,又在飯店工作,提出和他分手,他受不了,悶頭喝酒,于是導致了肝昏迷。那個時候州醫院條件很差,回天無力,他就這樣死了。我匆匆趕到醫院。看到劉元的姐姐和弟弟在,看到剛剛換好斂衣的劉元,臉上白白的,毫無表情,只是頭發從額頭上落下來。仿佛被汗凝成了一縷。停尸房里沒有其他人,也沒有一點兒聲音。奇怪的是,他姐姐和弟弟也都不講話,好像司空見慣似的,直到我默默走出門,他姐姐才看了我一眼,點點頭,她煞白的臉上面無表情,其實我知道她很愛這個弟弟,或許是早就已經過度透支了悲傷,這時已經恢復平靜了?
我沒有哭,也哭不出來,昏昏然地走回宣傳隊所在的山上,路兩邊的樹木在夜風中颯颯作響,我高一腳低一腳,至今不知道怎么走回去的。
四
我越來越相信“禍不單行”這句話。劉元死后,也許是因為照顧他的緣故。他媽媽也染上肝炎,只好成天躺在床上。這一家從北京來的時候是六口人,兩個大人四個兄弟姐妹,可是現在卻走了兩個,父親和長子。劉元的姐姐劉萍比我高一班,是學校出了名的美人,在1967年組織“苗嶺展新圖”演出團的時候,她是幕間朗誦者,因為當時模仿大型革命歌舞劇《東方紅》,朗誦的人是主角,挑選很嚴格,可她一來因為從北京來,口音好不必說,二來是人長得漂亮。所以一下子就入選。據說當時暗戀仰慕者成群,后來下鄉到白臘公社當知青,好多男生還借了種種緣由,去她的寨子里晃悠,想有機會親近,可是,最終她卻因為家庭問題,是最后一個從那個緊靠麻風村的白臘寨子離開的。劉元的弟弟劉剛,個子很高,和我弟弟是同學,“文革”開始的時候,只是一個小學生。這個時候也在一個工廠里做工人。他們的妹妹最年輕,好像還在學校里念書。因為劉元的關系,我還是常常去他家看看,雖然幫不上什么忙,總是默默站一陣,說上幾句話,這時通常是劉萍出來,淡淡地寒暄兩句。
好像是過了幾個月,突然有消息傳來,說劉剛殺人,被抓起來了。這讓我大吃一驚,跑去打聽,原來這個平時不聲不響的青年,在家里的種種變故之后,心理早已崩潰。州黨校就是他父親的單位,有一個當初帶頭逼他父親自殺的人。現在是“革委會”的頭頭,劉剛把他的孩子,大概只有10歲吧,騙出來殺了,尸體裝在麻袋里,扔下了清水江。事后審訊的時候問他原因,很簡單,就是給他父親復仇。結果當然不必說,不僅是故意殺人,情節惡劣,而且是向“文化革命”瘋狂復仇,自然是判了死刑。
有時候思緒轉移很奇怪,這件事情在我的心里,一直很不愿意翻出來。畢竟這是一個殺人犯,對手無寸鐵的孩子下手,太狠也太無能。不過,因為劉元的緣故,也為了他父親的緣故,對于劉剛。我又始終恨不起來。我把劉剛那張還很幼稚的面孔埋到心底,連想起劉元的時候也盡量不連帶到他。多少年過去,我好像已經不再想起他來。也把這件殺人案淡忘了。可是,前幾年在歐洲一個大學里看到西洋人畫的《行刑圖》,洋人驚異中國人觀看凌遲的熱心和好奇。畫上了很多圍觀者,然而我看到這幅圖的時候,不知道為什么,突然劉剛的故事又浮現在我腦海里,而且異常地清晰,近得好像就在眼前。
在執行死刑的那天,我并沒有去看,我怕受不了,聽說我弟弟去了。中國有一個很奇怪的習慣就是看殺頭。好像很多人心底的惡念與憤懣,是在看殺人時宣泄的。看殺人仿佛是一種慶典,凱里南邊有一個殺人坳,似乎就是這個祭祀儀式場地。從大十字到殺人坳那一公里多的大道。仿佛是引人進入神殿的甬道,用刑車加上喇叭押解犯人赴刑場那天,好多人在路的兩旁觀看。后來,我聽到轉述,好像劉萍姐妹都去了,據說,她們去付了5分錢的子彈費。然后收了尸。看見她們的人說,她們姐妹倆的眼睛里面,毫無表情,也沒有眼淚,那種司空見慣渾間事的鎮定和冷漠,反倒讓人想來就不寒而栗。
幾天以后劉元的媽媽就死了,后來,劉萍曾經告訴我,其實沒有人告訴她兒子被槍斃的事情,但也許在暝暝中,上帝已經把徹底的絕望傳遞到她的心中,她不再服藥,一直等到閉上眼睛,去另外一個世界。
五
就像三角缺了一角便不穩一樣,自從劉元去世又加上劉剛被處死,這個夾在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間的小團體便解體了。后來的兩三年間,也曾有其他好手偶爾加入戰團,但是,沒有了當年的悲情,打球仿佛只是消遣,在無聊的歲月中打發時間和發泄精力。
時間過得好快,轉眼中國發生巨變。1977年、我考上北京大學,終于離開生活了17年的貴州北上讀書,接著,惠倫也和一些朋友結伴離開,去了開放的深圳,只有劉元的靈魂永遠地留在那片山坡上,他和他的母親、弟弟,留在那片亂墳崗上。離開凱里的時候,我曾經去過那個山坡,冬春之際,新草未生,坡上一片枯黃,墳邊的衰草和墳上的白布條,在寒風颯颯中搖曳。他家從北京來的六口人,最終只剩下了煢煢孑立、相依為命的姐妹倆。聽說,為了撫養妹妹,劉萍嫁了中央廠礦一個俗氣的天津人。很多朋友都奇怪這段不相稱的婚姻,但是我明白這是無奈,畢竟這是個工人階級。又是中央廠礦的。不過。據說10年后劉萍離婚了,也去了深圳,她的妹妹也嫁了人,到了安徽,但是我一直沒有她們姐妹的消息。
2002年的春天。深圳觀瀾湖。因為在香港教書,我和在深圳的惠倫再次見面。20多年沒有見面,我們聊打球,聊生活,聊北京、香港和深圳,很奇怪,就是閉口不談往事,既沒有太多地聊那個我們生活了17年,卻始終視我們為陌路人的凱里,也沒有提到那個時候朝夕相處一起征戰的好朋友劉元,只是有時候,彼此目光相對,便又匆匆分開,心底有一點兒悲情猶在,眼中似乎有一些往事在說,但是。畢竟誰也沒說,也許是的,往事如煙,既然已經藏在心底。又何必再翻出來呢?
責任編輯:熊源王亞平李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