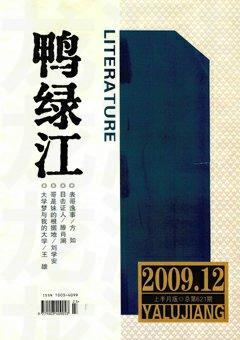老龍口·酒神(連載之十七)
鄒長順 李同峰
講得口干舌燥的大師傅呷了口茶水,一酒工說道:“我知道了,老龍口的苦水井變成甜水井,是因?yàn)樯屏嫉拿献泳凑塘x救下了白衣少年,結(jié)果那個少年不是別人,正是東海龍王的小兒子,遼河小白龍,是他把那口苦水井變成甜水井的。”
大師傅端起茶缸,放到了自己的嘴邊。
“凈瞎編。”一個叫衛(wèi)陽的遼陽酒工不陰不陽地來了一句。
“放屁,這是真的,有能耐你編一個呀。”山西人不樂意了,要討個說法。
“算了。別和這樣的地痞斗氣,犯不上。”
“你說誰呢?”
“說你呢,怎么的?”
一場爭斗一觸即發(fā),各派各自操起了家什。
……
二十二
李偉彬在朝鮮的信件,飛越了千山萬水飛到丁靜蕾的手中,漸漸地融化了丁靜蕾那顆冰冷的心。
在老龍口院里,她和亭亭玉立的常芳雅走了個面對面,倆人臉上都自然地帶著笑意。
丁靜蕾首先說話,很高興的樣子:“芳雅,偉彬快回來了?”
常芳雅一頭霧水,反問道:“你怎么知道的?”
丁靜蕾被常芳雅問蒙了,她反應(yīng)過來了,原來李偉彬要回來的事,他還沒有來信告訴常芳雅,而是先告訴了自己。
面對常芳雅的疑問,丁靜蕾急中生智地搪塞著說:“我那天在報紙上看到的,說是抗美援朝的戰(zhàn)爭結(jié)束了,大批志愿軍要回國了,所以,我想李偉彬肯定要回來了。”
常芳雅聽了心里很得意,她認(rèn)為丁靜蕾說得很有道理。殊不知,丁靜蕾若反應(yīng)慢一點(diǎn)兒的話,恐怕就會被聽出破綻。
常芳雅此時臉上掠過一絲愁容,說:“三四年了,我天天為他擔(dān)驚受怕的。可他倒好,總也不來封信。”
丁靜蕾聽后,心里咯噔一下,想,信是總來的,也沒少來,可給的都是我呀。
“天天打仗,又沒有固定的地方,上哪郵信去。”丁靜蕾說。
常芳雅聽后點(diǎn)點(diǎn)頭,很同意丁靜蕾的說法。
“等偉彬回來就好啦,我就能吃上你們的喜糖了。”丁靜蕾又說,“那天王廠長在醫(yī)院里還說呢。”
“說什么?”
“他說,看到我,就像看到了你,他平生就做了四次大媒,都成了,等偉彬回來,成了功臣,他就更有面子啦,一定要把你們的婚禮弄得熱熱鬧鬧的。”
常芳雅聽后,開心地笑了,說:“王廠長對咱們太好了。”
“我首先祝福你,芳雅。”丁靜蕾說。
“秀龍哥他……”常芳雅問了一句。
“噢,他還是那個樣。”丁靜蕾很沉悶地回了一句。
“聽說他畫的畫、寫的字都能賣個好價錢?”
“那有什么用呢。”丁靜蕾聲音很輕地說,一種惆悵的表情掠過臉龐。
“靜蕾姐,我去辦公室了。”
“去吧,過一會兒我找你去。”
“哎,靜蕾姐,聽說新曲種快試驗(yàn)成功了?”
丁靜蕾此時得意地一笑:“快了。”聲音很干脆。
“這下你可成了老龍口的功臣了。”
“又不是我一個人的事。”
“起碼是你牽頭干的。”常芳雅說,“靜蕾姐,我調(diào)到你那兒去怎么樣?”
丁靜蕾一笑:“這不是我說了算的事。”
“我去找廠長。但是,你必須答應(yīng)要我才行。”
“沖著李偉彬,我也得同意呀。”
“謝謝你了,靜蕾姐。”
“我走啦。”
丁靜蕾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坐了下來,腦海里翻騰著剛才和常芳雅交談的一幕。她真的看明白了,在李偉彬眼里,只有她而沒有常芳雅。丁靜蕾在想,李偉彬啊李偉彬,你這到底是為什么?我什么地方讓你在心里放不下,我是有夫有子的人了,你干嗎這樣無休止地攪動我的心?等你回來的時候,我一定要把話和你說開,我們都是老龍口人,是朋友、同志,但不可能是……
丁靜蕾心里有些亂了,她不敢再想下去了。她又從抽屜里取出了李偉彬剛剛寄來的信,專心地看著。
靜蕾:
告訴你個好消息,我再有一個月就回國了。回國后,我仍然回老龍口上班,和你天天在一起,我想我會很開心很快樂的。你雖然身邊有秀龍,又有女兒,可這些都阻擋不了我對你的真情。
靜蕾,在回國前的一個月里,希望能收到你的最后一封信,我要把它揣在心里帶回去。你以前給我回的信,我都一封沒落地收著呢,我也一塊兒帶回去。將來,它們可以見證我們的感情。
靜蕾,時間過得真快,三四年了,你還是那樣嗎?我想應(yīng)該是的。
靜蕾,夜深了,到此擱筆吧。千萬別忘了給我回信。千萬,千萬……
李偉彬
丁靜蕾又一次看完了李偉彬的信,然后取出了筆和信紙,閂上了門,開始給李偉彬?qū)懶拧K氚堰@封信寫成絕交信,因?yàn)樗吹搅顺7佳艑λ钠谂魏桶V情,她不想傷害純潔無辜的常芳雅,也因?yàn)樗怯屑彝サ娜?她無法面對李偉彬的一切。
手中的筆如行云流水般地在信紙上游弋著,留下的是串串發(fā)自內(nèi)心的聲音:
“李偉彬——”用詞很硬。
“同志——”距離很遠(yuǎn)。
“你好——”禮節(jié)詞匯。
“今天在老龍口院內(nèi),我看到常芳雅了,她聽說你要回國的消息后,高興極了,一個勁兒地說等你回來,就可以請我吃你們的喜糖了。她還說你們的婚禮還是由王廠長主持,噢,還有新來的書記孫林寶。”
丁靜蕾寫出這些話顯然是為了讓李偉彬減少一點(diǎn)對她的思念,因?yàn)樗杏X李偉彬?qū)λ乃寄钸h(yuǎn)遠(yuǎn)超出了對常芳雅的思念,丁靜蕾想這怎么可以呢,名不正言不順嘛。
“我們老龍口廠這幾年發(fā)展很快,建起了西廠房后,又建起了職工療養(yǎng)食堂,寬敞明亮的車間辦公室。我相信,你回來后肯定不敢認(rèn)了,會感到驚奇的。西廠房和職工療養(yǎng)食堂的建成都有我們一份功勞,我們每天下班后都干到半夜,搬磚、和灰、抬石頭、挖地基,什么活都干,你若是在的話也會和我們一樣的,你說是嗎?”
丁靜蕾這段話像是寫給一般同志的一樣,把廠子情況介紹一下,只是事件,不涉及情感,平淡得很。
“目前,秀龍和我都很好。他雖然起不了床,下不了地,可心里一直想念你,當(dāng)我告訴他你快回來了時,他高興極了,連連地說要畫一幅最好的畫,在你和常芳雅成親的那一天,讓我代表他贈送給你們。連我們?nèi)龤q的女兒晶晶都奶聲奶氣地問李叔叔長什么樣。”
丁靜蕾的這段話已經(jīng)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地告訴李偉彬,她的家庭是幸福的、美滿的,雖然黑秀龍以床為伴,但在丁靜蕾眼里家庭還是幸福的,她在情感上還是沒有雜念的。
“我們?nèi)珡S上下都在大干,加班加點(diǎn),要實(shí)現(xiàn)建國五周年紀(jì)念日前產(chǎn)量翻一番的目標(biāo)。我們技術(shù)室也要在建國五周年前把曲種試驗(yàn)成功,以實(shí)際行動為建國五周年獻(xiàn)禮。”
丁靜蕾介紹廠里的情況,如寫一篇新聞報道,讓任何人讀起來都會振奮。但是,誰也不曉得,這背后有著一種怎樣的情感撞擊。丁靜蕾苦思冥想地這樣寫信,既要表達(dá)自己的心聲,又不能傷害李偉彬?qū)λ囊黄嬲\,真是難為她了。
丁靜蕾寫完信后,又仔細(xì)地看了一遍,才把信紙疊好,裝入信封,寫上了地址,粘上了郵票,她要在今天下班路上把信投到信筒里去。這是她給李偉彬的最后一封信,她已經(jīng)在上面畫上了一個感情上的句號。
信雖然寄出去了,可是夜深人靜的時候,她的雙眼卻睜得雪亮,心里還怦怦地跳,臉上還有些發(fā)熱發(fā)脹。她想,李偉彬這些年給她的信件無數(shù),每封信都述說著他對她的真誠和渴望,她也只能用信件回應(yīng)。這種文字交流很簡單,無論說什么,怎么說,都是停留在紙上,人還相隔千里。可是,再有不長時間,李偉彬就要回來了,而且還在廠子里工作,這下可不太好辦了。倘若李偉彬再見到她,還是像信上那樣一往情深的樣子,該怎么辦?回避?抬頭不見低頭見;拒絕?人心都是肉長的,她說不出口。想來想去她覺得,大概李偉彬和常芳雅成了親之后,也就會自然而然地打消對她的那份深情吧。
丁靜蕾的腦海中閃出了下面的詩句:
想去對你表白一棵樹的心跡,
我的語言都無法為你勾勒出一片碧綠的草坪。
想去眺望你的內(nèi)心觸摸你的深情,
我開辟不了一條通往你心間的小徑。
想去阻止你對我一往深情的心靈,
卻沒有足夠長度的手。
想對你說,喜歡、愛字字分明,
只能播下真誠,讓它在你我眼中飄忽無定。
我知道我自己肯定會顆粒無收,
你對我來說,也同樣會是囊中空空……
黎明到來了,黑秀龍醒了,告訴她感到自己身子下面濕了。丁靜蕾急忙停下了腦子里的“詩”,來解決黑秀龍身子下面的“濕”。
“李偉彬什么時候回來?”黑秀龍輕聲問。
“還有二十幾天吧。”
“夠用。”
“什么夠用?”
“我給他畫一幅畫的時間。”
丁靜蕾聽后不語了,因?yàn)樗幌朐诤谛泯埫媲斑^多地提起李偉彬。自己已經(jīng)為李偉彬一夜沒合眼了,這都是李偉彬三四年來用書信把她折騰的。
“靜蕾。”黑秀龍臉上帶著一種沉思的表情,雙手墊在頭下。
“嗯,還有事?”
“你當(dāng)初要是嫁給李偉彬就好了。”
丁靜蕾被黑秀龍的話弄得一頭霧水,不知所措,張著嘴說不出話來。心里在想,是不是她和李偉彬通信的事他知道了?不會的,李偉彬來的每封信,她都收藏得很好。她還在想,凡事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看來,雖然黑秀龍?zhí)焯焯稍诖采?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第六感覺卻是有的,而且挺靈敏。
“看來,你當(dāng)初選擇我是錯誤的。”黑秀龍不緊不慢地說。
“你說什么呢?”丁靜蕾來了一句。
“不,我是在說心里話,我在想,當(dāng)初你要是嫁給李偉彬的話,你我今天就不會這樣子了。我倒無所謂,可難為的卻是你。”
“好啦,秀龍,就別說這些了。”
(未完待續(xù))
責(zé)任編輯 喬 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