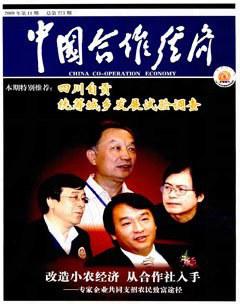“我們培養的是高端農產品經紀人”
曹 杰 高瑞霞
記者:上海大宗農產品市場提出了“中國第一農產品網上市場”的概念,如何描述這種現代農業的模式?
費建:我們將“電子商務、特許經營和創業就業”等信息時代的元素融入現代農業之中大宗農產品交易體系的建立,有利于促進大宗農產品的標準化生產與標準化貿易,有利于合理配置我國大宗農產品資源,有利于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調整中國農業產業結構,為中國大宗農產品在國際上行使定價權,促進中國由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轉變創造必要的市場機制條件。
記者:什么算是大宗農產品?
費建:從概念上講,沒有具體的說法。從實踐中看,大宗的概念就是量大、有標準,社會公眾認可的大批量產品。量大是第一位的。但同時,有五大類我們不做,比如棉花、玉米、水稻、小麥,也就是最大宗的農產品,我們并不參與。所以,實際上,做的是大宗里面的中小宗期貨產品。
記者:大宗農產品期貨和農業有直接關系嗎?
費建:關系很大。大宗農產品市場的交易模式和期貨很相似,但主要有兩個不同,保證金比例不同。大宗農產品不低于20%。期貨就很低了,風險容易放大。第二個,交易總量要控制,必須在商務部備案。比如,全中國的羅漢果產量只有1億6千個,那么你的網上訂貨量最多不能超過這個總量。你不能炒作概念。本來這個你只有一個,你把它炒到11個,還有10個你交不出貨來,那買方就通著你9月份交貨,那就被人逼死了。大宗農產品則必須交貨,這個和期貨不同。期貨,本來按照國家定位,是一個金融概念,而我們這個是商品流通中交易的最高模式,也就是中遠期交易合同。
記者:怎么體現這個最高?
費建:最高就在于交易的標準化。首先,交易的合約標準化,這方面類似于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的棉花交易市場。只不過,我們的農產品品種多。而交易基礎、法規模式都是一模一樣的。其次,由于合約標準化,必然會要求交易的產品標準化,從流通追溯而上,實現了農產品生產的標準化。交易的模式電子化,可以借助網絡撮合交易。
記者:網絡撮合交易是否可實現全國聯網?
費建:目前,我們還做不到全國聯網,但是兩三年后就可以了。市場有這個潛在的需要,這個是最根本的。我舉個例子,比如油菜籽的主產地在湖北、安徽,今年產量可能是200萬噸,本地消費了150萬,剩下50萬噸流出原產地。問題來了,浙江要20萬噸,江蘇15萬噸,上海5萬噸,但流轉的時候誰也不知道這個確切的需求量,會在幾個地域出現重復流通,造成浪費。如果通過網上充分交易,把區域需求確定下來,就可以真正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現在的地市縣都在建我們交易商服務中心,增長速度很快,最多的一天,全國有14個交易商服務中心開業。2009年年底,全國總體的網點建設將突破1000家。我們計劃全國性網點布局將在2012年全部完成。
記者:這種現代農業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當下的農民群體和農民經紀人?
費建:我們網點主要的工作就是培訓農產品經紀人怎樣用好互聯網進行撮合交易。我們培養的都是高端農產品經紀人,我們把很多大學生、有經營頭腦,甚至很多有經營實體的農產品經紀人培養出來。能夠引導一方經濟發展,不是簡單的將農民的東西收上來,販賣出去。我們可以讓農產品經紀人真正穿上皮鞋。實際上,我們這個網絡平臺是經紀人的得力助手,通過這個市場,看出了全國的市場需求是什么樣子的。為有效服務全國近千萬農產品經紀人,我們規劃在全國2861個縣和333個經濟中心城市區建立交易商服務中心,并探索將交易商服務中心實行特許經營,幫助更多的農民創造平等的貿易機會。
記者:農產品大宗市場的交易模式能在多大程度上解決三農問題呢?
費建:訂單農業為何失敗?“龍頭企業+農戶”模式搞產前產中產后服務,看上去能抓住農民,但實際上,市場價格高了,農民就私下賣了,價格低了,才會賣給你,根本不尊重訂單合同。而通過中遠期交易合同,再發揮農產品經紀人的信用中介模式,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比如,某村的一個經紀人在網上進行交易,可以在生產季節就提前把最終的產品賣出去了。而這種關系是有資金做保障的,首先雙方的身份有保證,20%的保障金:另外一端,和農民之間,經紀人憑借的是自己的信用,將經紀人的信用證券化了,開發了新的資源。而農產品經紀人從交易中得益,很大一快來自于自身信用收益。長此以往,這種高端農產品經紀人就可以振臂一呼,你們今年都給我種油菜籽。因為他可以通過中遠期合同,在生產之前,就把銷路通過網絡撮合交易的合同確定下來。這樣能從根本上解決農產品的賣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