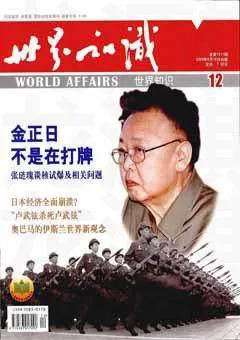作為知識分子和“政客”的加爾布雷斯
作為知識分子的加爾布雷斯
在西方語境下,“知識分子”的含義往往與我們中國人對這個詞的理解有所不同。有知識的人并不一定就是“知識分子”,單有知識并不足以構成知識分子的充分必要條件。
“知識分子”是指那些在公共生活中運用理性并拓展理性,執守理念又反思理念的人。“知識分子”概念往往更多地和“理念”而不是“知識”聯系在一起。一本著名的研究知識分子的社會學著作就以書名給知識分子提出一個別稱——“理念人”。它和“普遍性”、“公共性”聯系在一起,有時與“專家”概念相對立。它和“反思性”、“批判性”聯系在一起,意味著與權力和體制的疏離甚至對抗。它與對“正義”和“解放”之類的價值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追求聯系在一起,因此又往往和激進的、變革的、左翼的思想共生。
現代世界的各色意識形態大體上都是知識分子們所塑造的,個體知識分子也往往和特定的意識形態聯系在一起,但劉。各種意識形態和主流信念予以拷問、質疑、批判和顛覆的最主要的力量也是知識分子。有人信任,尊崇知識分子,但也有入鄙薄、憎惡知識分子—一比如美國歷史上就有源遠流長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亦可譯為“反知識分子主義”)傳統。有人對知識分子引領和改造社會的作用寄予希望懷有信心,但也有人哀嘆,由于現代社會的工具主義和專業化鐵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在西方社會中將趨于衰落和消亡。
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漫長、豐富而成就非凡的一生,就提供了一個獨特而又意義極為豐富的現代美國知識分子的個案。
加爾布雷斯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一個農民家庭,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取得農業經濟學障士學位后于1934年進入哈佛任教,1937年加入美國國籍。二戰中他曾擔任美國聯邦政府價格管理辦公室副主任等職,戰后重返哈佛,1950年代初即以《美國,資本主義》、《豐裕社會》等暢銷書和大量媒體文章成為美國最有公共影響力的公共思想家之一。他以凌厲風趣、寓莊于諧的“加爾布雷斯式文體”,不僅就美國和現代社會的基本問題提出了豐富的思想,而且造就了許多廣為流播的詞匯和妙語雋言。1976年曾他被哈佛一個雜志評為“百年來哈佛最有趣教授”。
在學術上,加氏置身于經濟學界,但就戰后美國經濟學的格局和潮流而言,毋寧說他是“反經濟學的經濟學家”,是經濟學的“偶像破壞者”,因為他以批判和諷刺神學化、教條化的主流經濟學為主要學術責任,直斥其已淪為“金錢勢力”和“沒有心肝的社會”的支撐。就經濟學家的批判性特質,以及超越專業領域的公共影響力而言,當今在《紐約時報》上寫專欄的保羅·克魯格曼也許可以被認為是加爾布雷斯的繼承者。由此也可見,以公共性、批判性加以界定的知識分子在美國尚未消亡。今日,面對在西方主流經濟學——這是加氏和克魯格曼共同厭惡和批駁的對象——影響下發生的金融危機,我們有理由更加重視加爾布雷斯的思想遺產。民主黨自由派的思想家和發言人
克魯格曼在一點上還無法與加爾布雷斯相比:他從未如后者那樣做過“政客”。戰后很多美國社會科學學者在學界和政府之間“進進出出”,但其中大多數人是以專業知識服務于政治權力,履行專業化、技術型職能,大體兼容于政府官僚體制,黨派和意識形態色彩并不突出。還有些更清高的學者,則刻意與政治權力拉開距離,甚至持批判和對抗姿態。相較之下,加氏深深介入黨派政治,與權力核心一度建立密切關系,在學者中實屬罕見。他不僅不忌諱,而且自豪于自己的“政客”(politician)的身份。而加氏的政客身份,加強而不是損害了他作為“知識分子”的身份。
加氏在政治上有明確的歸屬,自稱“執著的自由派”。而他的政治活動以為民主黨領導人代筆捉刀撰寫演講稿為重要內容。早在1940年在羅斯福第三任期競選期間,加氏就加入競選UnCbfbkcpuFfE04etVsnq3lj31+qR0d8rooMFuPHCkg=演講稿寫作班子。1947年初,他參與創建民主黨自由派的組織堡壘“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成為其領導人之一。1952年,加爾布雷斯加入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史蒂文森的競選團隊,充當其文稿的主要撰寫人。史蒂文森敗選后,加氏與其哈佛同事施萊辛格等組成“芬萊特小組”,就社會、經濟和外交問題對這位民主黨領袖進行“成人教育”。1956年史蒂文斯再次參加總統大選,加氏仍被召人競選班子,充當顧問和演講文稿起草人。史蒂文斯再次敗選,但芬萊特小組的活動直接導致了民主黨咨詢委員會的建立。在以后的幾年時間里,隨著肯尼迪在民主黨內的崛起,這個機構成為醞釀“新邊疆”政治綱領的主要思想庫;加爾布雷斯擔任其國內政策委員會的主席,成為民主黨自由派最主要的思想家和發言人之一。
在肯尼迪的內圈
在民主黨咨詢委員會的活動使加氏最終進入肯尼迪集團。1930年代約翰·肯尼迪及其兄長約瑟夫在哈佛讀本科時,加氏就曾是其輔導教師。戰后肯尼迪參加國會競選,加式和他接觸多起來,在各個領域向其提供咨詢。加氏的政治期望也逐漸由史蒂文森轉向肯尼迪,逐漸進入肯尼迪團隊的內圈。在由學界精英組成的肯尼迪“內圈智囊”(Inner Brain Trust)中,加爾布雷斯是重要而醒目的一員,乃至于與肯尼迪在大選中對陣的共和黨尼克松甚至高叫民主黨“已經成了施萊辛格、加爾布雷斯和鮑爾斯的黨”,以此來說明民主黨太左太激進。實際上,加氏的作用遠遠超出了通常意義上提供政策建議的幕僚策士:他實際上是塑造肯尼迪政治綱領的自由派特性、使之接續羅斯福新政傳統的主要人物。
本來在民主黨內,肯尼迪的自由派色彩并不突出,且與傳統的新政派之間頗有隔閡。加爾布雷斯不僅以自己的政策建議和“政治勸導”影響肯尼迪,而且利用自己在民主黨自由派和學術界中的影響力為肯尼迪爭取急需的支持。加氏認為“沒有任何事情比把其他自由派拉到肯尼迪陣營更重要了”,而使肯尼迪獲得民主黨自由派的標志和領袖人物、前總統羅斯福夫人埃莉諾的支持是關鍵環節。為此他不惜充當“權力掮客”,煞費苦心地拉近肯尼迪和埃莉諾,最終促使后者支持肯尼迪。加氏認為是自己一手促成了羅斯福派和肯尼迪最終的政治結盟,并稱這是他“在政治上最了不起的成就”。
1960年大選是加氏政治生涯的巔峰。他向肯尼迪提交了一個全面周詳、充滿自由派變革精神的競選戰略綱領,為“新邊疆”制定了政治基調和精神氣質。此外,他還向競選總部和肯尼迪本人提交了大量關于競選策略和政策議題的備忘錄和通信,其中包括供肯尼迪本人使用的一個“經濟問題精粹手冊”,上面列出可能會在各種場合被問及的問題及其應答。
加爾布雷斯又親手拔擢肯尼迪的政治魅力。在競選的高潮階段,加爾布雷斯“像一個老辯論教練對待一個深孚眾望的學生”那樣指導著肯尼迪,與之討論演講和辯論的各種技巧。在收聽了肯尼迪的一次廣播演說后,加爾布雷斯當即致信提出批評,毫不客氣地譏諷肯尼迪的演講風格“簡直是在模仿一只斷了翅膀的島”。
肯尼迪勝選后,加爾布雷斯理所當然地加入了就職演說的撰寫班子。筆者在肯尼迪總統檔案館親眼看到,在就職演說第一稿和第二稿上都留下了他大刪大改的紅色筆跡。“讓我們重新開始……”,“我們決不出于恐懼而談判,但也不要恐懼談判”,“(外援)不是為了擊敗共產主義,不是為了贏得選票,而是因為這是正確的”等傳誦一時的句子均出自其手。加氏對自己在這篇就職演說形成中的作用頗為自負,并稱:“愚意以為最好的部分還是我寫的那些。”
加爾布雷斯對肯尼迪的非同尋常的熱情和投入,乃出于其一貫的社會政治理想和對肯尼迪實現其理想的期望,出于其相信這是一次歷史性的抉擇,關乎共和黨人執政八年后美國能否重新恢復社會變革的動力,關乎能否給社會公正、自由的擴展和世界和平以機會。2006年5月在哈佛大學為加爾布雷斯舉行的悼念會上,肯尼迪的弟弟愛德華·肯尼迪參議員說:加氏的思想和建言賦予肯尼迪“以作為一個總統候選人所需要的正大莊嚴(gravitas)。沒有肯(加氏名字的昵稱),或許就沒有‘新邊疆’。”
加爾布雷斯之于政治權力,無論是此時的襄助和介入,還是肯尼迪之后的離棄和批判,都始終致力于把良知注入其中,也始終保持了作為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和批判精神。加氏在肯尼迪集團中所處的位置,實際上不過是“內圈的外緣”,在最核心的“愛爾蘭黑幫”之外。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加氏可算得上是肯尼迪的“帝王師”,但他并不把肯尼迪當成“主公”。肯尼迪需要他的思想和建言,但不想因為加爾布雷斯而使他的政府蒙上過于濃重的激進自由派色彩,招致政治上的麻煩。所以出乎很多人的意外,肯尼迪派加氏到印度去做大使。但加氏對自己和肯尼迪的關系洞若觀火,后來說:“我從來就認為,肯尼迪樂意于讓我待在他的政府里,但是要有一個合適的距離,比如說像印度那么遠的距離。這樣就能使他和我當時已加以充分闡述的經濟學觀點不至于湊得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