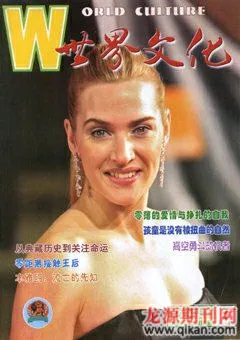本雅明:流亡的先知
現實秩序的壓迫和冒險精神的結合會導致“流亡”,流亡的終點是回家,或者重建家園。但是,如果無家可歸,或者無家可建,則就只能永遠流亡。
法蘭克福學派作為一個流亡的思想家團體,二戰結束后,紛紛修成“正果”,不再流亡:霍克海默爾任職大學校長,阿多諾是政府以及主流社會尊崇的學術權威,馬爾庫塞成為西方大學生心目中的偶像,弗羅姆已是心理學界的泰斗……真是個個功成名就。只有一個人例外,法蘭克福學派諸大家中最富有原創性思想的人物——瓦爾特·本雅明。1940年,他在逃亡途中,服毒自殺。雖然,已經搬遷至美國的法蘭克福研究所,急切地盼望他到來;雖然,在巴勒斯坦,希伯萊大學仍然在為他沒有赴任的教職提供薪水;雖然,他已經來到法國的邊境……但是,他卻用自己的手,將自己定格在“流亡”上。這是一件極富有象征意義的事件,對于他本人,對于20世紀的思想史,對于西方的文化文明,它包涵的意蘊,至今仍被人們評說。
疲憊的肉體生命不再流亡,但是他的思想,他的精神,猶如幽靈,在思想界,在學術界,在文化藝術界卻流亡游蕩至今,不時引發出一陣陣喧囂、一陣陣贊嘆,甚至一陣陣痙攣。20世紀逐漸離去,法蘭克福學派諸大家也似乎在逐漸淡出,走向謝幕,而只有他,愈見光彩熠熠。生前,他的影響僅限于一個個小小的精英圈子。唯一的謀生手段:寫作,甚至并不足以維持生存,他只得依賴法蘭克福研究所,以及遙遠的耶路撒冷的希伯萊大學所提供的津貼。而現在,他被稱為“先知”。從西方到東方,從學者到藝術家,從教授到大學生,人們閱讀他、談論他,從中汲取冒險流亡的思想、勇氣和力量。美國著名女哲學家蘇珊·桑塔格曾哀嘆到“自由知識分子是一個滅絕的物種”,而稱本雅明則是“歐洲最后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美國著名學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將其稱為“20世紀最偉大、最淵博的文學批評家”……
他的“流亡”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學術權力機構,思想流派的領地,社會制度、現實生活秩序,甚至親友圈子,似乎都無法完全容納他,迫使他在大大小小的領域邊緣徘徊、游蕩。或許,在心靈深處,在無意識中,他也根本不愿意因臣服而被收編、熔化、整合,因而失去思想鋒芒,失去智慧的沖撞力。
獲得博士學位后,他先后向海德堡大學、法蘭克福大學等申請教職,均以失敗而告終。其求職論文《德國悲苦劇的起源》,教授們評語:“一片泥沼,不知所云……”。有意思的是,幾十年后,此書又被學術界稱為20世紀文學批評的偉大經典。他試圖進入法蘭克福研究所,提交的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出發研究資本主義危機的論文《波德萊爾筆下的第二帝國》,阿多諾在回信中卻認為,本雅明根本沒有達到自己所認為的馬克思主義境界,在本雅明的文中“看不到全部社會進程的中介……只是膚淺的把一種揭示力量賦予一堆資料”。他的天才性的論著《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也被認為是認同了大眾文化,而遭到迎頭批評。同樣有意思的是,幾十年后,這部論著成為當代電影理論的經典。無論是他對波德萊爾的研究,還是對電影的研究,現在都公認是法蘭克福學派最重要的學術成果。而且,時代背景的變化,思想潮流的發展,無論是洛文塔爾,還是馬爾庫塞,甚至阿多諾,這些大眾文化最堅定的批判者,都或多或少地修正了自己的理論,向本雅明幾十年前就提出的思想靠攏,并且承認他的思想是更有智慧的。
他憎恨迫害猶太人的納粹政權,比其他法蘭克福學派成員更早就逃離德國,試圖在法國、丹麥、西班牙、意大利、美國、瑞士尋找避難所。可是他又是這些國家的民主制度的不妥協的批評者,是資本主義文化堅定的批判者,他的思想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大蕭條時期,西方文明似乎正在走向衰落,而當時的蘇聯似乎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于是,1926年他前往莫斯科,希望能找到光明,甚至準備定居蘇聯,為蘇聯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可是,到了蘇聯后,卻大失所望,這里也不是他的理想家園,蘇聯夢破滅了,不到一年就返回了巴黎。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發現蘇聯知識分子已經被納入了政治權力的體系中,已經失去了自由思想的勇氣和力量,這是他絕對無法贊同的。他對猶太教的哲學思想深感興趣,他的摯友猶太教神學家格雄·舒勒姆(1897-1982),他的妻子朵拉,都是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中堅,他也曾向往去巴勒斯坦。可是他最終沒有成行,連舒勒姆為他爭取到的在耶路撒冷的研究席位,他也一年一年地延宕,最后不了了之。或許,他認為以色列建國后的制度也不會好到哪里,也不一定能成為他的家園。
他有幾個好朋友:法蘭克福學派的旗手阿多諾,著名戲劇家布萊希特,神學家舒勒姆,德國著名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等等。他努力維護與他們的友誼,在這些強悍、盛氣凌人的朋友面前,他甚至顯得唯唯諾諾,即使被誤解也不辯解。一旦朋友有困難,他立刻“拔刀相助”。例如,當布萊希特的《三毛錢的小說》發表后,遭到評論界的圍剿,本雅明就挺身而出,稱贊這部作品表現出了極高的思想水準和罕見的諷刺力量,作者的反諷水平可以與尼采相提并論。而更有意思的是,他的這些朋友之間,則要么是死對頭,終身不解,要么從不來往。當本雅明與布萊希特交往,阿多諾奉勸本雅明要“懸崖勒馬”。他認為布萊希特是一個不入流的“粗俗的馬克思主義者”。舒勒姆甚至不客氣地揚言,本雅明再與布萊希特來往,不惜要割席斷交。上世紀50年代,阿多諾夫婦編選出版了《本雅明文選》,以及“書信集”。應該指出,正是因為這些書的出版,本雅明才真正具有了世界性的影響。而布洛赫讀后卻哀嘆“我的朋友又死了一次”。同為本雅明摯友的著名女哲學家、女權主義運動的旗手漢娜·阿倫特則義憤填膺地斥責阿多諾諸人為“惡人幫”。本雅明默默忍受,從容不迫地來往于這些朋友之間,用自己的智慧、思想幫助他們、啟發他們、豐富他們,同時又從這些朋友那里汲取力量與智慧。時光流逝,這些朋友們都痛感到本雅明的可貴。無論是布萊希特,還是阿多諾,當他們認真研讀了本雅明遺留下來的手稿,都認真反思了自己的思想和學術觀點,并且都加以了修正。
本雅明與異性之間似乎也在不停地流亡。他的初戀情人是他的一位高中同學的妹妹,叫尤拉,而且兩人還有了婚約。可是,1913年秋,本雅明在柏林一個研討會上,與朵拉相遇,朵拉是一名來自奧地利維也納的極富知識修養的猶太后裔。聰明漂亮的朵拉憑借著優雅的風度和得體的談吐一下子就深深吸引住了本雅明,朵拉對本雅明這位青年才俊也是一見傾心,兩人各自解除了之前的婚約,于1917年在柏林舉行了婚禮。婚后不久,感情就出現危機。而且,當本雅明又與尤拉相遇時,情感復燃,甚至,兩人一直保持情人關系直到1925年尤拉結婚。后來,本雅明將《論〈親和力〉》一文作為禮物獻給了尤拉。而與此同時,他的妻子朵拉也與本雅明的高中好友謝恩保持了一段時間的情人關系。兩人各自的不忠為這段婚姻的破滅埋下了伏筆。1924年春天,本雅明來到意大利風景如畫的卡普里島度假時遇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女人——來自蘇聯的女導演阿西亞·拉西斯。拉西斯年輕漂亮,身上洋溢著青春的朝氣。對于本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