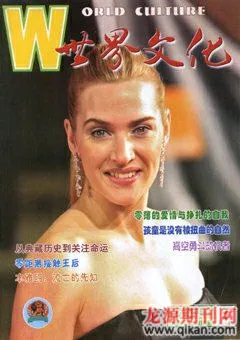《洛麗塔》:一只絢麗的彩蝶
蝴蝶情結(jié)
弗拉迪米爾·納博科夫(1899—1977),當代著名俄裔美籍作家,出生于俄國圣彼得堡一個貴族家庭,因有富裕的家境,他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3歲時,就可以用英文熟練表達,5歲時開始學習法文,到15歲時,他已經(jīng)閱讀了托爾斯泰的全部作品,并且用英文閱讀了莎士比亞的全部作品,用法文閱讀了福樓拜的全部作品,另外還有數(shù)百本其它書籍。7歲那年,他繼承父親收集蝴蝶標本的愛好開始著迷于捕蝶,終身不棄,以至在以后漫長的人生歲月里都與蝴蝶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從而形成了他文學創(chuàng)作中獨特的“蝴蝶美學”。
據(jù)納博科夫回憶,他對蝴蝶的迷戀源于父親遺傳給他的這種“鱗翅目感情和痛苦”,7歲那年夏天,幼小的納博科夫在父親的熏陶下開始走進蝴蝶那五彩繽紛的世界,很快就進入一種癡迷的狀態(tài),在僅僅一個月的時間里,他就熟悉了約20種普通類型的蝴蝶;8歲時,他就大量涉獵像《鱗翅目》,《新或罕見鱗翅目的歷史畫像》,《英國蝴蝶飛蛾自然史》,《歐洲鱗翅目大全》,《新英格蘭蝴蝶》等專業(yè)性的書籍,大開眼界,掌握了豐富的蝶類學知識,為他以后進行蝴蝶標本的采集,整理、歸類打下了堅實的基礎(chǔ);從9歲開始,他陸續(xù)把自己新發(fā)現(xiàn)的各種珍稀蝶類標本寄給“世界上所有時代最偉大的鱗翅目學家”;12歲時,他已經(jīng)“開始購買,珍藏稀有蝴蝶的標本,而且貪婪地閱讀俄語和英語的昆蟲學期刊”,對蝴蝶的敏感和迷戀,讓年幼的納博科夫有了大膽的設(shè)想:“似乎世界上再沒有什么東西對于我會更加甜蜜,勝過能夠憑著一次好運,給早經(jīng)別人命名的鳳蛾的漫長名單增加某些值得注意的新種類。” 1920年,納博科夫發(fā)表了第一篇學術(shù)論文——《論克里米亞蝴蝶》,是有關(guān)蝴蝶的。
1940年,納博科夫移居美國,初來美國的生活變化無常,而不變的是每年夏天,他都要攜妻帶子橫跨美洲大陸到洛基山去度假捕蝶。在來美的第二年,他當上了哈佛大學比較動物學博物館的兼職館員,專門從事鱗翅目的研究和分類工作。對蝴蝶的研究占用了他大量的時間,每天都要在顯微鏡下工作至少6小時,以致于后來損傷了視力,但納博科夫毫無怨言,而且樂在其中。他曾說:“哈佛博物館的歲月乃是我成年后的生活中最快樂最刺激的一段。”“ 愉快的難以置信的記憶事實上可以和我在俄國的童年相比。”一直到今天,我們?nèi)匀豢梢栽诠鸫髮W,康奈爾大學的比較動物學博物館以及一些科學院的陳列室內(nèi)看到納博科夫采集、捐贈的一些珍貴蝴蝶標本。
1952年,納博科夫采集到一種特殊的雄性蝴蝶,這種蝴蝶后來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把這種蝴蝶分為兩類,其中一類叫“多洛蕾絲”,英文是Dolores,是拉丁詞dolor派生而來的,意思是“悲傷痛苦”。1954年,他把這個從他的名字里孕育出來的“悲傷痛苦”的孩子寫進他的小說《洛麗塔》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就叫“多洛蕾絲”。這樣,一只美麗,靈動,炫目的蝴蝶就翩翩然飛入人們的視線。
《洛麗塔》中的蝴蝶美學意蘊
在《洛麗塔》的導(dǎo)言中,小阿爾弗雷德·阿佩爾說:“納博科夫的藝術(shù)記錄了一個永不停息的變的過程——藝術(shù)家通過藝術(shù)創(chuàng)造而帶來的自身成長——昆蟲的變形循環(huán)是納博科夫描述這個過程時起支配作用的比喻,因為他一生從事生物考察,在他的腦子里已確定了‘蝴蝶與自然界中心問題之間的聯(lián)系。’”由此可見,納博科夫的創(chuàng)作與蝴蝶確實有著割不斷的聯(lián)系,而他的藝術(shù)思想與蝴蝶的生活習性以及蝴蝶與自然界的關(guān)系密切相關(guān),正是他把這種特有的蝴蝶情結(jié)帶到了他的成名作《洛麗塔》里,從而形成了《洛麗塔》獨特的蝴蝶美學意蘊。
靈感
納博科夫認為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有一種“靈魂的震顫”,這就是“靈感”,在他的《文學講稿》一書中,他把靈感解釋成“狂喜”和“記憶”。“狂喜作為一種純粹的感情,它沒有有意識的目的,但是它在瓦解過去的舊世界和建立嶄新的新世界之間的連接上是最重要的”,藝術(shù)活動主要就是借助于這種充滿創(chuàng)造生機的“審美狂喜”來建構(gòu)完全新穎的可能世界,“審美狂喜”以其所帶來的巨大喜悅瓦解主體與客體,現(xiàn)象與本質(zhì),物質(zhì)與精神,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等之間的堅實的高墻,把藝術(shù)活動的主體帶進自由的天地。他還認為:“狂喜和記憶之間的差別主要是氣候上的,前一個是熱的,短暫的,后一個是冷的,持續(xù)不變的。……當時間成熟,作家安下心來編寫他的書,他會依靠第二種寧靜和始終不斷的靈感——“記憶”,這個可信賴的助手會幫助回憶并重建世界。”意思是說,當作家對某種事或物感到“狂喜”,也許這種狂喜只是短暫的一瞬,但它會變成“記憶”,當這種“記憶”與新的“狂喜”發(fā)生碰撞時,就會給你“靈感”,讓你去重建一個藝術(shù)世界。
納博科夫一生之所以靈感不斷,創(chuàng)作頗豐,跟捕蝶給他帶來的狂喜和記憶是分不開的,他在自傳性質(zhì)的文章《終結(jié)性的證詞》中寫道:“我在自然中找到了我在藝術(shù)中追尋的那種喜悅,兩者都有魔力般的形式,都有一種錯綜復(fù)雜的魅力與幻象。據(jù)我所知,很少有在情感欲望,野心或成就感等方面能超過對昆蟲學的探索的。”而《洛麗塔》一書就是上世紀50年代他在捕蝶的閑暇時間斷斷續(xù)續(xù)寫成的。納博科夫自己在談到這部小說的創(chuàng)作時說:“并無特殊目的,只是一種靈感的反應(yīng)或混合。”
他把捕蝶認為是“一種沒有時間限制的最高享受,一個隨機挑選的景點,我站在珍稀蝴蝶和它們喜愛的植物中間,這是一種狂喜,在這種狂喜背后還有更多的但卻是難以言述的東西,就像一瞬間我所喜愛的東西突然襲來,感到天地合一,一種對人類命運對位的精神或者對溫和的幽靈嘲笑幸運的生物感激的震憾。”小說中亨伯特對洛麗塔那種如癡如醉的迷戀和狂喜似乎可以看作是蝴蝶情結(jié)帶給《洛麗塔》的又一種影響。
偽裝
偽裝是蝴蝶生存的本能,關(guān)于蝴蝶的偽裝,納博科夫有大段的描述:“摹擬之謎對我有一種特殊的魅力。其現(xiàn)象展現(xiàn)出通常聯(lián)系著人造事物的一種藝術(shù)的完美。……當一只蝴蝶不得不像一片樹葉時,不但一片樹葉的所有細部都被美麗地呈現(xiàn)出來。而且還慷慨奉送模仿蛆蟲所鉆的洞孔的斑點。‘自然選擇’,在達爾文式的意義上,無法解釋摹仿特征與摹仿行為的奇跡般的巧合,人們也無法訴諸‘生存競爭’的理論,在一種防衛(wèi)器官被推至摹仿的精微,繁盛以及奢華的一個極點,遠遠超出了一種食肉動物的鑒賞力的時候,我在自然之中找到了我在藝術(shù)中尋求的非功利性的快樂。兩者都是魔法的一種形式,兩者都是一個奧妙的巫術(shù)與欺騙的游戲。”“保護色”的蝶類它們有與棲息環(huán)境相似的顏色,形態(tài),像枯葉蝶,不僅狀如枯葉,而且還有蟲咬或發(fā)霉的斑紋,讓捕捉者難以辨認;而“警戒色”的蝶類則摹擬有毒蝴蝶的色彩和飛翔的姿態(tài)來迷惑捕捉者,所以納博科夫坦率地說:“騙術(shù)最高的應(yīng)首推大自然,從簡單的借物力進行繁殖的伎倆到蝴蝶、鳥兒的各種巧妙的保護色,都可窺見大自然無窮的神機妙算。”對鱗翅目的研究使納博科夫深諳蝶類的這些變幻“伎倆”,當然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他的創(chuàng)作。阿佩爾說:“納博科夫?qū)H象棋、語言和鱗翅目昆蟲學的酷愛,促使他在作品里采用紛繁纏繞的模式。”《洛麗塔》創(chuàng)作的虛構(gòu)性,文本的迷惑性則是蝴蝶偽裝特性對他創(chuàng)作的影響的突出表現(xiàn)。
納博科夫給文學下過一個定義:“一個孩子從山谷里跑出來,大叫‘狼來了’,背后果然緊跟著一只大灰狼——這不成其為文學,孩子大叫‘狼來了’而背后并沒有狼,這才是文學。”“藝術(shù)的魔力在于孩子有意捏造出來的那只狼身上,也就是對狼的幻覺,雖然孩子最終可能被狼吃掉,但孩子是當之無愧的最初的作家。”所以就這點來看,納博科夫認為“偉大的作家都是大騙子”“所有的小說都是虛構(gòu)的,所有的藝術(shù)都是騙術(shù)”。1962年7月在接受英國BBC電臺采訪時,納博科夫說:“洛麗塔沒有任何原型,她誕生于我的頭腦,此人從未存在過,……洛麗塔是想象的產(chǎn)物。”
其實不光是洛麗塔這個“性感少女”,整個創(chuàng)作都是虛構(gòu)的。《洛麗塔》表面上看是一部自傳體小說,但其敘述剛剛開始就已經(jīng)暗示了作品的虛構(gòu)性。作者在前言中告訴我們:《洛麗塔》是一個鰥夫的懺悔,是對自己罪行的供認。《洛麗塔》的作者亨伯特先生以及他的敘述中的主要人物洛麗塔都已經(jīng)死亡,這明顯是在告訴我們:這些文字死無對證。接著,我們跟隨亨伯特先生的自述走進《洛麗塔》的情節(jié)之中,卻馬上發(fā)現(xiàn)亨伯特是一個曾多次接受精神治療的瘋子。在供述中他多次發(fā)誓他的回憶是真實的,但是這相當于建筑在流沙上的碉堡,堅不可摧卻瞬間顛覆,讀者會相信嗎?只有傻瓜才會相信這樣一個瘋子對自己往事回憶的真實性。而創(chuàng)造這一切的納博科夫是不是在告訴我們:這所有的所有都是虛構(gòu)的?
藝術(shù)從來不是簡單的,最偉大的藝術(shù)具有異常的復(fù)雜性和迷惑性。納博科夫說:“《洛麗塔》就像編寫了一個美好的謎,其結(jié)構(gòu)和謎底在于你怎樣去看待它,”正如作者說的一樣,走進《洛麗塔》就仿佛走進了一個色彩斑斕、變幻莫測的世界,身邊涌過的一切都似真似幻,魔術(shù)的語言,巧合的情節(jié),變換的人物,這就是納博科夫的藝術(shù)魅力。
在《洛麗塔》的前言中出現(xiàn)了一個看似并不重要的人物,維維安·達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