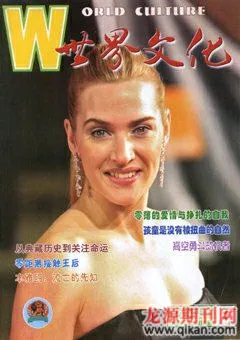紐約地鐵
紐約的地鐵是一座地下迷宮。
每天我的游程都是從地鐵開始,又從地鐵結(jié)束,一張杏黃色的小小METRO CARD成了我進(jìn)進(jìn)出出地下迷宮的通行證,地鐵真是紐約多快好省的交通工具!在美國(guó)生活不能沒有私家車,但在紐約可以省略,不少有車族都是出城才開車,市內(nèi)的交通全靠地鐵!即使你第一次獨(dú)闖紐約,舉目無親,也不用心存疑慮問東問西,到處打探景點(diǎn)離你有多遠(yuǎn),什么時(shí)代廣場(chǎng),洛克菲勒中心,大都會(huì)博物館,蘇荷,格林威治村,乘船去自由女神南碼頭,它們?nèi)诘罔F站的出口處等著你呢!有了地鐵,這個(gè)不欺生的“鐵哥們”,你可以氣定神閑假裝熟門熟路地走著瞧。特別是看到大街上擁堵的車流,更是慶幸“鐵哥們”的通達(dá)。
地鐵車站里沒有白天和黑夜,沒有陽光和雨水,卻有一股強(qiáng)大的地氣。在冬天,它是一股溫?zé)岬呐鳒卮嬷悖辉谙募荆闪藧灍岬某睗裾吵碇恪V挥袩艄馑募就鳎o你援助和信心,你無畏而又無奈地走在這個(gè)鋼鐵怪獸的胸膛里。
乘地鐵可是多數(shù)紐約市民每天早晚必做的功課。而我每天必乘的是地鐵7號(hào)線,它在地鐵圖上的標(biāo)識(shí)是一條東西方向輕盈伸展的紫線,坐在晃動(dòng)的車廂里,虛構(gòu)著自己是順著紫線優(yōu)美的弧度從皇后區(qū)滑向了曼哈頓。事實(shí)上,我常常要換地鐵才能到達(dá)想去的地方。比如去蘇荷或者小意大利,就要在中央大車站換乘6號(hào)線。
換乘地鐵的經(jīng)歷就是迷宮游走的經(jīng)歷。在十幾條線路交匯的中轉(zhuǎn)站,上上下下的扶梯組成了意義不同的循環(huán):不同的線路、不同的標(biāo)識(shí)、不同膚色的人流,奔向不同的目的地。我循著彩色箭頭的標(biāo)記,跟蹤追擊,記不清上上下下了幾個(gè)樓層,也不知道中轉(zhuǎn)最多的站臺(tái)最多有幾層,直到跨進(jìn)一節(jié)車廂,加入一個(gè)無須相約的短暫旅程。
在三五分鐘,或半個(gè)小時(shí)的行程中,你不要幻想浪漫和奇遇,幻想赫本遇到了派克,上演一部紐約版的《羅馬假日》。不至于,我們不是兵馬俑,但我們都是陌生人,使用最多的語詞是SORRY。當(dāng)然只要你不是閉上眼睛假寐,總有什么會(huì)滑入你的眼簾,撩起你的思緒。阿拉伯人包著深色頭巾想心事,印度人披著艷麗的頭巾在車廂里很醒目,黑人女孩的眼睛特別明亮,滿頭用五彩斑斕的頭繩扎出的小辮……多數(shù)人是沉默的,不同膚色的手,捏著不同文字的報(bào)紙埋頭閱讀是車廂里最日常的景象。
世界各地的人分享著一個(gè)個(gè)小小的車廂,紐約的地鐵,國(guó)際化的車廂,就是一個(gè)什錦糖的糖罐,看不見的手,看不見的力量把我們糅和在一起。偶爾會(huì)碰上一個(gè)不請(qǐng)自來的演講客,一通義正辭嚴(yán)的演說后,因無人應(yīng)對(duì)又悄然下車了,有時(shí)也會(huì)上來一個(gè)小提琴手,沉悶的車廂里一下子琴聲如訴……看來車廂又像是一個(gè)流動(dòng)的舞臺(tái),上演著沒有編劇,誰也捉摸不定的塵世連續(xù)劇。
有一次在回程的車廂里,我不知道是哪一站,車廂門打開,一陣溫柔而沙啞的歌聲驚醒了我疲憊的身心,我四下張望,還是沒有發(fā)現(xiàn)歌者,地鐵已經(jīng)啟動(dòng),轟鳴聲淹沒了一切,歌聲消失得無影無蹤,像是我的幻覺。對(duì)于人生的瞬間,溫暖的,寒冷的,乏味的,苦澀的,有情的,甜美的,我們無從把握,只能承受,體驗(yàn)痛并快樂著的過程,因?yàn)槲覀冊(cè)诼飞稀?br/> 我坐過站了,下車,站在空蕩蕩的站臺(tái)上重新等車。粗壯的雨水從黑暗的空中灑下來:我在哪兒?我怎么會(huì)站在被雨水圍困的站臺(tái)上,寂靜中龐德的《地下鐵車站》從記憶的空中飄灑下來,淅淅瀝瀝地成了我等待地鐵的旁白:
“人潮中那些面容的影子,潮濕黑暗樹枝上的花瓣。”
走在黑暗的雨水中,陪伴我的是詩(shī)中的花瓣,家太遙遠(yuǎn)了,只有旅館的燈光等待著我。
午夜過后的地鐵仿佛換了一張臉,會(huì)有讓警察防不勝防的骯臟交易,也會(huì)有讓市民頭疼的地鐵涂鴉客的午夜大行動(dòng):他們帶著手電、梯子、油漆和噴槍,對(duì)著墻壁、車廂,對(duì)著地下迷宮的各個(gè)部位,對(duì)著紐約人的視覺,噴射他們被這個(gè)功利城市擠碎的白日夢(mèng)。
據(jù)稱,紐約市政府每年要撥出8位數(shù)的預(yù)算來清洗這些涂鴉之作。吊詭的是《新聞周刊》又有報(bào)道稱:地下鐵涂鴉代表作“飛行的電視機(jī)”的售價(jià)已達(dá)2萬美金,作畫者吉斯·黑林也因此一舉成名,他創(chuàng)作的卡通形象如“飛行的鐘表”、“祈禱的人”、“搏動(dòng)的金字塔”等贏得了紐約人的青睞。黑林不失時(shí)機(jī)地開起了POPSHOP,專賣各式新潮的文化衫,于是他的多種“涂鴉”形象便隨著高矮胖瘦不一的身軀在紐約的街頭漫游。
離開紐約的前兩天,想去世貿(mào)遺址看看,翻開地圖一查,離世貿(mào)最近的地鐵站點(diǎn)標(biāo)有灰色的箭頭,旁邊注明“9·11”之后暫時(shí)關(guān)閉,只能改乘離世貿(mào)最近的5號(hào)線。幾十個(gè)月過去了,它們依然關(guān)閉著,這是紐約捂不住的傷口。
地鐵進(jìn)站了,越來越近,巨大的轟鳴聲中仿佛站臺(tái)和鐵軌一起顫動(dòng),這是紐約地鐵的典型性格,最貼切的注解是:“大地在顫抖,仿佛天空在燃燒。”
紐約的地鐵已有百年的歷史了,可它依然精力充沛日夜奔忙,歲歲年年世界各地的人都帶著自己的欲望和氣息走進(jìn)車廂,它是夢(mèng)想的載體,一個(gè)有著呼吸的鋼鐵怪獸;它是這座城市的精靈,是紐約的血管,也是紐約記憶的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