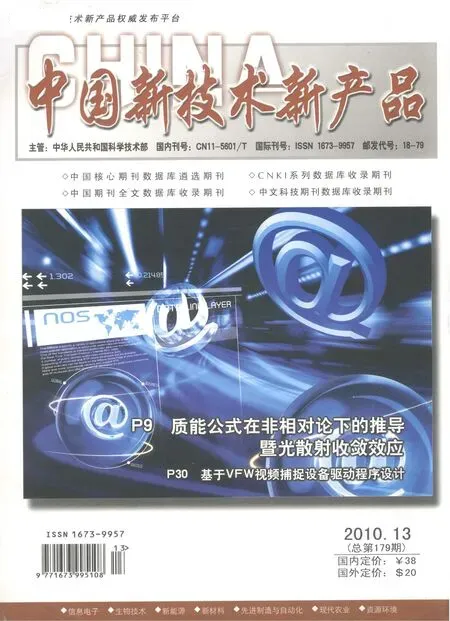城市轉(zhuǎn)型中“城中村”的現(xiàn)狀與未來
薛文選
(鄭州市綠化工程管理處,河南 鄭州 450006)
1 “城中村”的界定
“城中村”是指改革開放以來,在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的地區(qū)和城市,由于疾風(fēng)驟雨式的城市建設(shè)和城市化進(jìn)程加快,城市用地急劇膨脹,將以前城市周邊的村落及其耕地納入城市用地范圍。村落集體土地已基本被城市建設(shè)所征用,變?yōu)閲型恋兀谡鞯剡^程中返還給鄉(xiāng)村的用地和以前的村民住宅用地等則維持集體所有制性質(zhì)不變,在這些用地上以居住功能為主形成的社區(qū)被稱作“城中村”。
2 “城中村”的人居現(xiàn)狀
2.1 用地與人口性質(zhì)
在《城市用地分類與規(guī)劃建設(shè)用地標(biāo)準(zhǔn)》中沒有對這類用地的性質(zhì)進(jìn)行專門的界定。居住在該地區(qū)的居民,即能享受到城市居民所得到的服務(wù)設(shè)施,又能在擺脫傳統(tǒng)“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nóng)村生活方式后,還享有國家賦予農(nóng)民占地建房等特殊政策。傳統(tǒng)的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所帶來的農(nóng)業(yè)和非農(nóng)人口之間的區(qū)別在此蕩然無存,城市總體規(guī)劃中計(jì)算城市人口時又難以對此加以統(tǒng)計(jì),村鎮(zhèn)用地、人口性質(zhì)和規(guī)模難以確定。
2.2 生活在“城中村”的居民
“城中村”的出租屋是在農(nóng)民的宅基地上建立起來的,本不能用來作商業(yè)出租,但農(nóng)民建房用以出租由來已久,各級政府只能接受這個既成事實(shí)。在城市高速發(fā)展的過程中,原住民們走上了一條依賴房屋和土地出租的致富之路,村民通過建私房收租金和集體分紅,過著衣食無憂的富足日子,形成一個名副其實(shí)的“食利階層”。
第二、三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和廉價出租屋帶來大量外來流動人口,使得村莊內(nèi)人口構(gòu)成復(fù)雜,相應(yīng)產(chǎn)生諸多社會問題。
2.3 “城中村”的人居環(huán)境
2.3.1 空間形態(tài)與內(nèi)部功能和周邊環(huán)境反差較大
快速城市化的地區(qū),村莊內(nèi)部用地凸顯功能紊亂現(xiàn)象,居住用地、工業(yè)用地、商業(yè)用地等相互交織;建筑物及建筑景觀雜亂無序,建筑密度高達(dá)60-80%,村民建房一般建至3-8層,通風(fēng)、采光等居住條件差,居住生活的私密性得不到保障。
“城中村”的規(guī)劃、建設(shè)、管理極其混亂,外來人口膨脹,出租屋成為黃賭毒的溫床,“超生游擊隊(duì)”的藏身之所。這些和現(xiàn)代城市的整潔與舒適大相徑庭。基礎(chǔ)設(shè)施嚴(yán)重缺乏,道路狹窄曲折、不成系統(tǒng),無法滿足人流、停車和消防的基本要求。樓間污水橫流、垃圾遍地,排水設(shè)施不合理導(dǎo)致經(jīng)常內(nèi)澇。學(xué)校、幼兒園、醫(yī)療衛(wèi)生等公共服務(wù)設(shè)施的數(shù)量和質(zhì)量都嚴(yán)重滯后,難以滿足生活的需要。
2.3.2 “城中村”的防災(zāi)隱患
“城中村”現(xiàn)有樓房大都沒有經(jīng)過設(shè)計(jì),沒有加固就隨意加高(某些城中村甚至將磚混結(jié)構(gòu)的房子建至12層),極易發(fā)生傾覆坍塌。樓與樓之間距離很近,一旦發(fā)生火災(zāi)、地震,很有可能造成“火燒連營”和“倒一間、砸一片”等群死群傷的嚴(yán)重后果。以鄭州市中心區(qū)內(nèi)的“城中村”為例,這些“城中村”大都沒有消防通道,消防水源不足,防火間距不夠。
3 改造“城中村”,實(shí)現(xiàn)其合理城市化
3.1 “城中村”改造的意義
“城中村”已成為我國城市化發(fā)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城市化發(fā)展戰(zhàn)略順利實(shí)施的關(guān)鍵所在。改造“城中村”不僅有利于合理利用城市土地資源,優(yōu)化城市空間形態(tài),落實(shí)城市總體規(guī)劃,而且有利于改善人民群眾的居住環(huán)境,提升城市總體形象,加快城市化進(jìn)程,保障群眾同享城市改革發(fā)展和文明進(jìn)步成果。
3.2 “城中村”改造的思路
“城中村”的改造不僅意味著搬遷和翻建,而且意味著產(chǎn)權(quán)的重新界定和村落社會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的重組。另外,“城中村”為大量城市外來勞動力提供了廉價的住所,降低了勞動力成本,從某種意義上說,雜亂的“城中村”支撐著現(xiàn)代都市的繁榮。對“城中村”的改造可能會影響所在城市的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
“城中村”改造對于城市化管理者而言是一個必須面對的現(xiàn)實(shí)問題,但又沒有一個現(xiàn)成的可以照搬照抄的模式。從純粹改造開發(fā)的角度看,似乎問題很簡單,要改變“城中村”為人們所詬病的建筑“超強(qiáng)密度”和混亂無序狀態(tài),無非是開發(fā)高度空間來替代低度空間的擁擠。但在“城中村”改造的博弈中,存在著三方對弈者:政府、房地產(chǎn)商和“村民”。最終改造方案,將是使這三方利益達(dá)到平衡:“村民”們的要求是在改造中保護(hù)他們的租金收益;房地產(chǎn)商的要求是在投資改造中至少獲得平均收益;而政府的希求是避免財(cái)政的壓力和保證市場、社會的穩(wěn)定。
政府的擔(dān)憂是,拆遷過程中的利益沖突會成為社會不穩(wěn)定的因素,政府自己開發(fā)因成本過于高昂難以啟動;房地產(chǎn)商的擔(dān)憂是,此種拆遷開發(fā)中的利益矛盾重重,不確定的變數(shù)很多,高昂的交易成本會消散房地產(chǎn)開發(fā)的正常收益,政府對容積率和建筑密度的管制會使開發(fā)最終變得無利可圖;“村民”們的擔(dān)憂是,他們既得的房地產(chǎn)租金收益在開發(fā)中得不到保護(hù),而且會損失市中心區(qū)域房地產(chǎn)升值前景的好處。在這種情況下,“城中村”改造的真正難點(diǎn),就是改造的資金的來源。
3.3 可供借鑒的三種模式
每個城市都有符合自身實(shí)際的改造模式,有三種改造模式比較現(xiàn)實(shí):
開發(fā)商投資改造的模式
開發(fā)商自籌資金,按有關(guān)規(guī)定先對所有被拆遷業(yè)主進(jìn)行補(bǔ)償安置,所開發(fā)的商品房進(jìn)入市場競爭經(jīng)營。這種模式緩解了政府大規(guī)模資金投入的壓力,不需村民及村集體再投入改造資金,規(guī)避了投資風(fēng)險(xiǎn)。
2006年3月,由河南升龍置業(yè)有限公司投資的鄭州市燕莊城中村改造拆遷工程正式啟動,燕莊改造成的“鄭州曼哈頓廣場”目前已成為鄭州市的新地標(biāo)。隨后,升龍公司相繼投資開展了小李莊、崗劉、鳳凰臺、齊禮閻等幾處城中村改造項(xiàng)目。鄭州市目前開展的城中村的改造工程均屬于開發(fā)商投資改造模式。
開發(fā)商與村集體、村民合作改造的模式。村集體、村民的積極參與,可以有效地減少拆遷的難度,而開發(fā)商的加入,又解決了村民與村集體改造資金的問題,村集體、村民的利益也得到了保障。
集體組織和村民自己改造的模式。深圳市漁民村創(chuàng)造出了獨(dú)特的“村股份公司自己組織改造、村民自籌資金的改造模式”。由村股份公司組織改造,避免了房地產(chǎn)公司為經(jīng)營利潤而高強(qiáng)度、高密度地開發(fā),違背改造本意和影響村民利益。改造完成的漁民村目前已成為了“城中村”成功改造的榜樣之一。
另據(jù)《經(jīng)濟(jì)時報(bào)》報(bào)道,“公寓式出租屋亮相廣州”。在城中村部分房屋更新時說服屋主聯(lián)合起來,連片拆建為公寓式出租屋。這種公寓式出租屋的出現(xiàn),使“集體組織和村民自己改造模式”更具可操作性,可能為“城中村”的改造開辟出一條新路。
4 “城中村”的未來之路
一個由親緣、地緣、鄉(xiāng)規(guī)民約等社會網(wǎng)絡(luò)聯(lián)結(jié)的村落鄉(xiāng)土社會,其終結(jié)不是農(nóng)轉(zhuǎn)非和工業(yè)化就能解決的。“城中村”改造過程,充滿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改造“城中村”,使主體村民最終在文化層面上城市化,以及在“城中村”這個混雜的社區(qū)群落中實(shí)現(xiàn)文化融合,并最終形成和諧健康的城市文明社區(qū),從而實(shí)現(xiàn)合理的城市化,是“城中村”的未來之路。
[1]李培林.改造“城中村”的邏輯:政策和產(chǎn)權(quán)置換資金[N].湘聲報(bào).2005.7.
[2]王華春,唐任伍,陸勁.“城中村”問題的制度成因及治理思路—城市土地資源優(yōu)化配置的重要環(huán)節(jié)[J].寧夏社會科學(xué),2005.06.
[3]楊爽,周曉唯.“城中村”改造中制度安排的選擇[J].重慶工商大學(xué)學(xué)報(bào)(西部經(jīng)濟(jì)論壇),20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