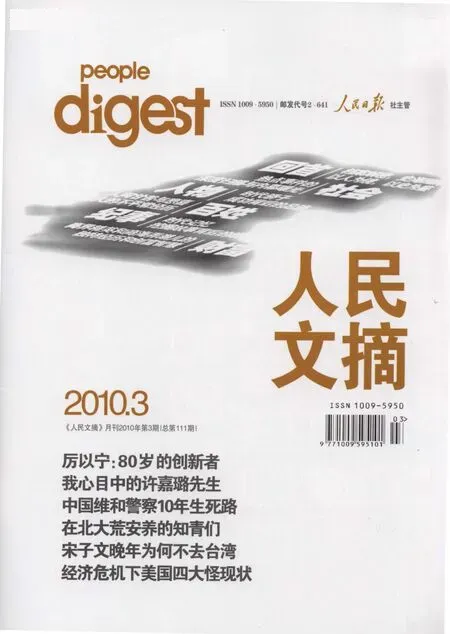我心目中的許嘉璐先生
◎陸昕

大約在上世紀60年代初,許嘉璐先生常到我家來。當時他是北師大中文系的青年教師,三十歲出頭,住校內。祖父陸宗達是語言教研室主任,居城南琉璃廠。系里或教研室有什么事,都是許先生來。后來又發展到他時不時來家中學《說文解字》,師生相處十分融洽。即便在“文革”爆發且在“史無前例”地進行時期,他也常到家里來。他來后便與祖父久久交談,經常一連幾個小時。然后從書桌挪到飯桌,談話的“家常便飯”變成真正的家常便飯。祖父吃飯時必得喝酒,而喝酒最怕的是一人喝悶酒。這個遺憾很快就由許先生填補了。記憶中,每當許先生來,家中便總有歡聲笑語。
50年代時,古代漢語算作過時的封建時代的那套學問,在全面向蘇聯學習的狂熱中,一些古代文化的課被砍掉,祖父自然“失業”了,于是改行去教現代漢語,還帶出了一屆現代漢語研究生。那時有多少青年人不愿追隨時代當弄潮兒,而去學無用的腐朽的“八股”?而50年代后期畢業留校的許先生卻選擇并愛上了這門被視為“枯燥”的學問。五六十年代,他便從祖父習《說文》、訓詁,從未中輟。“文革”形勢剛剛有所緩解,祖父從師大山西臨汾干校奉調回京,每日到師大化學系的《新華字典》編寫組上班,許先生一星期便有兩個上午去詞典組,在一間小屋里從祖父“偷學”《說文》。周末,又常來家里討教。記得某次祖父吃飯時說:“嘉璐不錯,現在這種時候還跑來跟我學《說文》。”水滴石穿,終成方家。正如祖父對他的評價“嘉璐這個人,聰明,天分高,肯用功。”
許先生多才藝,這也是他與人容易溝通的原因。記得這樣一件事,80年代初,卓別林的電影風行一時,有部電影名叫《舞臺生涯》,里面有這樣幾句臺詞:“黃昏時的暮色像夢一般美,天空中彌漫著丁香花的氣息……”我那時正當青年,尚未婚娶,因此滿腦子玫瑰色的浪漫,對這兩句話非常喜愛。有次我到許先生家給祖父辦事,閑談中提到這部電影,我就把這幾句臺詞背了出來,并說翻譯家潘耀華翻得真好。許先生笑道:“那是我寫的。”細問,原來潘耀華也住北師大,他每譯一部卓別林的電影都要請許先生潤色修改。
祖父好吃,是美食家,這一方面是人的天性,另一方面是由祖父的老師黃侃所傳。由此,祖父“文革”前就經常帶許先生下館子,邊吃邊聊邊談學問。印象最深的是這樣一件事,黃侃先生的侄子、武漢大學教授黃焯先生來京,與祖父和祖父老友趙元方先生聚會。大家先去照相,照相館在樓上,而趙先生腿腳不利落,正當為難之際,許先生自告奮勇,和司機小申輪流將趙先生背上背下,完成了老人們的一樁心愿。然后大家來到菜市口的“美味齋”聚餐,又是照此辦理。
祖父去外地開會,許先生經常陪同,有時他也給我講一些陪祖父去外地開會時發生的趣事。有年冬天他陪祖父去武漢開會,他說:“到飯店把爺爺安頓好,我又出去辦住宿登記。回來一看,二百八十歲的老頭正幫爺爺找棉褲。”世間哪有二百八十歲的老頭?他解釋說:“有四位老先生去看爺爺,都已七十多歲,合起來不是二百八嗎?”結果四個人到處找也找不到棉褲,他了解爺爺,往爺爺腿上一摸,說:“您不是正穿著嗎?”
有段時間祖父不在家,被“專政”住進“牛棚”。許先生雖然也自顧不暇,但還隔三差五來家看我祖母。有一次我從外地回家,看見他手里拿了兩包油紙包裹細麻繩捆扎的點心,正和祖母來回推讓。只聽他說:“老師不在,做學生的應該。”
祖父去干校后,每月送工資都是許先生來。祖父回來后,除去與許先生論文治學,文稿的出版、交涉,稿費的支取、收領,書籍的拿取、郵寄也主要是他奔走。除去這些,許先生還幫我們收拾藏書。祖父藏書豐富,雖經“浩劫”,殘存倒也不少,但皆七零八落,狼藉于各處。祖父雖有心收拾,但已力不從心,這副擔子自然也落在許先生身上。第一次整理時是個溫煦的秋日,他帶著我在北房的廊下整書。線裝書的書名、卷次全標在書根,彎腰撿看十分費力。這時他過來教我,說:“你看,像我這樣,把一種書的首頁翻開,露出書名,然后你把撿到的同一種書都先放到這書下邊,最后再給這套書順前后,看看是全的還是殘的。”就這樣,那次我們干了一整天。以后又收拾過幾次。“先生有事,弟子服其勞,”這話在許先生那兒算應驗了。祖父最后的那段日子,是在友誼醫院度過的。許先生時任中文系主任,自然又是少不了操持。想起那些點點滴滴的往事,實在令人難忘。
這些年里,每當我從書刊上、報紙上、電視里或是電話和相見中,看到、聽到許先生講述他的學術生涯、治學途徑、人生道路的時候,他都會一再提到、回顧我祖父對他的影響和教誨。其實,一個人的一生,名師的教誨固然是重要的,然而,路畢竟是自己走出來的。前幾年,香港鳳凰電視臺錄制了對許先生的訪談節目,主持人吳小莉問許先生,您現在有這么多職銜,最看重哪一個?答曰:“先生。”在許先生看來,做一個讓人愛戴的教師不容易,因此也是無上的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