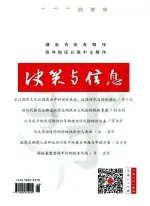國債危機關系多國生死存亡
文/丁雨晴 魏萊
一場規模空前的“國家債務危機”從希臘向整個歐洲迅速蔓延,即使連美國這樣的世界最大債務國也有些心慌意亂。二戰后,發行國債曾幫很多國家發展了經濟,但最近10年很多國家的國債越發越濫,世界上不欠債的政府已經不多。西方的問題尤其嚴重,在經濟不景氣、稅源有限的情況下,很多國家的政府為了討好選民,繼續舉債謀求福利、刺激經濟發展,根本無心償還前屆政府留下的債務。甚至有人擔心,如果西方經濟持續萎縮,像美國這樣的大規模債務很可能成為“永遠的爛賬”。清華大學國際經濟問題專家說“世界需要一次全球性的金融監管制度改革和快速的經濟增長,只有這樣,各國的債務危機才有可能得以緩解。”
多國陷入“國家債務危機”
作為一種債權融資方式,發行國債本身無可非議,是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的一種國際上通行的融資手段。最早發行國債是為了戰爭目的,如早在中國戰國時代,周天子討伐秦國,就曾向商人借貸。俄羅斯在亞歷山大一世統治時期還專門立法,規定國家在國債方面的義務。俄國第一筆外債是1769年與荷蘭銀行家簽署的,期限10年,年息5%。之所以需要這筆外債,是因為當時沙皇俄國在地中海的艦隊和向波蘭擴張需要一大筆開銷。在西方,歐洲近代歷次大規模戰爭,參與國多發行國債籌措軍費。二戰后,隨著經濟的發展,政府開支擴大,各種以平衡赤字或基礎建設為目的的國債大量涌現,在發達國家中幾乎沒有零外債的,而且加拿大、希臘、日本等國國債負債率超過了GDP總值。也有一些國家把“無債一身輕”當作自豪,中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既無外債也無內債”。時至今日,也有一些非洲和獨聯體的小國因為政府開支小,沒有發行國債。此外,像索馬里等戰亂國家根本無債可借。
如果國家政府管理不當,國家舉債過度,也會引發“國家債務危機”。第一個吃了國債大虧的事例出現在阿根廷。2001年阿根廷由于匯改失敗,巨額國債一下崩盤,導致經濟受到毀滅性打擊。有阿根廷人當時悲哀地稱,這是“有史以來第一個從發達國家發展成發展中國家的國家”。北歐國家冰島由于大規模舉債,而所獲資金又大量投入虛擬經濟,在2008年金融泡沫破滅后,幾乎成為“第一個破產的西方政府”,最終導致政權更迭。
不僅如此,在希臘2009年年底出現債務危機后,國際三大評級機構將希臘的長期主權信貸評級下調一檔,從“A-”降為“BBB+”。持續蔓延和惡化的主權債務危機,不但使這些國家面臨由于失業人數劇增導致的社會危機風險加大,還有可能影響到國內政治穩定和國家間關系發展。面對“瀕臨毀滅邊緣的雅典”,意欲出手施救的德國也陷入兩難境地。
這些年受國債困擾的國家還有很多。截至2009年底,烏克蘭外債規模已經達到1000億美元,約占當前GDP的80%~90%,已經遠遠超過了警戒線,造成國家經濟不穩。靠著能源交易所得,俄羅斯償還了大量國債,標志著這個大國正在恢復元氣。但據俄《商業咨詢日報》2009年12月21日報道,俄外債形勢仍不容樂觀,到當年10月外債總額仍有4782億美元。俄經濟學家謝爾蓋耶夫表示,俄政府加大國債的發行規模主要是為了減輕對儲備基金的依賴。國債還有內債和外債之分,按照俄羅斯的財政規定,內外債要各占50%才可以。而在絕大多數國家,國債都是“欠”本國百姓的占了多數。
日本在戰后初期一度厲行“零赤字國債”,但從1965年起,日本央行開始再度發行“赤字國債”,此舉曾在日本內需疲軟、稅源枯竭的經濟背景下救了國家,但也因國債負擔積重難返引發了新的問題。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特別研究員富田俊基在2000年就曾經警告說,在老齡化負擔沉重且難以增稅的條件下,不謹慎地亂發國債不僅“政策作用有限”,負債和利息的累積壓力反而將使財政更加脆弱。日本關西大學教授宮本勝浩還對日本去年年底發行大量國債進行了猛烈抨擊,他認為,政府在沒有具體償債計劃的前提下毫無節制地發行赤字國債無疑是“亡國行為”,將使不堪重負的日本財政狀況雪上加霜。日本的國家債務年年攀升,在各發達國家中遙居首位。宮本勝浩擔心,日本鬧不好會出現像2001年阿根廷陷入無法償還債務的情況,這樣的話,國債就會變成廢紙,日本將信譽掃地。據日本一家商業機構分析,由于利率低和償還能力差,日本長期和中期國債的信用評級已跌落谷底,在發達國家當中排名末位。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數據顯示,2009年公共債務在日本GDP中所占比重已經高達218.6%,成為工業國家中政府負債率最高的一個。日本新首相菅直人6月12日在日本國會發表講話時警告說,日本正面臨希臘式的債務危機,如果繼續過度依賴國債不進行改革,將有破產的可能。
韓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也吃過國債的苦頭,因此對歐洲國家近期的債務危機十分關注。韓國《亞細亞經濟》、YTN電視臺等媒體紛紛公布了三星經濟研究所的一份“國家債務再研究報告”。該報告稱,最近葡萄牙、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等歐洲國家的債務危機正在蔓延成為全球危機,世界經濟格局進入“不尋常狀態”。同樣的危機也可能在韓國出現,韓國政府應提前采取措施,提高國家信用度,預防可能發生的危機,否則2040年時韓國債務可能占到GDP的92%,最終制約韓國經濟增長,甚至帶來債務危機和財政危機。

最大債務國讓世界最不放心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世界上債務最為嚴重的國家是日本和英國,而美國是最大的債務國。據美國國會預算委員會透露,美國將永遠無法再次取得預算平衡。對此,英國《金融時報》評論文章說:“這不禁使人們再次想起美前財政部長薩默斯提出的那個令人啞口無言的難題:‘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能夠在多長時期內保持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地位?’起源于西方文明誕生地希臘的財政危機,很快將越過海峽抵達大不列顛。但關鍵問題是什么時候危機將波及位于大西洋彼岸的西方強國堡壘呢?”
美國《評論信使報》在評論當今世界的國債危機時說:“早在200多年前,亞當·斯密就已預見了當今的國家主權債務危機。國債日益上升的風險在世界經濟歷史上一再上演。斯密早就窺見了它的到來。一言以蔽之,無論是共和國、帝國,還是任何有史以來的國家的衰落都如出一轍:他們的消費嚴重超支。”對于“美國國債已經累計12.4萬億美元,很快就將相當于其GDP總量”,而奧巴馬為期10年的預算計劃將為美國再新增10.634萬億美元債務的預測,該報認為,如果美國債務等級持續下滑,美國國防能力將遭到破壞,其他國家將尋求在世界舞臺上排擠掉已經衰敗的美國巨人,“在這種意義上,不斷飆升的美國國債將危及美國國家安全”,而繼續縱容債務膨脹將肯定使美國遭遇衰敗和戰爭。
1989年美國國債僅2.7萬億美元,20年后接近11萬億,且在正常年份每天還以35億美元左右的速度增長。對此,有中國學者擔心,美國國債將成最大“龐氏騙局”。上世紀30年代,美國還是債權國,而現在則是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英國媒體認為,對于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美國而言,“最后的審判日”似乎依舊遙不可及,但如果投資者爭先恐后將更多現金放進美國國債“安全港”里是很危險的,“仔細看看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狀況就會發現,所謂的‘安全港’根本就是子虛烏有,這個‘安全港’倒是與1941年時的珍珠港有著相同的安全系數”。
針對美日舉債規模增加和希臘等國遭遇債務危機的問題,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孫立堅教授表示,日本大規模發行國債性質是建設國債,是為了解決日本老百姓民生方面的問題的,長期來看,如果搞得好,可以釋放日本經濟中內需與消費的潛力,促進經濟增長。而美元的霸權地位保證美國可以比日本政府舉債更多,實在走不下去的時候,美國政府可以通過“印美元”的方式來勾銷這筆債務。相比之下,部分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過度依賴發達國家貸款來維持經濟增長的小國家有可能會步希臘的后塵,出現危機。
眾議中國減持美國國債
在所有國家的國債“交易”中,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的任何變化都最受世界關注。中國去年12月減持342億美元美國國債,不僅創了10年來最高單月金額,也使中國降為美國第二大債權國。一時間,很多分析開始說,“中國可能要通過減持國債向美國政府施壓”。美國《紐約郵報》的一位財經問題專欄撰稿人說:“我多年來一直警告說,只要美國不停止從那些不一定是美國的朋友的人那里借錢,情況就不會變好。很多人似乎現在明白過來了,這個問題也是美國的國家安全問題。”《華爾街日報》的一篇文章認為,“中國對美國國債的積累,成了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一個政治問題”。有美國學者曾說,“在中國這成了一個問題,因為他們說,如果手里所有的錢都是美元,為什么不施加更多影響?”
在美國媒體的擔憂聲中,也有相對樂觀的分析說,中國大量持有美國國債已使兩國在財政上互相依賴,所以,這使得中國不大可能持續拋售美國國債,而且為保持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穩定和維持巨額國際收支盈余,中國的央行別無選擇,因此,美國國債仍然是中國存放外匯儲備最方便、最安全的地方。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分析家認為,雖然中國的減持量按月度計算是創了紀錄,但相比中國持有的總量,也只是“一桶水中的一滴”。
俄羅斯一投資公司經理康斯坦丁·杰姆琴科預測,拋售美國國債將是中國一項長期戰略,特別會在兩年后加快,而那時世界經濟已經從金融危機中復蘇。俄國際金融市場公司領導人尼古拉·馬卡雷切夫曾表示,針對中美摩擦不斷增多,作為美國的最大債權國,中國從美國國債市場撤資的任何舉動都會引發金融世界的恐慌情緒。俄《導報》也報道說,中國已不愿成為美元最大的債權國,中國此舉不能不讓美國政府感到擔心,去年俄羅斯中央銀行高調宣布減持美國國債后,也引起國際金融市場一片震蕩。

由于希臘債務危機的影響,歐洲金融市場也陷入恐慌。
日本《每日新聞》評論認為,中國減持美國國債是“美中關系緊張的反映”。日本“瑞穗證券”的一位分析師說:“中國的行動包含著相當程度的政治意圖。”看到中國方面在減持美國國債,有日本分析家也提醒政府和銀行“應當注意并借鑒中國分散風險的策略”。
難尋治愈國債危機的妙藥
國債引發的兩難問題,也讓歐洲人頗感頭痛。法國《回聲報》載文評論說,希臘債務危機給歐盟出了個大難題,因為歐元區的一體化使得希臘國債的崩盤必然連帶整個歐元區,見死不救將讓大家一同落水。法國總統薩科齊怒斥無節制亂借國債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在歐盟方面,有人提出對希臘采取“保守療法”,即認購希臘長期國債的方法緩解其危機,但《西南法國報》批評這種做法“等于是把國債危機的爆發時間推后,是飲鴆止渴的行為”。
談到國債危機困擾世界的難題,澳新銀行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劉利剛認為,盡管日本有學者擔憂國債太多是“亡國行為”,但因為日本是高儲蓄國家,所以不會近期出現國家債務危機。在歐洲,希臘政府不會出現國家信用違約的情況,原因是一旦希臘突破這層底線,其他一些歐洲國家也會紛紛出現信用違約的情況,那將明明白白地告訴世界歐元區崩盤。這是德法等歐洲大國和美國都不愿意看到的。
劉利剛認為,從中國的國家利益來看,歐洲出現的債務危機給了中國良機,一方面可借機分散過多的美元儲備,逢低買入歐元債券,獲得豐厚息差;另一方面,通過金融外交手段適當幫助歐盟,增強中國的大國地位。至于中國自身發行的國債,整體規模還沒有超過中國GDP總量的26%,遠低于世界經濟合作組織的平均水平。只要中國經濟平穩地保持在8%左右的增長水平,中國的國債可以說一點風險都沒有,中國老百姓和外國投資者都可以放心持有。

2010年6月7日,歐元區成員國財政部長就7500億歐元的歐洲穩定機制達成一致。

危機后,美國到處推銷國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