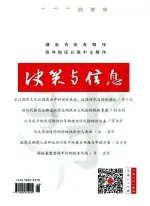胡春華治蒙新政:勒緊韁繩,放緩速度
文/李靜 葛江濤
8 年GDP增速全國第一的內蒙古今日民生怎么樣?新任內蒙古自治區委書記胡春華到任后,提出了勒緊韁繩、放緩速度的新政方略。
經濟增長與農民收入之比
從2000年開始,經濟排名一直在全國末尾的內蒙古開始了奇跡般的增長。2005年,內蒙古GDP的位次一舉跨過吉林、陜西等4省區,上升到全國第19位。2006年再跨過山西、廣西等3省區。到2009年,內蒙古已連續8年GDP增速領先全國其他省市。
能源開采、重化工是最強力的支撐點。素有“南糧北牧,東林西鐵,遍地是煤”之說的內蒙古,以豐富的煤氣資源、特別是全國第一的煤炭儲量,成為資源產業發展的理想之地。
2000年~2007年,自治區工業企業利潤增長38.9倍,增速是全國平均水平的7.5倍。
與此同時,由資源開發帶來的利益分配卻引發了新的社會問題。到2007年,內蒙古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距,已由2000年的1151元擴大到1408元。在崗職工平均工資、農牧民人均純收入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在諸多需要改善的民生指標中,牧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顯得最為迫切。根據內蒙古發展研究中心調研組的報告,“十五”期間內蒙古牧民純收入年均增長2.85%,低于“九五”時期6.38個百分點,增速明顯放緩。“十一五”以來,隨著中央和自治區惠農惠牧政策力度的加大,牧民純收入年均增長8.33%,速度明顯快于“十五”時期,但仍低于城鎮居民和農民3.93、3.83個百分點。2008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牧民人均純收入差距由2003年的3811.9元擴大到8226.7元。
中國農科院農業資源與農業區劃研究所研究員辛曉平說,隨著草地生態惡化,牧草質量和生產能力連年下降,導致肉產量增速放緩,牧民增收乏力。這些年,牧業半牧業旗縣農牧民的收入要低于農民人均純收入,且差距逐漸擴大,牧區正成為貧困人口最多的區域。
“第一”的差距
如果只看靚麗的GDP,原來一些復雜的問題就可能被簡單化。作為一個資源輸出大省,內蒙古用資源大輸出換得了經濟大增長。眼下的問題是,現實的收益與未來的收益如何評估、擺布呢?
對于內蒙古未來前景的思考乃至擔心一直在官員中存在,畢竟在內蒙古之前,中國已經有許多“資源大省”的曾經快樂而又痛苦的經驗可資借鑒。
山西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建設國家能源基地,同樣爭取到大量投資。最后形成了“挖煤、發電、引水、修路”以及修路后“再挖煤、再發電、再引水、再修路”的循環。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十幾年里,山西輕重工業投資比重接近1:30。
由于在低價輸出資源的同時或多或少地喪失了其他產業,山西又不得不高價從外地購入消費品。此前有報道稱,1980年~1988年9年間山西由此導致的雙向價值損失達到654億元,年均流失72億元以上。
與今天內蒙古情況類似,山西即使在GDP快速增長之時,農民生活水平提高也不夠快。早有觀點認為:單靠資源輸出并不能贏得一個大的區域發展的全部。

2010年6月1日,胡春華向內蒙古烏蘭察布市四子王旗蒙古族小學贈送學習用品。

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土左旗民族學校老師用先進的教學設備上課
“我們不是沒意識到,但是沒人愿說。一直到胡春華書記來。”一位地方旗縣負責人說。
2009年12月30日,就任一個月的胡春華在自治區經濟工作會議上向各級干部提出:過去用多大力度抓“強區”,下一步就要用多大力度抓“富民”。
對一個擁有資源的區域來說,靠資源快開發、大開發尋求快增長、大崛起,有其歷史階段性的某種必然。而比開發更為復雜的是開發衍生的一系列問題和對發展全部內涵的考量。“一直講強區富民,胡春華書記一來,變成了富民強區。”錫林郭勒盟的一位基層官員說,雖然只是語序的調整,但已經感到內蒙古的發展將出現一種全新的民生生態。
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胡春華又明確表示:“我們不再追求第一的速度。”他坦然指出,內蒙古的不少民生指標不僅沒有達到全國平均水平,而且與先進省市差距太大:“強區”的實現效果,遠遠超越了“富民”。
在2010年的發展規劃目標中人們發現,自治區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增長遠低于2009年實際增幅,城鎮居民和農牧民人均收入增長目標卻高于2009年。
在不少內蒙古官員眼中,胡春華對民族團結和邊境穩定有著充分和深刻的認識。有人甚至評價他是一位民族問題專家。這個判斷來自胡春華14年的西藏經歷。在那里,他不僅學會了一口流利的藏語,還喝藏酒、跳藏族舞。
今年年初,內蒙古自治區出臺政策在財政上增加對牧業的支持。“以前也提過,但沒有解決實際問題。這次的政策含金量很高,比如牧民買牧業機械、買種畜都有補貼。這樣,牧民就直接增加了一些轉移性收入。”內蒙古發改委發展研究中心《北方經濟》總編輯包思勤說。
需要“止血”
胡春華的到來不僅帶來了新的發展思路,對于經濟增長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3月下旬,他在鄂爾多斯的杭錦能源化工區考察,提出“要跨地區發展”。
“意思就是,園區里不見得都是杭錦旗招商引資的項目,相鄰的巴彥淖爾的煤化工項目也可以拿到這里發展。杭錦旗可以把生活區放到相鄰的巴彥淖爾烏拉特前旗,那里都是農耕地,居住環境要好些。”鄂爾多斯市杭錦旗經濟商務局副局長崔建國認同這個理念。
自治區發改委發展研究中心服務業社會發展研究處處長李靖靖透露,自治區正著手編制一套規劃,具體推進“區域一體化”。“一下子打破原有的行政壁壘也不太可能。就是逐步地,首先從產業布局方面入手,將來還會過渡到城鎮一體化。”
不過,眼下內蒙古最大的問題恐怕還有在中央支持下盡快“止血”的問題:讓更多血液在體內循環,使每個牧民都受到滋養,讓每塊草原都得到恢復。
“高輸出、低回報”資源開發模式并非內蒙古獨有,但在民族地區,它的后果可能更為嚴重。
其實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內蒙古也曾經歷過一段不一樣的“黃金時期”。雖然當時GDP增長并沒有今天這樣迅猛,但改革開放后成長的一批青年干部已成為地方政府骨干,通過發展農牧業,群眾生活有顯著改善。
許多牧民都會回憶起這段“美好時光”:家里的電視等家用電器都是通過這一時期的積累購買的。
發展使國境線兩邊蒙古族本來不相上下的生活水準產生了落差:內蒙古不僅遠遠好于蒙古國,而且與臨近的漢族地區也沒有太大差距。
“新一代蒙古族青年有文化,更清楚哪些利益應該屬于誰。”多位地方官員均表示,在生態遭受某種程度的破壞的大背景下,“高輸出、低回報”的資源開發模式顯然不能再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