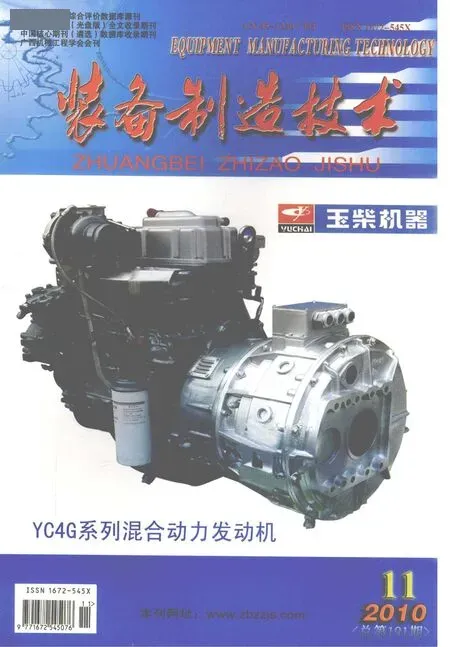不同試驗條件下阿特拉津的生物降解研究
徐冬英,呂錫武
(1.紹興文理學院 土木系 浙江 紹興 312000;2.東南大學環境工程系 江蘇 南京 210096;)
梅梁灣系太湖北部的一個湖灣,是無錫市著名的風景旅游區,也是該市賴以生存的水源地。近年來發現大量化學合成的有機化合物通過各種渠道和途徑進入水體,其中很多化合物在水體中長期滯留。在圍繞這一環境問題進行的各種研究工作中,有機物的生物降解性研究是當前重要的課題之一。該研究目的在于通過人工介質對湖水中的土著微生物進行有效的富集,在介質表面形成一層生物膜[1,2,3],通過微生物的降解作用來降解湖泊中所含微量有機物,為在示范工程區內有風浪、透明度小、無底泥淤積等難于恢復水生植物的區域內應用該技術提供參數。
阿特拉津是在1952年由Geigy化學公司研制開發的一種除草劑,1958年申請瑞士專利,1959年投入商業生產[4]。阿特拉津又名莠去津,英文名atrazine,化學名稱為2-氯-4-乙胺基-6-異丙胺基-1,3,5-三嗪,系均三氮苯類農藥,25℃時在水中的溶解度為33μg.ml-1。它適用于玉米、甘蔗、高梁、茶園和果園,可防除一年生禾本科雜草和闊葉雜草,
對某些多年生雜草也有抑制作用[5]。由于阿特拉津的大量生產和廣泛應用,已造成全球性的生態問題,阿特拉津的結構穩定,難以降解,在環境中廣泛分布[6~7]。Dodson等人[8]發現低濃度0.5~10μg/L阿特拉津的暴露可引起水蚤Daphnia胚胎雄性后代出生率的增加。Leeuwen等人[9]發現0.05~0.65μg/L水平的阿特拉津與胃癌的發生有關(置信度大于95%)。阿特拉津被認定為有潛在的致癌作用并可影響人體的內分泌系統[10,11]。
1 試驗設備與試驗方案
1.1 試驗裝置與試驗流程
試驗裝置及試驗流程分別如圖1、2,反應器內有掛膜良好的組合填料人工介質,在貯水池內投加微量阿特拉津,貯水池出水口連接硅膠管,通過蠕動泵調節流量。
1.2 試驗儀器與有機藥劑
55×45×35(cm3)試驗池;25WZB1.5-201無堵塞自吸泵(上海藍鯨電機制造有限公司);帶攪拌器的150L貯水池;BT00-300M型蠕動泵,泵頭型號TZ1515X(河北保定蘭格恒流公司);增氧泵;阿特拉津(Atrazine)AR上海試劑一廠。
1.3 阿特拉津降解試驗方案
1.3.1 馴化
低濃度阿特拉津馴化過程共歷時60天,其水力停留時間(HRT)為5天,在試驗池中置放人工介質,其中一個試驗池投加阿特拉津,另一個貯水池作為對照。同時,經常采集不同地點的太湖底泥,用超聲波將細菌分離出來,取上清液投加到試驗池中,以增加細菌豐度。
1.3.2 動態降解試驗
該試驗主要目的是考察微量有機物濃度和水力停留時間的改變對微量有機物生物降解情況的影響。實驗室內采用空調恒溫,通過調節蠕動泵轉速控制流量。進出水方式為下進上出。保持微量有機物投加濃度不變,水力停留時間逐步控制在5天﹑7天。每次改變停留時間,穩定運行2至3周后采每個試驗池的進出水樣用GC-MS法分析微量有機物含量。
1.3.3 靜態態降解試驗
在滅菌的三角瓶中加入含微量阿特拉津的水,依次調節溶液為相應pH值,然后放入培養箱中,并保持充分光照效應及供氧泵充分供氧,測定不同試驗條件下的降解效果,隔6天后測定有機物濃度,每次取3組重復樣,測定結果取平均值。
2 結果與討論
2.1 動態條件下阿特拉津濃度變化的降解性能
人工介質經水體中低濃度阿特拉津馴化后,富集了能降解對應有機物的微生物,因而在不同條件下均能對阿特拉津有一定降解作用。GC-MS法分析阿特拉津含量,阿特拉津的動態降解結果如圖3和圖4。

圖3 HR=7d阿特拉津降解

圖4 HRT=5d阿特拉津降解
從圖3、4可以看出,停留時間為5天和7天時,試驗池中去除率比較穩定,分別在50.0%~62.6%和66.4%~71.4%的范圍內,對照池中去除率有所提高,分別在7.6%~10.2%和9.9%~15.1%的范圍內。從阿特拉津進出水濃度角度看,試驗池中阿特拉津出水濃度明顯低于對照池中阿特拉津出水濃度,如阿特拉津進水濃度為6.2μg/L,19.9μg/L時,在HRT=5d的情況下,試驗池和對照池的阿特拉津出水濃度分別為3.1μg/L和5.7μg/L,7.8μg/L和18.9μg/L;在HRT=7d的情況下,試驗池和對照池的阿特拉津出水濃度分別為1.4μg/L和4.3μg/L,5.1μg/L和12.9μg/L,說明在停留時間內,經過馴化的生物膜可以有效去除一定濃度范圍的阿特拉津,且水力停留時間越低,其去除效果越差。
2.1 不同溫度條件下的降解性能
溫度是影響微生物生長代謝的一個重要因素,根據試驗中不同培養溫度(5℃、10℃、15℃、20℃、25℃、30℃、35℃)時的降解液定時取樣的有機物測試濃度和去除率的數據,繪制它們的歷時曲線。
由圖5可知,溫度對去除阿特拉津的影響非常顯著,在此溫度系列中,均能去除污染質阿特拉津,即使在低溫條件下,阿特拉津菌仍具有較好的生長代謝能力,對研究區地下水10℃左右阿特拉津污染的原位治理具有重要應用價值。由圖表明,在試驗的溫度范圍(5~20℃)內,阿特拉津菌對農藥污染質阿特拉津的去除能力隨環境溫度的升高而增加,20℃時阿特拉津的去除率為69.5%,明顯高于10℃時的去除率44.3%,而5℃時的去除率則為最小,溫度為25℃時,去除率為9.9%,阿特拉津的去除率逐漸下降,說明溫度高于25℃時,反而不利于農藥污染質阿特拉津的去除。這說明該菌在低溫條件下反而生長的更好,對阿特拉津的去除能力也較高。該菌確定為一種嗜冷菌,只適于在低溫條件下去除阿特拉津,高溫反而抑制了它的生化去除作用。

圖5 不同溫度下阿特拉津的降解
2.2 不同pH值下的降解性能
圖6為不同pH下組合介質對阿特拉津的去除效果。

圖6 不同pH下阿特拉津的降解
圖6表明,在HRT=6天,pH值對去除阿特拉津的影響也是非常明顯的。當pH值為6~7范圍內時其去除效果比較好,當pH值為6時,去除能力最高,而pH值過高或過低時,去除能力都受到抑制。即此類微生物降解適宜在微酸性至中性環境中生存。對于難于生物降解的農藥污染阿特拉津,在pH為5~10范圍內對其均有明顯的去除能力,其中在pH為6左右,去除液的濃度下降近似達最小值,之后的去除趨于緩慢。其原因之一是體系中營養物質的消耗而抑制或阻止阿特拉津菌的生長代謝和對污染質的去除。圖3.5中反映在pH值為4、9時的去除率較小而在pH值為6和7的去除率最大。如pH為6時,阿特拉津的去除率為60%,而pH值為4和9時,阿特拉津的去除率則明顯低于pH值為6和7的去除率。可見,在此pH值范圍的系列試驗中,阿特拉津適宜的pH值范圍是6~7,此時的弱酸堿環境條件下,阿特拉津菌具有較好的去除污染質的能力,與野外條件下的弱堿性(pH值7.5左右)地下水環境條件比較接近,有利于菌種在實際原位治理中的應用[12]。
3 結論
依據上述試驗結果和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結論:
(1)通過人工介質富集的微生物的降解作用,對水體中所含硝基苯具有一定降解去除作用。當停留時間為7天時,硝基苯的去除率在66.2%~75.6%的范圍內。且HRT=7d的去除效果明顯優于HRT=5d的去除效果。
(2)溫度對有機物的去除影響很大,在試驗的溫度范圍(5~20℃)內,阿特拉津菌對農藥污染質阿特拉津的去除能力隨環境溫度的升高而增加,溫度高于25℃時,反而不利于農藥污染質阿特拉津的去除。這說明該菌在低溫條件下反而生長的更好,對阿特拉津的去除能力也較高。該菌確定為一種嗜冷菌,只適于在低溫條件下去除阿特拉津,高溫反而抑制了它的生化去除作用。
(3)阿特拉津適宜的pH值范圍是6~7,此時的弱酸堿環境條件下,阿特拉津菌具有較好的去除污染質的能力,與野外條件下的弱堿性(pH值7.5左右)地下水環境條件比較接近,有利于菌種在實際原位治理中的應用。
[1]徐冬英,呂錫武,王志雄.微生物降解阿特拉津試驗研究[J].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05,25(10):38-41.
[2]徐冬英,呂錫武,吳敏,等.微生物降解阿特拉津、酞酸酯類有機物試驗研究[J].凈水技術,2006,25(1):52-54.
[3]徐冬英,呂錫武.微生物降解1,2,4-三氯苯試驗研究[J].南京師范大學學報(工程技術版),2007,7(4):55-58.
[4]王世杰,谷慶寶,杜平,等.零價鐵表面積對泥漿反應體系中阿特拉津降解行為的影響[J].環境科學研究,2007,20(6):106-109.
[3]李清波,黃國宏,王顏紅,等.阿特拉津生態風險及其檢測和修復技術研究進展[J].應用生態學報2002,13(5):625~628.
[4]胡宏韜,林學鈺,劉娜,等.阿特拉津降解菌的生長規律及降解特征的實驗[J].城市環境與城市生態2003,16(3):20~22.
[5]Mills M S et al.Preferential dealkylation reactions of s-triazine herbicides in the unsaturated zone[J].Environ.Sci.Technol.1994,28:600~605.
[6]Schottler S P et al.Atrazine,alachlor,and cyanazine in a large agricultural river system[J].Environ.Sci.Technol.1994,28:1079~1089.
[7]蔡寶立,黃金勇.除草劑阿特拉津生物降解研究進展[J].生物工程進展,1999,19(3):7~11
[8]Dodson S L,Merritt C M,Shannahan J P.Lowexposure concentrations of atrazine increase male production in Daphnia.Environ Toxicol& Chemistry,1999,18(7):1568~1573.
[9]Van Leeuwen J A,Walnter-Toews D,Abernathy T.Associations between stomach cancer incidence and drinking water contamination with atrazine and nitrate in Ontario(Canada)agroecosystems,1987~1991,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1999,28(5):836~840.
[10]Nalina S,Elizabeth D.A review of epidemiologic studies of triazene herbicides and cancer.Critical Reviews in Toxicology,1997,27(6):599~613.
[11]任晉,蔣可.內分泌干擾劑的研究進展.化學進展,2000,13(2):135~144.
[12]胡宏韜,程金平.阿特拉津降解菌的生長與降解特征研究[J].上海應用技術學院學報,2005,5(2):9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