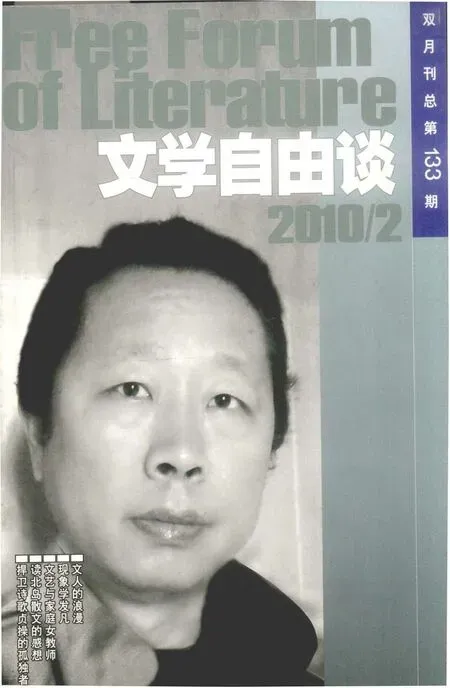日讀一萬與夜寫三千
●文 高 為
認識幾位“牛人”—— 一夜能寫三千字,這么說還不確切,應是夜夜能寫三千字,起碼他們是這么要求自己的。
第一位牛人跳過好幾次槽,折騰來折騰去把自己的檔案跳丟了,也不太在意,順勢成了自由人。我認識他的時候,這位老兄正在一家雜志社打工——當編輯。同事說他每天夜深人靜時三小時寫三千字,而且全是用手寫!寫得中指都有些變形了。我一聽不由得肅然起敬,驚嘆不已——三小時他愣能寫三千字,而且夜夜如此!神啦!三小時我抄一千字都很勉強。盡管只見過兩面,他還是頗為不滿地脫口而出質問我:咋這么慢呢?!
慚愧慚愧!
此仁兄擅長寫紀實文學,報紙、雜志上總能見其大名。后來雜志社大換班,他又失業了。好在他有夜寫三千的本事,不至于太狼狽。一晃十幾年過去了,不知他現在是否還用手寫。去年突然在電視上看到了他,正在接受記者采訪,介紹他寫的一部大實業家的傳記,語言樸實無華,確實是文如其人。我祝他的三千(文)都能變成一萬(錢)!
第二位牛人是個處級“冒號”,手下幾十號人馬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都得操心,整天還要上工廠,下農村,跑機關,指導工作,指點創作,做匯報,聽匯報,開會,上電視做嘉賓,舉辦活動當評委等等等等,忙得不亦樂乎。哥們們不無夸張地說,他的朋友遍天下,走到哪都能碰到熟人。這種情況我就目睹了幾次:大伙正喝酒呢,忽然鄰桌有人同他打招呼,或他同鄰桌的熟人寒暄。這么一位超級忙人,不管回家多晚,也要寫夠三千字!用另一位作家的話形容:嘴比手快,腦子比嘴快,說話像打機關槍。
這個冒號出了名的好脾氣,沒見他發過火。一次朋友們去郊縣玩,晚上就不回來了。此公因為第二天一早要帶隊參觀,吃完晚飯不顧大家的一再挽留,自己打車又回了市里!即使這么忙,中短篇、長篇小說還是不斷問世,不能不說是奇跡。我想,這很大部分要歸功于他夜寫三千字的計劃和恒心。
第三位牛人是個地級市冒號(局級?處級?),也是我一位朋友,管的人和事就更多了,甚至連招商引資都管,全國到處跑,有時一不留神就跑出了國。業余時間還上網當版主。他是否夜寫三千字沒聽他說過,但他已經出的十本書在那擺著,包括經濟論文集、報告文學集、散文集、隨筆集,那能是什么時候寫的呢?沒有夜寫三千的本領根本不可能有這么大的成就。
在香港工作時,此冒號一天寫好幾篇文章(最多時一天寫七篇,同二戰時蘇聯的著名作家和記者愛倫堡有得一拼),在甲報刊登正方觀點,在乙報刊登反方觀點,自己跟自己干仗,挑起爭論在暗中偷著樂,練就了反復辯難、下筆千言、倚馬可待的本領。舉凡政治、經濟、哲學、文學、社會、婦女問題、婚姻戀愛等等等等,沒有不能寫的。此公也是語速極快、思維敏捷。白天忙得團團轉,什么時候寫作呢?只有晚上。
在下年過五旬,主動寫的文字攏共不到二十萬,年均四千,與夜寫三千相比,不啻天壤之別。夜寫三千,是打死我也達不到的目標。能達到此目標的人不會很多,但能夠日讀一萬的人不會太少。
胡耀邦同志嗜書如命,手不釋卷,號召我們要讀一億字的書。我算了一下,如果一天讀一萬字,讀完一億字需要三十年。如果每頁五六百字,一萬字也就十七到二十頁的篇幅,只要想讀,人人都能夠辦得到。
作為職業讀者——編輯,別說日讀一萬,就是日讀兩萬也不多。讀得多了,自然就有寫作沖動。“某些書仿佛能迸濺出瓊漿玉液,使我們陶醉,使我們受到感染,敦促我們拿起筆來。”(帕烏斯托夫斯基《金玫瑰》)不僅好書能誘使我們寫作,爛文也會刺激我們動筆。1990年我去北京參加英語四、六級作文閱卷,看到某些文理不通、缺胳膊短腿的文字時,忍不住就想拿起筆來替考生們寫。
職業讀者退休后還沒讀夠,就心滿意足地當起了“讀家”——隨心所欲,想讀什么讀什么,想讀多久讀多久。安徽一位同行,出過四本書,都是讀書筆記,現在把以前沒時間讀的書細心讀來,欣喜非常,贊揚《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是思想性、資料性、可讀性俱佳的杰作。說不定她又會寫一本讀書隨筆。我以前在大學的一位同事,工作幾十年了,職稱還沒解決,但他毫不在意,每天博覽各種圖書,自得其樂。對此,我完全理解。我也在盼著能從職業讀者晉升為“讀家”。
對于業余作家、非職業讀者來說,日讀一萬或夜寫三千固然很牛,要是既日讀一萬又夜寫三千那就更牛了。但如果反過來,日讀三千,夜寫一萬,那就更更牛了。一著名教授兼作家對同事評論他們的院長:寫的書比讀的書多,引起哄堂大笑,成了經典的名言,也成了持久的笑談。比這位院長還牛的是那位向央視要求正當權益而被封殺多年的著名笑星:我不讀別人的書,我只想寫書給別人讀!瞧瞧人家!瞧這氣魄!
葉兆言撰文引用張謇的話:30歲以前讀書,30歲至70歲做事,70歲以后做不動事了再讀書。這只適用于張謇這種絕頂聰明又有辦事能力而且長壽的天才(鬧著玩就中了秀才,臨時抱佛腳又點了狀元,幾千年恐怕就這么一位)。對于我輩凡夫俗子來說,讀書是終身的事,而這終身,誰知道是70歲,還是60歲,或者50歲?人生苦短,最好從現在開始,日讀一萬。一過30歲,我就邊讀邊忘了。所以叮囑女兒讀書要趁早,年輕人記憶力好。盡管書中既沒有千鐘粟,也沒有黃金屋,更沒有顏如玉,但讀書自有至樂,不足為外人道。
錢鐘書先生說:“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真正的讀書就是為了讀書而讀書,是自娛自樂,沒有功利性,沒有目的性,所讀的書都是“無用的”。對讀書的愛是無緣無故的。言必稱希臘羅馬不應被嘲諷,恰恰相反,應當被推崇,得到普及,因為那是素養,是素質。
1933年,愛因斯坦曾應邀為大學新生的出版物《小帽子》寫過一段話:“……永遠也不要把學習當成是一種任務,而只應看成是令人羨慕的機會,這個機會使你為自己的快樂而去認識精神王國中美的事物所具有的解放力量,還使你將來為社會做有益的工作。”(《愛因斯坦短簡綴編》)
讀書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不是工作方式。“為……而讀書”,境界就低了一等。為了考本、出國、晉升而死背章程,突擊外語,狂啃數字,那都不是讀書,確切些說,那是為別人讀書。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代學者的目的在修養自己的學問道德,現代學者的目的卻在裝飾自己,給別人看)此是正解,下段是戲說。
只讀不寫的人,有點像劉海戲金蟾的金蟾,只進不出,自私自利自滿自足。(“古之學者為己”)只寫不讀的人,頗似偉大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只出不進,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今之學者為人”)
如果日讀一萬不是了解科學民主,而只是反復讀《資治通鑒》,以至于讀了十多遍,掌握的是帝王馭臣愚民術而不是世界大勢進步潮流,那這樣的好學還是少一點的好。倘若夜寫三千都是無病呻吟,與藝術、現實、民生無關,一邊充分享受民主,一邊竭力鼓吹獨裁,東食西宿,一身二嫁,形神分裂,學位再多,也是豬油糊住了心眼,書都讀進了臀眼;本事再大,恰如張飛痛罵的呂布:喪心病狂的“三姓家奴”——轉益多爹是汝爹,那這樣的勤奮沒有也罷,否則著作等身無異于垃圾遍地,不能造福自己,只會貽害人間。
附記:此篇寫完,從《文學自由談》《中華讀書報》等處獲悉,云南省納西族作家王丕震,從62歲開始寫書,2003年5月去世。18年間共創作了142部歷史小說,總字數超過3000萬字,涉及中國100余位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現代名人,平均每天寫5000字,而且完全是手寫。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王丕震全集》共80卷,收入長篇歷史小說127部(另有15部暫時未收入)。抄錄于此,使讀者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還有更厲害的“牛人”存在!